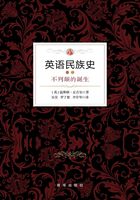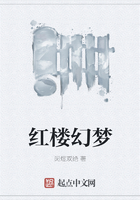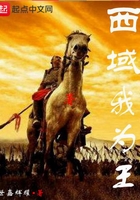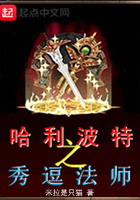汪皇后虽然在口头上劝告皇帝要慢慢的剪其党羽,削其权责,但事实上她自己却几乎是一刻也等不得。
皇帝对唐觉之的猜忌,正中汪皇后的下怀。汪皇后虽然闲居深宫,却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唐大将军长期执掌军务,军士但知其帅而不知其君,就已经让皇后为之担心,而这次出征在外,唐觉之既不奉皇上的敕旨,也不听朝廷的号令,拥兵自守,一意孤行,凡此种种迹象都表露出大将军事君不忠,似有不甘臣伏之心。
只是大将军现在还动他不得,他领军在外,要是闻讯生事而于阵前倒戈的话,搞不好会颠覆了社稷,所以即使再难忍受,也只能慢慢设法图谋。
汪皇后思来想去,觉得现在只有跟太宰周如喜捐弃前嫌,前朝后廷共同联手以压制唐觉之的嚣张跋扈。
那么首要之急就得先卸去唐觉之所掌的兵权,无兵无权,唐觉之便无所依仗,即使再厉害,也只剩下匹夫之勇,掖庭里的一个小小的狱卒,动根小指头都能把他捻碎。
然而怎样才能分得唐觉之的兵权,而且还要做得不显山露水,让他无所察觉,或者即使察觉了,也不以为意,这才是事成与否的关键所在。
况且这件事还不能做得太露骨,否则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后果堪忧。汪皇后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之后,终于定下心来,派出了身边的心腹宫正监何知书与周太宰结交传话。
汪皇后现在厌弃王守礼的油滑与世故,事情交给他办,往往不大靠得住,所以皇后决心要栽培一个一心听命于自己的人,在宫里要是没有两个贴心能干的奴才帮自己跑腿当差,简直就是事事难办,步步难行。
何知书本来对大将军唐觉之并无特别的好恶,何知书所恨的是左相唐会之,唐会之丢弃了徐州,他那尚在丰沛的家族只怕是凶多吉少。他何知书如今在后宫内廷混得人模人样,却不能保住自己的家族老少,叫他心中岂不抱憾怀恨!
汪皇后的心事跟周太宰的想法自然而然的一拍即合,周太宰一直以来也在考虑这事,许成龙能征善战,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材,皇帝应该加以重用,况且太宰也想培植私人,如果自己既能得到皇上的支持,又有来自军中的奥援,那么宰执的地位一定牢不可破。所以当宫正监何知书登门到访的时候,太宰大人不禁喜出望外,亲自降阶相迎。
太宰跟汪皇后虽说有些小小的矛盾,但这矛盾并非根深蒂固不可化解,当今大将军擅作威福,揽权自专,根本不将皇帝敕旨和朝廷政令放在眼里,如此一来,皇上何以行权而宰执如何施政?
况且大将军征战在外而并无大功,相反引来祸水,几乎使江淮不保,这正是罢除他兵权的好借口。太宰已经在皇上面前积极推动此事,如果再有皇后在枕边时常吹吹风,唐觉之收权归府应是意料中事。
周太宰与何宫正谈兴甚浓的聊了一个下午,两人在谈话的时候自然提都没提大将军的名字,也没有说起这换帅罢将之事。他们只是彼此闲话一些历朝历代掌军治国的经验得失,谈了些唐季和五代的藩镇之害,顺便也说了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高明之处。
两人的唔谈好象漫不经心,又象是在互打机锋,意在言外,品品却又余味无穷。
何宫正说:自古迄今,武人弄权,都非国家之福,身为宫里的内使,思之常心怀忧愤!
周太宰也叹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身为国家大臣如果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岂不愧疚?吾只要在位一天,必不容此事发生。
何宫正皱眉说:虽说事不迟疑,然终需从长计议,千万不可打草惊蛇!俗话说,狗子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是以不可不慎!
周太宰微笑道:权在朝廷,命出圣上,一切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凡事但取息事宁人为上。吾辈所为,岂为一己私心?
何宫正也笑道:太宰大人忠勤体国,皇后娘娘在宫里也是颇为称颂。
周太宰怡然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君臣相得,两不疑猜,实在是难能可贵。
何宫正又说:许将军战功卓著,值此朝廷用人之际,相爷应当选贤与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材……
周太宰说:内使所言极是,老夫亦有此意,当不遗余力在圣上面前极力保举,使干臣能将尽为朝廷所用。
何宫正晗首道:相爷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国家大事能有相爷操劳,又有什么可担忧的?
周太宰微笑不语,何知书这时也低下头喝茶,堂中两人寂然而座,堂外日已西沉,霞光余晖,诸色满天。
时日已晚,何知书言讫告归,出得厅堂,日落的余晖洒了一身,不觉抬头说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今日何幸,能与相爷作此倾心之谈。
周太宰道:内使大人光临寒舍,事前未能扫榻置酒,已是怠慢贵客,待他日有暇,当专致问候请约之意。
何知书拱手称谢:承蒙相爷厚爱,岂敢无事到府上叨扰。
周太宰说:你我相见如故,自不必虚伪客套,闲时常来,当把酒言欢,一醉方休。
何知书含笑再谢,登车欲走,临行前却又微笑言道:娘娘要小的带话与大人,国事烦劳,天下未安,大人殚精极虑,日理万机,所以尤需要养息身体,为国善自珍重……
周太宰拜谢说:皇后母仪天下,辅弼圣上,涎育圣嗣,厥功至伟,臣等惟有格外忠勤,全力以赴,方可不负抬爱厚望。请内使大人回宫后代为请安致意。
回到宫里,何知书赶紧将自己与太宰会面唔谈的情形一五一十的禀报给汪皇后知晓,汪皇后听罢连连点头,对周太宰的回复颇为满意。
汪皇后虽对唐觉之不甚放心,却也并不想赶尽杀绝,唐觉之要是识相,保全自家的荣华富贵自不消说,便是太尉大将军的官职在名义上也仍然可以继续当下去。朝廷不但不会为难大将军,反而会让他放心,同时也是让在外掌军领兵的将帅们安心,只要肯替朝廷卖命效力,皇上对于他们是格外宽容优渥的。
现在政事堂的周太宰和中宫的汪皇后都在替许成龙说好话,皇帝本人也很看中这个脱颖而出的将才,都说江南多秀士,北方出豪杰,呵呵,朕的江南也还是卧虎藏龙,人材济济。
皇帝私下里已经采纳了皇后的建议。皇后当时是面带忧色的跟他说,唐氏掌兵多年,军中尽是其私家子弟,长此以往,当恐黄袍加身的故事重演。妾听说许将军屡立奇功,陛下宜放手重用,用以分大将军之权,若有人心怀异图,亦足以制之!
皇帝深以为然,他现在乐于倾听皇后的意见,满朝的文武和天下的百姓或许都会有改朝换代之心,而作为自己的嫡妻元配的皇后,总不会想取而代之,君临天下。
况且皇后的贤德仁厚,天下皆知,象揖捕司送上来的呈文,提到京师的舆情,但凡说到皇后,每每都是称颂之言,说其贤惠仁德,千古难寻,彪炳史册,永受钦敬,皇上有此贤后,实是社稷苍生之福。还有人说,皇后跟太后一样,都是菩萨转世,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中宫有这样一位无可挑剔更无可指摘的皇后,让皇帝由敬生爱,这敬爱之心一起,自然对于皇后的劝告,就由起初的充耳不闻变成现在的心领神会。
皇帝说:待唐会之方大用歼灭徐州的贼兵,当召还许成龙委以重任。唐觉之坐守不战,拥兵观望,不赴京师之危难,殊为可恨!
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徐州围歼一直难以奏功报捷,唐会之和方大用虽以将近三倍于敌的兵力围攻徐州竟然久攻不下。
政事堂致书询问其故,唐左相回书朝廷说:新招的兵士,欠缺演练,不习战法,而徐州城池坚固,地势高拨,易守难攻,臣虽督师于城下,亦颇无奈,请朝廷增派军士协助攻城。
周太宰手执此疏,不顾君前失仪,在皇上面前“废物、饭桶”的一顿大骂:真是岂有此理!他弃城而逃时便说是城池年久失修,军士寡难敌众,恐将难守,怎么同一座徐州城,一但为敌人所占,这便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了?
皇帝对此也是颇为头疼,唐觉之与靖王相持于南阳,现在唐会之与宋有道又相持于徐州,南北僵持,既战不得又和不了,这仗竟是没法打了。
皇帝又一次提出调用驻防在京师的边军开拨前线,增援徐泗,却被周太宰所极力劝阻。皇帝想,边军一调,京师空虚,若再生变,将何以抵挡?于是暂罢此议。
陆太师建言说:攻城八法,水攻不成火攻,火攻不成那就掘暗道,架云梯,置硝石硫磺,臣不信会攻不下来。左相大人久攻不克,未免有些心浮气燥,朝廷应该严辞督责,诸军将士可鼓劲而不可泄气,万不能使其懈怠。
兵部据此拟定若干攻城的妙法奇招寄发给唐会之,然而就在这时,方大用的上书也送达到朝廷。方大用对于徐州久攻不下,却另有一套说法。他认为是唐会之偏听偏信,犹疑不决,因而损兵折将,延误战机。假若当时委臣以攻城重任,事当不至于此。
周太宰于是撺掇皇上,不妨换上方大用为主帅,节制诸军,指挥攻城。
陆太师却说:阵前换将,军中大忌,朝廷只有严加督责,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换帅。
周太宰听此言大是不快,拉下脸面,指责陆正己一心回护,不遗余力,其与唐氏究属姻亲,故以私废公。
陆太师也愤然辩称,他这全是替国家社稷着想,忠君忧国,岂有私谋,太宰若是见疑勾陷,当效仿前任柳国老,退归府第,不复问事,从此闲云野鹤,作世外逍遥之人……
周太宰便讥讽道:身处世外,心在红尘,纵然飞来飞去也只在帝都禁苑。
两人为此险此又争吵起来,皇帝左右为难,只得宣布散朝。
战事由此转入僵持,钱粮物资的消耗日甚一日,户部奏称,府库将告空虚。
太宰与众门人议,提出改铸新钱,以一当十,弥补国用的不足,至于钱上的铭文也由“承运通宝”改作了“承运元宝”,虽然如此而仍有不足,朝廷只能都摊派到州县下民身上。
江南虽称繁盛,百姓亦都不堪重负,原先吃米的人家如今都要掺瓜咽菜,至于穷乡僻壤之地,官吏为足额完差,只能敲骨剥髓,搜求务尽,浑然不顾生民困苦,奄奄一息几乎将死。
举国上下官吏民众因此都有了厌战恶兵之心。御史中丞周如乐省时度势,在朝中首倡罢兵谈和之论,一时跟风者甚众。
大将军在前方得知,上奏称,不灭靖逆,誓不还家!有倡言罢兵和谈者,请陛下斩之以安军心!
皇帝使人传话:和谈一事,纯系谣传,请大将军安心征讨,朕与朝臣静候佳音。
然而北方陷入僵持,西南却又不稳,新授封大理郡王的林东臣趁朝廷全力北讨、焦头烂额之际,于此时上表皇帝,说自己新近练就藤甲精兵和战象,愿意前来江南助朝廷一战。
书到朝廷之际,夷兵的前锋所及,已然逾越了当初双方约定汉夷各守的金川江。
皇帝再次感到吃惊,北边锋火正急,西南可不能再乱,当下急召宰执们商量,这也是屋漏偏逢大雨,周太宰和陆太师异口同声,都说眼下只能安抚,不宜动怒。
当下由政事堂拟诏,严厉申斥林东臣背盟毁约,犯境害民,应退兵归藩。
朝臣们写起文章自然都是好手,一篇雄文洋洋洒洒,说古道今,既晓以唐时南诏大理与大国通好,自守其境,而子孙蕃盛,享国绵长之理,又以诸葛孔明七擒孟获使远人归伏为喻,告诫林东臣,天朝大国威不可犯,郡王应知当年木成栋遗妻弃子,远窜外邦的旧事。
文章之末,亦透出朝廷不欲生事,委曲求全之意,晓尔大理郡王谨守职贡,素称勤勉,现愿带兵勤王,忠诚亦属可嘉,然朝廷北上讨逆,连奏大捷,并不需郡王带兵助战,宜退归藩地,自守自安。
林东臣到也没有妄动,他再上一书,以郡王职小位卑,而辖下地广人多,请皇帝陛下授予王爵之号,使名实相符。
接到林东臣的二次上书,朝廷到也放了心,区区所求,不在话下,皇帝当即诏准,并派遣使者给大理王送去王印、袍服以及许多馈赠赏赐。
战事转眼就拖到了十一月上,也就是大雪节气的这天,徐州在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终于被攻克,但是美中不足,由于唐会之和方大用彼此争抢着入城,两支人马互不相让,结果在一片混乱之中,让宋有道逮住机会,冲杀出一条血路,于千军万马中突围而走。
皇帝闻讯,跌足浩叹,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原指望活捉逆臣宋有道,执献于太庙,上能告慰祖宗的在天之灵,下能使天下百姓知朝廷之神武,所以奸佞伏法,山河光复,天大的一件好事,却生生的给搞砸了。
皇帝因此赌气不肯下诏称捷,经过周太宰陆太师的反复劝解,皇帝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朝臣的庆贺,并同意政事堂拨出银两赐赏劳军。
唐会之方大用见放跑了宋有道,也有点傻眼,相互埋怨了几回,回到自家的营帐后,都吩咐身边的文胆在写奏稿上表章的时候,尽量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失推给他人。而皇帝仍在生气,所以两边呈来的奏稿他都不看不批,留置不理。
徐州光复,唐会之方大用明里暗里的彼此争功,而双方的将士也为此常生口角争端,几乎到二虎不能相容的地步。唐会之以为自己才是独挡一面的主将,方大用不过是奉命由侧翼助攻,论功论劳皆不及我,而若非他贪功冒进,宋有道本来插翅难飞。
而方大用痛感于寄人篱下,虽有功而不显,何况他是降臣,要取信于上惟有立功建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一怒之下,率部北上,转而攻袭胶济,一举收复滕、兖二州及邹城、曲阜诸县。这样一来,唐会之守徐泗,方大用踞兖曲,双方各有所获,一时也平复了纷争。
徐州光复之后,贼兵远遁,金陵城转危为安,此前的路禁夜禁自此予以解除,调集来戍守京师的西南边军也都返回越州驻扎。
朝野上下这回才算是真真正正的松了口气,周如乐及一干御史们现在又开始申言讨贼,每次朝会,他们都是积极主战的一派,浑不提当初曾经力促和谈。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朝廷现在应挟余威,一鼓作气直捣洛上,又说大将军拥兵自重,意存观望,应予召回严加议处。
言官们虽无实权,但是上折子折腾恶心人最是拿手,谁叫大将军提议要斩倡言和谈者的人头!大将军征而不战,便是罪过,怨不得御史谏议们上弹章究劾。
就在皇帝和朝臣们都在敦促唐大将军挥师讨逆之际,忽然接到前方大将军的奏报,许成龙所率的孤军被贼兵围拥堵截在许昌。
这意外之变让皇帝心头惴惴,他裁示说:千军可弃,一将难求,许成龙务必要保全,大将军应当立即率军解围。
唐觉之不以为然,世无常胜将军,许成龙虽有神勇,究非神仙,让他吃上一堑,必能长许多见识,况且二万精骑也能支撑些许日子,到不必急于驰援。
唐觉之此时所想的,应该是趁靖逆的精锐被许成龙所吸引,突袭南阳,攻破靖逆的大营,这也是围魏救赵,一举两得。
唐觉之派出的探马都回来说,靖王自率一军转攻许昌,此时南阳的大营只有副帅领兵驻扎,从军而行的钦天监的天文生也说,后夜月晦星暗,将起大雾。
唐觉之以为机不可失,密令各部子夜出发,偷袭靖逆的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