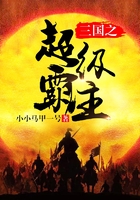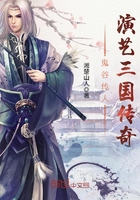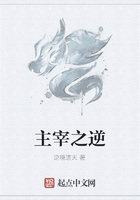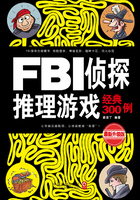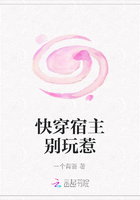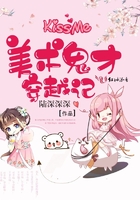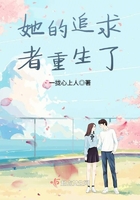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周太宰惶恐不安、度日如年的过了几天,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努力。他现在待罪在家自然不奉旨不得进宫,但是他的续弦夫人韩氏却仍然是深宫里的常客、太后跟前的红人,并且这几天因为自家相公的事,昌国夫人往宫里走动的更加频密,她要拯救自家这个倒霉的老头子。
在周太宰面前,韩夫人平静如常,总是开导劝慰,舒其心怀,但到了背着人时,她便蹙眉悲叹,这满城杀声阵阵,都要说动皇上拿取周相爷的项上人头,以谢天下。韩夫人并不认为皇上真会拿她家的老头子开刀泄愤,然而她怕就怕,还没等到皇上有赦旨,老头子自己就已经顶不住了,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这后半辈子岂不就跟眼泪作了伴?所以韩夫人无论如何也要搭救相爷。说穿了搭救相爷也就等于是在搭救自己。
昌国夫人韩氏因此不惮辛苦,日日穿梭于太宰府与永寿宫之间,她常常满怀着一泡眼泪向周太后诉说心中的无限委屈,她怎么能不委屈?相爷为国事几乎操碎了心,这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还有勤劳,皇上怎么不问个青红皂白,一竿子就把人打到底!
老头子这两天,长吁短叹,吃不香,睡不好,头发看看就白了一大把……且说承平库里的银两,相爷可是一两也没有往家里拿过,都分毫不差的用在皇上分派的工程营建上,长公主府,忠义郡王府,南乡郡主府,那个不是拿大把的银子堆筑砌就的!太后娘娘,您得说句公道话,用朝廷的银子替朝廷办事,这也有错么?虽说寅吃卯粮,用了旧年积攒的银子,这往后把它给补上,不就成了,怎么到了朝臣口中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死罪!你一句我一句的非要置人于死地?难道相爷死了,这银子就能回来了?这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话说完了,韩夫人不禁抽抽嗒嗒的哭,手里捏着的汗巾子,挤出来的都是眼泪水。而韩夫人只要一哭,周太后的眼睛就会泛红,她一想起她的两个弟弟,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唉,这大过年的,一个要闭门待罪,一个却是居家避祸,搞得好端端的年节都不能过得安生,这些朝臣还要杀要剐的,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诚心欺乎我的娘家人不是?
张福妃通常都侍候在周太后的身边,看着情形不对,就赶紧上前劝: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太后老菩萨的娘家兄弟,竟也敢去动得!当家过日子,总会有银钱不趁手的时候,一来典当,二来告借,只要度过眼前的难关就好,太宰理一国之事,自然亦同此理,便有些许疏漏过失,容他设法弥补就是。哪里就到要杀要剐的地步,这应该都是小人结党勾陷,欲置相爷于死地!
周太后听了这话,愈发恨恨的说:对着他那就是冲着我!哼,只要哀家我尚有一口气在,看他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这要杀要剐的,叫他们先来拿哀家问罪开刀!
因为太后这句话,韩夫人脸上的苦泪就都变成了喜泪,是啊,老头子有什么好怕的?有太后娘娘在哩!常言道,舅舅家的牛,外甥有只头,这话反过来说,外甥是当今皇上,难道当真会跟自家的娘舅过不去?
从周太后那里出来,韩夫人往往还会去拜望皇后娘娘,她指望着皇后也能够帮腔说上两句,可是汪皇后除了一开始安慰两句,别的就没再多说什么。但是皇后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她似乎是专门在等着自己来。
跟往常一样,汪皇后还是没有多说话,她只是淡淡问起周太后的态度,然后看似不经意的点拨了韩夫人一句:政事堂三相任事,何以独罪一人?相爷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周太后之前所讲的话已经让韩夫人宽了不少心,而汪皇后的话则被韩夫人如获至宝的带回去告诉给了相爷听。
周相爷一听,顿时喜出望外,三相任事,何以独罪一人?妙,妙,皇后这话极妙!朝堂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会使银子!结果管事干事的有罪,在旁边袖手的却把脏水全泼在我一个人身上!
周太宰越想越觉得自己冤,他操持国事,心力焦瘁,能说容易么?结果非但没落得好,反凭空遭来这场祸,周太宰想想不甘心,他要上书辩诬。盐酒的事,他是替皇上背了黑锅,何况这也是皇上当初所默许认可的。别人不明就里,加以攻讦诬陷,皇上可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太宰的这道剖冤陈情的上书,写得委委屈屈,哀哀戚戚,他费了一个晚上的功夫,涂了改,改了涂,反反复复的写写誊誊,字斟句酌的仔细推敲,一直忙到天光大亮,却还意犹未竟。
昔时的文人常以香草美人自喻喻人,周太宰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文中就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满腹幽怨,却哀而不伤的三贞九烈的女子,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却不幸被那些长袖善舞,工于狐媚,巧进谗言的妖物所嫉妒妨害,最终成为一个被夫君冷落的弃妇,但即使成为一个弃妇,她对自己的夫君依然忠贞热烈,九死而不悔,只是她就算去死,也要死得清白干净,也要让夫君明了自己那些暗藏于心却得不到回报的款款深情,因此太宰迫切希望皇上能在百忙之中召见自己。
太宰的文章固然写得很好,但皇帝却一直没有时间看。宫里正逢年节,单这行礼受贺,赐赏宴乐的诸多杂事便够人忙上一气,况且皇帝忙里偷闲时还要慎重考虑,罢了周如喜的相位,却该由谁来接掌中枢?
皇帝对太宰的一着不慎,从而身败名裂,终究觉得惋惜。太宰治国虽然不无瑕疵,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他能够兢兢业业的把交待的事情给办妥贴,小节上的些许差错,皇帝也不会去斤斤计较,然而皇帝这次到底是龙颜震怒了,他震怒就震怒在周如喜的瞒与骗。
承平库的银子本来用了就用了,前一阵子,前方吃紧,朝廷花钱如流水,国库空虚,民力憔悴,这些皇帝都是知道的,周相只要据实禀报,皇帝岂有不准动用的道理!然而错就错在,他背着皇帝使这瞒天过海之计,机关算尽,却给人识破揭穿,结果是弄巧成拙!现在国人皆曰可杀,场面不可收拾。皇帝只有顺从舆情民意,罢除他的相位,以此安抚京师朝野、上上下下的人心。
皇帝知道,今年的这个新春佳节百姓们过得不大痛快,先是物价飞涨,继而百物篑乏,朝廷却又银钱不足,府库空虚,对于缓解民生的艰困,一直拿不出象样的措施来。象揖捕司送来的的呈文就屡屡提到京师的民怨,因而对于太宰的倒台,百姓们都是拍手称快,人人叫好。皇帝本人也听到太宰倒台的那日,京师连绵不绝的锣鼓和鞭炮,似乎就连除夕夜都没有这般喧嚣热闹。
但是皇帝也常想到周太宰为相时的好处,他自从入相以来,君臣之间难得的彼此融洽,互不猜疑,太宰凡事都还谨慎小心,事上以忠,恭顺听话,这要是换作旁人为相,怕是再不会有这般方便。
虽然犹豫为难,皇帝最后还是下了罢相的决心,周如喜如今为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起因都在这物价飞涨,民生多艰上,皇帝如果不罢他的职,自然难以向天下的臣民交待。而罢了他的相位,将一干过失全推到他的身上,多多少少能够安抚一点人心,这江山社稷也才能借此安定稳固。
只是皇帝同时觉得罢相这股风潮,遂然而起,瞬间就刮得如此猛烈,以至于时下难以收场,这背后要是没人点火煽风,推波助澜,那是决计难叫人相信。
皇帝厌恶手下人的瞒骗,更痛恨的却是朝臣们的结党,太宰虽因瞒骗而去职,但这瞒骗说来不过是小错,而这结党才是真正的大恶。朝臣结党,图谋私利,危害国家,倾覆社稷,都在于权归豪门,利在私人,最后自然是视天子如弃履,而礼仪征伐出自诸侯。所以皇帝现在隐隐有些怀疑,陆太师和唐家兄弟之间是不是彼此有什么勾结联合?象太宰挪用承平库银两的事,前脚陆太师刚来告发,后脚唐左相便予以揭露,而一旦太宰去职,眼前现成的继任者惟左相唐会之而已。是不是因此这唐陆两家才会联手,千方百计设下这么一个局,让周太宰一头栽进去。至于要诛国贼,谢天下,朝中也数陆太师、唐郡王喊得最响;再则左相唐会之对于册储妃立太孙的事,当真如他所言的那么心无芥蒂,胸怀坦荡?私心里恐怕未必!
皇帝想,朕既不是个小孩子,更不是个大傻子,谁要是机关算尽或许就误了卿卿!
皇帝在正月初五这天终于召见了周太宰,一开始君臣见面,相顾都是无言。皇帝先叹了口气,命人为太宰设座,周太宰见皇上叹气便也叹了口气。
皇帝让太宰入座,然后便开门见山的问他:相国之任,太宰以为可选何人?
周如喜听了这话心里便明白了,自己罢职归家已经成为定局,再无挽回的余地,皇上只是借着闲谈,委宛的告诉他一声。太宰于是想保持镇定,然而情绪终究不免有些激动,他怔怔的望着皇上,满腹委屈,瘪瘪嘴刚要说话,却欲言又止。
皇上的眼睛也不看他,嘴里只是喃喃的说着:太宰为国操心,殚精竭虑,朕是知道的……这才打完了仗,库藏皆空,百废待兴,朕也都知道,而眼下民生苦困,衣食日用不足,却逢上这新年佳节,故而怨气冲天,说来实非太宰之罪……
皇帝的这席话,说得周太宰热泪盈眶,当下碰头至地,声调哽咽的说:此中甘苦,难与人言,伏惟皇上明鉴。
皇帝点点头,说:太宰请起,坐吧。太宰系朕舅父,为相以来做事总比外人当心,只是……只是……
皇帝正斟酌着怎么说时,周太宰却顿首道:皇上之意,臣都明白,皇上当不必多说。臣有负圣恩,归家待罪,乃是恪尽臣子的本分,岂敢对陛下有丝毫怀恨怨望之心。臣只是担心臣去职之后,圣上恐将为霄小之辈所媚惑蒙敝,一任大事今后也都操弄在奸佞小人的手中。
皇帝“噢”了一声,抬头看着太宰,似在等其下文。
周太宰振作精神,又说:陛下对臣信任,而臣亦不敢负陛下所托,凡事竭心竭力,力图家国中兴。然而朝中臣僚并不都能知臣苦心,有人心怀鬼胎,有人点火煽风,有人暗中使坏,凡事不以国家社稷为重,反而蝇营狗苟,干尽小人的勾当。象陆太师和唐郡王整日狼狈为奸,以攻讦诬蔑宰执大臣为能事,而唐左相入值中枢,却阳奉阴违,彼此暗通款曲,互为策应……臣不讳言,当初不经陛下诏准,擅自取用了承平库里的存银,此诚为大罪!然库中储银本为艰困时所使……况且臣原本也想呈奏,但想及年节将至,如此空劳皇上挂忧,反正挪用库银只是救一时之急,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再者等度过眼前的难关,来年便将所用的库银给弥补齐全,这也是臣一时犯下的糊涂,既欺瞒了圣上,又自蹈不法,虽悔之而无及……
皇帝叹道:挪用库银并非大事,这罢相去职说到底还在于民生艰困,百姓心生怨怒,朕不得不为……
周如喜忙说:身为太宰,既不能分担君父之忧,又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想及于此,臣实在是愧疚在心,汗颜无地!不过京师物价飞涨,京中众口一辞皆归罪于臣,说臣将盐酒二项折抵给城中的大商巨贾,故而价钱倍翻。可是当时臣所允折抵者只有盐酒二物,盐酒虽涨,各家各户又能用几何?其于民生所耗究属有限。而举凡油米粮谷民生日常所需之物,原不应涨?竟也一体暴涨?却究系何因?臣亦百思不得其解!年前皇上感念民生所需,专门差委唐左相督办此事,臣亦欣然,倾力相助。结果呢?市面益发萧条,商铺纷纷闭门,情形且更恶于前时!这明明就是左相大人办事不力,措置无方所致!然而唐左相不思弥补,却想方设法要推卸其责,意图稼祸于臣!于是才将当前困局归咎于臣私下动用承平库的事上。皇上若为此事降罪于臣,臣自然口服心服,不敢申辩;但若将市井萧条,百物匮乏的罪责归于臣下,臣恐怕担当不起,皇上亦自有明鉴……何况臣还听说,陆太师和唐郡王与京中的富商巨贾称兄道弟,交情深厚,而唐左相明出限价之令,陆唐两家暗中得尽先机,趁机囤集居奇,低买高卖,大发此中的横财。
皇帝皱眉说:果然如此?朕何以不知?
周如喜说:皇上但信揖捕司的呈文,然而掌领揖捕司的陆驸马,毕竟是陆太师的小三子,若事关其父,涉及亲长,为人子者当然要替尊者长者讳言。皇上何由知道这些细故详情?
皇帝皱眉不语,细想这话,果然有些道理,看来不能让左相唐会之担承重任。这唐陆两家,情谊独厚,彼此勾连,已属不妥,若再掌政理事,只怕尾大不掉,以至于祸害社稷。只是周如喜既遭罢斥,自然已不能再用,身为人君,朝三暮四,出尔反尔,恐将为臣民所笑。而三相当中,右相戴有忠年资尚浅,人望最低,况且其出身寒微,也不是可堪重用的人物。至于太师陆正己和大将军唐觉之,则早就排斥在选择之外;洛都留守方大用到可以用,但是用了他,旧京以及中原的防务却交给谁?皇帝想来想去,竟是想不出有适合的人选。
皇帝不觉低头叹息道:选相难啊,不论交给谁朕都不甚放心!
周太宰这时却说:有一个人不知皇上考虑过没有?
皇帝抬起头说:谁?你且说来听听。
周太宰说:臣以为忠义郡王宪源或许可以担此大任。
“宪源?”皇帝怔了怔,“宪源是宗室亲贵,虽尊荣富贵,依旧例却不得干政。”
周太宰说:事急从权,可以不拘旧例。忠义郡王是宗室亲贵,位居人臣之上,若能主掌政事,天下人必然肯服。况且郡王办事牢靠,此前郡王衔命办案,事涉长公主和唐郡王,两家各持威势,都不肯后退一步,这么一件难缠难断的糊涂案子,郡王居然给办得左右逢源,滴水不漏,使得上上下下既没意见也没脾气,足见郡王颇有些手段……臣再说一桩事,这京师的禁止纵马驱车令也是郡王首倡提议的,施行以来,标本兼治,官轿上路四平八稳,再无平日的拥挤难行……皇上,如此的贤能之人放着不用,还有何人能用?
太宰的话提醒了皇帝,当此用人之际,应该选贤与能,不拘一格。
初五的这一天,皇帝与太宰谈了将近两个时辰的闲话,直到周太后打发人来叫周太宰去体仁阁见面叙话,太宰这才拜辞了皇上。
而皇上对他说:凡事且宜宽心,相爷是朕母舅,虽有小过,亦有大功,朕不会为难相爷。
等到见过了自己的姐姐周太后,太宰周如喜更是一扫先前的颓唐,因为周太后跟他说:太宰位高权重,树大招风,早有人想取而代之,哼,幸好宫里还有我在,岂能让他们的痴心妄想遂愿得逞!
周太宰闻言感泣,周太后宽慰他说:你受了委屈,我都知道,皇帝也知道,自然会替你讨个公道。
周太宰返家,使人向忠义郡王称贺道喜,忠义郡王听言辩音,却是暗生隐忧。治国如当家,只是眼下这家却不大好当,自己就是出头卖乖也未必能够从中取巧,何况朝中的人事错综复杂,几家豪门彼此倾辄,若不小心陷身其中,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周如喜。
只是忠义郡王宪源最终也没有当成太宰,左相唐会之和右相戴有忠自然更不曾当此大任,皇上出人意料的将慈圣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御史中丞周如乐钦点为太宰,主掌政事。
当皇帝把这一决定在朝堂上公之于众的时候,朝臣们几乎难以置信。但是皇帝却是以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了这项任命。
周如乐出任太宰,其兄周如喜也没有退职归家,而是被皇上任为太傅,主修国史,以酬其功劳。皇帝希望朝臣们能够同心同德,以天下苍生为念,中兴国家,治臻大化。
事实上,在皇帝背后插手朝中人事的是周太后,而提议让周如乐出任太宰,掌领中枢政事的却是汪皇后。周太后对于周如喜的罢相去职始终耿耿于怀,朝臣们越是攻讦周氏兄弟,她就越是要站出来庇护她的娘家人。
汪皇后省时度势,劝告皇上听从母后的安排,皇后自有皇后的想法,周如乐既是储妃的祖父,又是皇上的母舅,如今且跟陆唐两家结下了梁子,朝中因此能够彼此制衡,相互牵扯,既有人想要专擅亦将由不得自己,身在后宫者,凡事但取折衷守衡之道,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皇后的提议既让周太后满意,更获得了皇帝的赞同,于是周如乐便脱颖而出,成为当朝太宰的不二人选。
然而宰执的更替并不能纾解民生的苦困,钱贱物贵,百物匮乏的局面丝毫未见改观。
承运八年的新年伊始,刚刚履新上任的周如乐周太宰心知重任在肩,所以踌躇满志的准备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