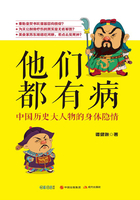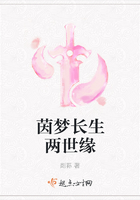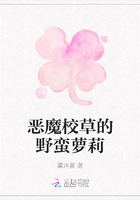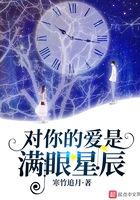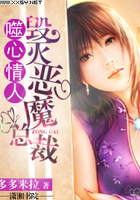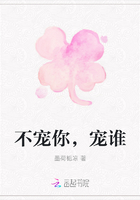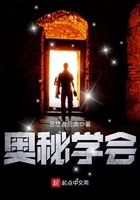承运八年有好些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月份,皇后娘娘生辰所在的四月就是其中之一。
在京师百姓的记忆里,整个四月的上、中两旬,南都金陵前所未有的喜庆热闹;亦是前所未有的人头攒动。尤其是在四月十五日,当高逾十丈,连点三夜的鳌山大灯彩被从上到下点亮放光的时候,万千臣民都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憾,这简直就象太白诗中所称道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美景如斯,人生难得几见?
而到了四月十六,皇后寿辰的正日,京师各商号会馆凑钱施放了好大一棚焰火,这烟花足足放了有个把时辰,璀灿的烟花把帝都的夜空映照得亮如白昼,也将江南的山河装点得分外妖娆,的的确确让人又叹为观止了一把。
皇上和皇后陪着两宫太后,带着深宫内廷里的后妃贵人们这天都登临丽景门的城楼,将内府所藏的“天地春”御酒遍赐京师的万民百姓。
而京师的各酒家食肆为了给皇后娘娘的寿庆添一份热闹,献一份孝心,也特意在丽景门的两庑下,设下锅灶,一字排开的煮起了长寿龙须面,游人到此,不需分文,尽可随意享用。
这一天是京师臣民备感荣宠幸福的时刻,每个人都抢着来到丽景门下,喝上一口御赐的美酒,吃上一著不花钱的寿面,顺便也睹一睹天颜,拜一拜至尊。
虽说满天的烟花总有散尽的时候,但逢着皇后娘娘千秋节的普天欢庆,大家趁着兴子自由自在的喜乐一把,说来也不枉在这盛世里快活的走过一回。
帝后贵人们在高大的丽景门上看灯赏景,俯瞰着城楼下如蚁般密集的子民,皇帝喜笑颜开的吩咐说:快让人再去搬些酒来,今天朕要与民同乐。
王守礼笑嘻嘻的回禀道:皇上,御酒已经开了四千坛,长寿面也安排了六十口大锅在煮,这不,还有好多人轮不上吃一口喝一杯哩……
汪皇后笑着插话说:让人再去开上二千坛御酒,皇上说了今天与民同乐,共庆升平,这二千坛御酒的酒钱,不必动官家的,就算在妾身的帐上。
皇后这话博得众人一致的称道,燕国长公主相与随喜,额外出钱加添一千坛御酒,唐贵妃又再添上八百坛,福妃等人都各是五百,宁安公主为母亲贺寿,自己出了八百坛,又替自己的一双儿女添加了二百坛。
李佛奴就是在这一天看见了他朝思暮想中的宁主儿。事实上,他所看到的那个人,他并不能够确定就是自己熟悉的那个既热情如火又温柔似水的宁主儿,她站在城楼上,优雅尊贵,仪态万方,而她的身份自然跟她现在所站的位置一样高不可及,宁主儿是公主!她果然是当今的宁安公主!如今这位公主跟皇上和一群娘娘们站在一起,站在臣民们的头顶上方,自己却可望而不可即。
李佛奴揉揉眼睛,往前挤了又挤,前边的人都回头冲他怒目,待看清他身上的巡字官衣,这才不情不愿的让出道来,前面还是人山人海,看样子是再难挤身进去,李佛奴只能仰头遥遥的望着城楼。没错,这一回他看得十分真切,宁安公主正是宁主儿,宁主儿便是宁安公主!他呆呆的仰着头望,脖子还没有酸,鼻子到先酸了。
“兄弟,再看可别看傻了!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么?走吧,马校尉该来换班了,先到我家去歇个脚,咱哥俩好好喝上几盅……呵呵,跟你喝酒就图个爽快,换了别人我还不乐意呢!”张宝官兜着后脑门顺手给了他一记,李佛奴这才有点回过神,心里却是一阵惘然,真是惘然如梦啊,那些稍纵即逝的欢好!他说不清自己到底追寻回味的是些什么滋味,但是这滋味他尝过了就再也忘不掉!
他木讷的跟在张宝官的身后走,时不时的回头,目光仍是定定的落在城楼上宁安公主的脸上、身上,依稀可以看见她在微笑,就象梦里的微笑,动人惑情,李佛奴皱着眉头,这会儿想哭又想笑……宁主儿这个人这时候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胸膛,把他的心塞得满满的,他几乎就挪不动脚了。
他根本就没有忘记她,只是有时候故意放在那里不想,唉,他怎么想,一个巡街的小卒配去想当朝的公主么?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傻里吧叽的做大梦哩!张宝官为这事不知骂过自己多少回。只是张宝官并不知道,他曾经在宁安公主的府第前守候了好几天,既不知道饥也不知道渴,只盼望能够见她一面,可是庭院深深,侯门似海,哪里能给他轻易的等到。便是好不容易看见公主的车驾,那车驾也是一溜烟的疾来疾去,豪奴健仆们四散在车驾旁边森严护卫。
车驾在李佛奴的眼前来来去去,李佛奴想朝前迈出一步,就给那些豪奴们给大力推搡回去。李佛奴这下终于明白,宁主儿与他,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老死都难再碰面,他就是硬生生的往前闯,也会被人给拿住了打死。在贵人们的眼里,他原是微不足道的尘埃,是个一捻就碎的蚂蚁。
李佛奴因此强压着不再想起,可是、可是,可是他今儿一见了她,立时就魂飞魄散,不复为常人。虽说张宝官好象明白自己的心事,总是张罗着要替自己找个媳妇,可是有句诗是怎么说的:曾经见过了沧海,就再也看不上别处的水……而宁主儿就是他的沧海!他便是那见识过沧海的人!
这一天,李佛奴被张宝官拉到家中喝酒,酒过三巡的时候,张宝官跟他说起一件喜事,因为皇后寿辰的缘故,朝廷将有封赏,而他已经保举李佛奴为从八品的都头。
李佛奴听了这话,闷闷的喝了一杯酒,心里没有半分喜欢。区区一个从八品的都头算得什么呢?想他本是东胡派到江南的使节,其家族在东胡也是累世的豪强,结果自己陷身在江南,有家归不得。现在就算他能够回去,他也没脸去见大汗和族人。何况,他还有心事未了。他想见宁主儿一面,他想要当面问问她,究竟她说的那些话还作不作数?
思念是种煎熬,但要是没这刻骨的思念,他苟活在江南又有什么意思?一具行尸走肉,埋身于行伍,终生碌碌,看不到一丝希望。
可是、可是他当真还能见到她么?她仿佛是天上的星星,而他就算身负双翅也未必能够摘她下来,所以虽有希望也总归有些渺茫……李佛奴怔怔的出神,眼前似乎又浮起宁主儿的微笑……
“来、来、来,喝酒,喝酒……这可是宫里的御酒‘天地春’,大内的公公叫咱们弟兄看护御酒,这不弟兄们顺手给我捎回了这几十坛,还有几百坛给送到了酒铺,公公们关照过了,卖出的酒钱日后对半分帐……哈哈,这可全托了皇后娘娘的无量寿福!”
张宝官兴致极好,频频举杯,李佛奴来者不拒,与他对酌,酒入愁肠,顿时化作一汪苦水,李佛奴叹息着说:张大哥,你说,我还能见到宁主儿么?
张宝官嘿嘿一笑,骂道:傻小子!什么宁主儿的,是你想见便能见的么?那可是天上地下差了十万八千里!
于是拿筷子敲着碗碟,唱起了一段戏文:好一场旖旎春梦,醒来却枕边空空,却记得那人笑,偏生是忘不掉!却记得那人笑,偏生是忘不掉!……你要我说,老哥我也说不好,总得看他妈的缘法……
李佛奴当下也拿筷子敲起桌上的碗碟,和着声跟唱:好一场旖旎春梦,醒来却枕边空空,却记得那人笑,偏生是忘不掉……偏生是忘不掉……偏生是忘不掉……来,来,张大哥,我们再干三碗……
不知不觉中,李佛奴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烟花散尽之后,还没等吃上五月端午的粽子,老天爷一下子就变了脸,滂沱的大雨成日成夜没完没了的下,下得人人都望着苍天哀声叹气,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江南在不停的下雨,眼看着江河里的水就要漫过河湖的堤防,然而更奇怪却是闽地乃至岭南却逢上了几十年未见的亢旱,老天似乎得了阴阳失调,五行失时的病,只可惜天有病,人难治。
天道莫非开始变了?渴望安生过日子的黎庶百姓们开始有些惊惊疑疑,于是就有人犹犹豫豫的把藏在箱子角落里的谶讳书偷偷摸摸的拿出来乱翻。掐指算,对照看,这从古到今,三皇五帝,谁见过盛世能长久?
这犯禁的话当然谁也不敢公开的说,背地里嘀咕都还怕不相干的人给听见。只是随着嘀咕此事的人越多,众人神神秘秘的越发显得心照不宣。
五月中旬,上游川江的来水溃决了洞庭和鄱阳两湖,沿湖州县一片汪洋,官吏上章告急,朝廷只得暂停营建中的山陵寿宫,左相戴有忠奉命急赴荆湖赈灾济民。而周如乐巧借籍田令所征得的银钱米谷,这下也派上了大用场。
水一处,旱一处,两处灾情遂然爆发,皇帝对此也很忧心,所以先是祭天地山川,后又亲往京师的龙王庙告难,南都各寺院的高僧大德亦都齐集在护国寺里颂经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也不知是皇上的虔诚感动了上苍,还是高僧的法力起了效用,总之,到五月下旬的时候,江南的淫雨渐渐地就止息了。而荆湖一带的灾民虽然逢灾遭难,但因戴左相携去的银钱米谷,自然也就人心安定,未掀起什么大乱子。现在只要大水一退,官府将督促灾民们各返故乡,开荒辟地,重建家园,再说以天下之大,难免水旱频乃,朝廷久经历练,见招拆招,自有一套尚称周全完备的应对之策,所以也用不着大担心。
而后随着江南雨止和荆湖水退,灾患几乎消解,朝廷上下正待松一口气,缓一缓神,闽地却意想不到的出了乱子。
这犯上作乱的仍是那个李三儿,年前他到是接受了朝廷的招降收编,由山匪海寇摇身一变成了建阳府的防御使,只是这官做得不大惬意,那建阳府的太守以文制武,事事掣肘,处处设限,分明仍当他是归附的山贼,于是李三儿心里一直就憋着这股子气,只是强忍着不曾发作。想来自己好歹已经改邪归正,现正做着这朝廷的命官,凡事自然应当俯首听命于上司。
谁知转过年来,这太守益发当他好欺,二月朝廷下令籍田,这本该文官所办的差事也压在他这个武职头上。建阳本山地,地瘦民贫,李三儿带兵催征,却往往空手而回,百姓穷困,委实榨不出太多的油水,太守却一昧催逼,这岂不要了穷家小户的性命!
因为这事,他跟太守屡起争执,到后来京中御史将巡建阳,太守情急无奈,只得亲自下到所属各县去催讨征要,总算凑齐缴清了积欠钱粮,而两人却因此彼此嫌恶。
到了三月,地方州郡为庆贺皇后娘娘的寿辰,又要主动上贡,奉献孝心,这差事李三儿再也推托不过,只好强行搜刮民间,虽说最终勉强交卸了差事,心头却也老大的不爽。
再后来闽境大旱,太守枯坐府衙,袖手旁观,全无一点措置,李三儿本系闽人,心念乡梓,故自掏私囊,施粥济人,不想反遭太守诬告,说他“收买人心,意图不轨”。
李三儿闻言大怒,与之争辩,太守强词夺理,李三儿忿怒难平,当下一刀斩杀了太守。这事做下,再无生理,只好重树反旗,复叛朝廷,自然原来“补天将军”的名号这回也改换作了“补天大王”。
江南大雨,闽地大旱,荆湖已成泽国,人心本已浮动,李三儿反旗一举,四方亡命之徒皆来投靠,而当地的饥民亦随军以求温饱。
李三儿见归附者众,胆气益壮,挥师连克建阳周边的府县关隘,其前锋直逼南平,声威阵势远非去年可比,也因此八闽震动,江南惊诧。
京中那些不满周氏兄弟的朝臣们这下子又获得了扳倒周如乐的机会,这李三儿不正是周如乐招抚劝降的,瞧他干的这些好事!引狼入室,招贼进门!别的且先不论,单论这“举荐匪人”的罪名,便足够让他引咎下台。
皇帝痛恨于朝臣缓急不分,于朝堂上严加痛斥。皇帝这次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眼下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朝臣们谁上谁下,而是要君臣一起同心协力,剿灭此顽匪反贼!因此皇帝特命皇叔宪源、陆太师、唐郡王、周太傅等一干宗室亲贵,参预国事,会商军情。
这一次御前会商,君臣都认为,贼匪天生反骨,朝廷前番招抚,已是仁至义尽,居然降而复叛,那是自寻死路,朝廷应当全力剿灭,以斩草除根,永绝匪患。皇帝最后诏以骠骑将军、右相许成龙为闽越节度大使,以太傅周如喜为监军,领兵五万前往进剿。
兵部所拨给的兵丁本是驻守西南的边军,也即是后来移驻于越州的那一支。许成龙心知这些边军,拖家带口,善垦而不善战,所以内心希望皇上能将自己原来所部的“百胜常捷军”归由自己指挥,但是又怕皇上不允。常胜百捷军如今已归入金吾卫,属于皇帝自将的亲军,其差遣调动非臣下能够插手干预。
许成龙把心中忧虑说给监军的周太傅听,周太傅听了,竟比他还急,忙不迭的拉他去见皇上,所有许成龙不好说得的话,自然也由周如喜代他说了。
皇帝先还迟疑,到最后终于首肯,许成龙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出了殿门便连边向周太傅道谢。周太傅说:谢我做什么?往后这行军打仗的事老夫还要多多仰仗将军。
周太后是从韩夫人口里听说了周太傅被差遣前往闽地监军,周太后现在一听到要动刀兵,就觉得心惊肉跳,连忙把皇后叫来盘问。
汪皇后说: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山匪毛贼,占山为王,妄图螳臂当车,等到大军一到,自当肃清扫平,母后娘娘无须担心忧虑。
周太后叹道:天下这不是好端端的么?怎么总是有人要犯上作乱?便想过几天安生的日子也是不能!阿弥陀佛,这些乱臣贼子,佛祖应罚他们来世变作畜生!
韩夫人却说:相爷是个呆秀才,对这行军打仗的事上可是一窍不通,何况年纪大了,身子又不好,别人不派去监军却派了老不中用的相爷?太后老菩萨,您是不知道,朝中向来有人作奸使坏,专跟我家相爷过不去!
汪皇后用眼里的余光扫了韩夫人一眼,正色说:“皇上派太傅监军,乃因太傅是自家的娘舅,所以打从心里面信得过。”
周太后点头说:一家人原不说两家话,太傅此去立了功劳,也好堵住那些惹事生非的嘴。
汪皇后几句话宽了周太后的心,正待告退,周太后却叫住她,喜滋滋的说:福妃那孩子好象是有喜了!
汪皇后一怔,环顾太后的身边左右果然少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张福妃,周太后看出皇后的疑虑,笑道:她既然有了身子,我岂能再让她成日侍候,要是伤了胎气,岂不是我的罪过。这孩子,当年我一看就知道是个有福的,自然错不了!这不,虽说承幸比别人晚,这肚子却比旁人都更争气!
韩夫人笑道:太后老菩萨看人,自然是一看一个准……
汪皇后勉强笑了一笑:母后看人自然有些门道,儿臣这就去看看她。
周太后说:你叫她不要惦记我,好生小心的养着身子。若有什么需要,还劳皇后多替她费些心。
汪皇后说:子孙延绵,宗族兴旺,社稷有靠,这才是多福多寿之征!儿臣岂敢不尽心!
韩夫人说:皇后娘娘待人素来仁慈宽厚,宫里宫外没有不敬服的,太后老菩萨这话似乎说重了些。
周太后笑道:话我是说重了些,好在皇后孝顺,办事也有条理,没有让我不放心的地方。
从体仁阁出来,汪皇后自己并没去看望张福妃,她只是打发何知书代她去探视了一回。何知书回来跟她说:福妃娘娘怀了身孕不假,可就是哼哼唧唧当自己是怀了龙卵,站不是,坐不是,躺不是,走不是,总之什么都不是……
汪皇后淡淡的一笑:她容易么?等了这么多年,又眼巴巴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皇上临幸了一回,居然这就有了!还别说,她当真是有些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