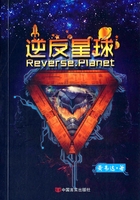站在清风拂面的窗台旁,邝亚滴捧着一只八音盒。这只八音盒饱满、娇小、通体墨黑,漆工极为精细。盒盖上是一朵小小的金色玫瑰,点缀在一角,如同一个孤独的忧思。八音盒的外形是半圆的,宛若舞会中的淑女帽,整个造型处理得干净流畅,是一件出色的手工艺品。
邝亚滴把八音盒放在窗台上,打开它,一段“叮咚叮咚”的音乐像小溪一样流进耳朵里。邝亚滴看着窗下的梧桐大街,来往穿梭的车辆印证了城市的喧闹与不安。邝亚滴喜欢以这样的姿态俯视这条大街,特别是这样的夜晚,街灯亮起来,闪闪烁烁的小光点串成一条不太光滑的绸带,给视野以一幅缀有诗意的图画,邝亚滴与安波并肩在这画上可以走上好长一段篇幅。与所有热恋中的情人一样,他们把枯燥的散步当作了浪漫旅程,在梧桐的伴随下并肩行走。
“先生,要马车么?”常会有这样的吆喝在这对沉醉于絮语中的情人身旁响起,这座发达城市保留了少量带牛皮雨篷的老式马车,它们代表了城市的高尚品位。对都市来说,品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必须的。的确,在散步劳顿之际,能坐上一辆这样的活古董感觉真是不错。
“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安波道。
“好吧。”他装出意犹未尽的样子(其实脚掌已很酸疼了)。
于是马车把他们送了回来……
邝亚滴将目光从梧桐大街撤回,不知从哪个瞬间起,眼泪充盈了他的眼眶。
拉上窗帘,夜幕般的黑暗均匀地涂抹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邝亚滴慢慢蹲下,户外吹过了一片风,使刚拉上的窗帘幅度很大地抖动。风坚持了几秒,窗帘呈船帆的造型鼓起来,旋即被吸出窗外,在夜色中猎猎作响。这其间,一件物品被窗帘击中,小溪一样的音乐荡漾在无边的空间里。一记刺耳的碎裂声使邝亚滴回过神来,他把头探出窗外,已经晚了。
邝亚滴头冲下凝固了好久,临街的楼房下是坚实的地坪。由于光线的缘故,什么也看不见,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爱情连同那只精致的八音盒被摔得稀巴烂了。的确,有时候虚幻的爱情会具体到一件物品的程度。
邝亚滴转过身,打开了蛋形顶灯,面对着眼前的废墟,的确是一片废墟,破坏力之强令邝亚滴感到震惊。因为他看见的并不是被砸坏的衣柜、矮橱、报时钟,也不是那盘被拉出内芯,并撕成破烂的录像带,他看见的是疯狂的安波正在哭喊中毁坏这一切的情景。他流泪了,不,他一直在流泪,眼泪的成分却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可冠名为痛苦、后悔、内疚、绝望。邝亚滴终于哭出声来,嘴唇哆嗦成一团:“安波——难道我就这样失去你了。”
安波给他的回答则是:“你这个该死的流氓,下流坯!”
这句话舞动在那盘录像带的贴纸上,笔迹潦草,甚至将厚厚的贴纸也戳坏了(那个感叹号的圆点)。可以想象,安波写这行字时,把笔当作了刀,把录像带当作了邝亚滴,她先是在情人身上一通乱砍,最后在他的胸膛上一记猛刺,用那个圆点把情人杀死在了心中。
满脸泪痕的邝亚滴捡起了录像带,它至少被安波摔了十次,塑料外壳龟裂成几瓣,内芯被拉出,地板上有长短不一的断线,如同委屈的蚯蚓。邝亚滴喉咙里有难以疏通的堵塞感,他捏紧一截芯头往外扯,拆一件毛衣一样动作飞快,终于,手势被卡了一下停顿下来。
“去你妈的。”窗帘再次在风中鼓起,在它被吸出窗外的一刹那,邝亚滴的身手像标枪运动员那样果断而敏捷,录像盒见缝插针地飞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