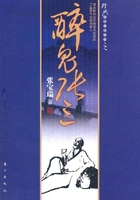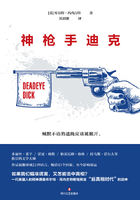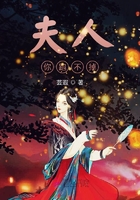华金最喜欢清晨。
他喜欢那些晴朗的清晨,天空由粉色渐渐转黄,最后变成天蓝。若天不晴朗,他喜欢雾气像一张毛毯笼罩着整个城市,绵延上所有的山峰和公路,浓厚得有时他可以伸手触碰到。
他喜欢清晨的宁静。他可以滑着滑板走完一整条街而不用担心撞上漫步的游客或迫使父母突然抱开学步的孩子。他喜欢独自一人的孤独,因为那时的“孤独”更像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太阳升起、雾气消散、现实复苏、众人醒觉之后,熙熙攘攘中的孤独则更让人难以忍受。
华金从山丘上朝着艺术中心猛冲下去,接着左转。滑板上的轮子是新的,它们是他的第18对领养父母“只因为想送”而送给他的礼物。
马克和琳达是好人,他们已经领养了他快两年,而且华金喜欢他们。琳达教华金开他们的旧小货车,不介意他把后排车门撞凹了一小块;而马克在上一个夏天带他去看了六场棒球比赛,虽然他们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起,每当裁判做出正确判决就不约而同地点头。比赛结束后,有一个老爷爷说:“真高兴能看到有爸爸带着儿子一起来看球。”这时马克咧嘴笑着,手环绕过华金的肩,而华金却飞红了脸,感觉自己快要发烧。
关于自己小时候的事,华金知道一些但不多。他一岁的时候被自己的母亲送进了寄养机构。他曾看到过一次自己的出生证明,因此知道生母的名字叫梅利莎·泰勒,父亲姓古铁雷斯。但在那之后他已经换了十来个社工,梅利莎也早已失去了抚养权。在他小的时候,梅利莎从没来探望过他。有时候华金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世上最坏的小孩,所以连亲生妈妈都不愿意见他。
对于他的生父,他只知道两件事。第一是他的姓氏,而第二件事华金照照镜子就能知道:父亲不是白人。某次,当华金表示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时,某个寄养家庭里的兄弟曾告诉他:“你看起来像墨西哥人。”没人在这件事上争论,所以事情就这样下了定论:华金是墨西哥裔。
过去的养父母和寄养家庭有好有坏。有一位养母曾经大发雷霆,用一把木梳狠狠敲了他的后脑勺,导致他像一个卡通角色一样头顶实实在在地冒了金星;有一对老夫妻因为某种华金不能理解的理由非要绑死他的左手,逼迫他用右手做事(但没用,华金依旧是个左撇子);有一位养父喜欢掐华金的后颈,用一种华金难以忘却的方式折磨他的脊椎;还有一对养父母把寄养孩子的食物单独放,那些无品牌小店自产的麦片就放在给他们亲骨肉吃的品牌麦片下面。
但另一方面,却也有朱厄妮塔这样的,这位在某个冬天他得肠胃炎时抚摸着他的头边哭边喊他“宝贝”的养母;有伊夫琳,她曾经在后院组织水球大赛,也曾在给他唱三只小鸡躲到鸡妈妈翅膀下的歌时睡着了;还有里克,这位曾给华金买了一整套油画棒只因为他觉得华金“真的太有天赋了”的养父。(可六个月以后,有一次里克喝多了和邻居动了拳脚,于是华金就被迫留下这套油画棒,离开了这个寄养家庭。华金现在依旧对失去他们感到伤心。)
马克和琳达是最新的寄养父母,并且,他们想要收养华金。
他们昨晚问过他了,当时他坐在餐桌边安装新的滑板轮。他们坐在他对面,双手交握。华金立刻就知道他们是要叫他离开。他已经被领养过17次了,以至于他对这些信号非常熟悉。他们会找一大堆借口,会道歉,有时候还会流眼泪(但华金从来不哭),可结局总是一样的,华金会将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放进垃圾袋里,然后等社工来接他去一个新家。(有一次,一个社工给他带来了一个手提箱,但在接下来的家庭里,那手提箱毁在了两个打架的小孩手里。不过华金更偏爱垃圾袋,因为那样他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华金。”琳达开口,但华金打断了她。他喜欢琳达,不想让她留给他最后的回忆是颤抖的借口和无力的保证。
“不,没事,”他说,“我明白,没事的。只是——是因为我弄坏了车门吗?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能修好的。”华金不确定自己能做到——他在艺术中心的工作并没有使他成为百万富翁,而他完全不知道靠自己该怎么修好那凹痕。不过,嘿,这不正是YouTube存在的意义吗?
“等等,什么?”琳达说。马克将他的椅子拉近华金,这使得华金本能地向后退了退,“别担心车,亲爱的,我们想说的不是那个。”
华金很少感到不对劲。经年累月,他已经非常擅长预测人们会做什么,会作何反应。而当他不能预测他们的行为时,他也懂怎么去引导,进而使他再次了然人心。马克和琳达带他去看的心理治疗师把这叫作“防御机制”,而华金想,这真像是一个永远不需要防御机制的人会讲的话。
但琳达没照着华金心里的剧本念。
马克俯身过来,手搭上华金的前臂,手上稍稍有些用力。但没关系,因为华金知道马克永远不会伤害他的,而即使他有那个居心,自己也比马克高三英寸重30磅,他很快就可以摆平他。而且,他觉得马克似乎是想让他保持平静。“伙计,”马克说,“你妈……琳达和我想跟你说件重要的事。如果你不介意,并且同意的话,我们想收养你。”
琳达跟着点头,眼里泛着光芒。“我们爱你,非常爱你,华金,”她说,“你……你就像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不能想象只是领养,而不是永久地收养你。”
华金的脑袋嗡嗡直响,几乎感到眩晕。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滑板轮,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样的体验之前只有过一次,那时马克和琳达(很随意,非常随意地)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叫他们“爸爸”和“妈妈”。“当然,你愿意的话。”琳达那时说,虽然当时他转过了身,但仍旧能听见她声音里的颤抖。
“你说了算,小家伙。”马克在岛式橱台旁加了一句,他在那儿盯了好一会儿笔记本电脑。但华金注意到,他并没有在点击网站,只是在同一个页面上来回滚动。
“好。”华金说。而他在晚饭时还是叫了她“琳达”,仿佛早上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华金选择假装没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神情。
华金从没叫过任何人妈妈或爸爸。他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在某些比较严厉的家庭里,叫某某先生或者女士。他的寄养生涯里从未像其他被领养的小孩有时会碰到的那样有祖父母、阿姨、叔叔或是堂表兄妹。
而事实上,华金很想叫琳达和马克妈妈和爸爸。他那么迫切,甚至能感到那两个词语正堵在喉咙里烤得他口干舌燥。如果他能把这两个词说出来,能让他们开心,能最终成为有人收养、有父有母的孩子,一切都会简单许多。
但它们不仅仅是两个词语而已。他以自己获知其他真相时的方式明白了自己一旦将这两个词叫出口,他们就会重新塑造他,他就得叫一辈子,而他的不幸经历告诉他,人是会变的,会说一套做一套。他不觉得马克和琳达会这样待他,但也不想去验证。他曾在二年级某一天下午的数学课上壮着胆子叫了数学老师“妈妈”,只是想知道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感觉,听起来怎么样。但因同学们起哄造成的尴尬太尖锐太剧烈,以至于这么多年了,他回想起来还是羞得面红耳赤。
但那只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而刻意叫琳达和马克“妈妈”和“爸爸”会让他的心变得更加脆弱,一旦打破就无法复原,而他不能也不会再这么对自己了。上一次心碎之后,他至今未能重新拼好他的心。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两个空洞,嗖嗖灌着冷风。
但马克和琳达想收养他。当他经过图书馆径直右转时,华金能感到滑板轮子在隆隆作响。不管他叫不叫,他们都会成为他的爸爸妈妈。他知道他们生不了小孩(“跟不下蛋的鸡一样!”琳达曾有一次与所有想掩盖心里最深切的痛苦的人一样,极其开朗地说),而华金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得偿心愿的最后的稻草,自己是否仅是一个结束的手段。
图书馆的某个窗口有一个“爸爸妈妈和我的故事时间!”的标志,华金直接滑着滑板掠过。
华金早就习惯了没有父母。他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傻了。那时候,他还试图让自己变得像他看过的情景剧里的小孩一样有趣且富有魅力。那些情景剧有着愚蠢的笑声音轨,而当孩子们做了什么蠢事,比如开着一辆卡车撞穿了厨房的墙,剧中的父母们也只会叹几声气而已。他五岁的时候就换过好几次寄养家庭,以至于幼儿园都去过三个不同的,这意味着他得以回避那残酷的“本周之星”推选。因为在“本周之星”推选上,小朋友们会谈论自己的家庭、宠物,而这些华金都没有,早在那时,他就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他上十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英语课的老师叫他们写如果可以时间旅行,他们想回到哪个时代。华金写了他想回去看恐龙。这可能是他这辈子说的最大的一个谎。如果他能穿越时空,他一定会回去拼命晃12岁的自己直到牙齿磕得嘣嘣作响,说:“你他妈的在毁掉一切。”他那时候真的很坏,总是向身体里沸腾的暴怒低头。他会翻腾扭动、尖叫呼号直到内心的猛兽暂时满意地退却,留下自己一个人精疲力竭,无可安慰,无可惩戒。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孩子,特别是这个孩子还几乎天天尿床。
8岁的时候,他理解了这其中的玄机。他漂亮的乳牙换成了龅牙和牙缝,胖嘟嘟的小脸也在发育过程中渐渐拉长。他不再有小孩子那可爱劲儿了,而潜在的养父母总是喜欢小孩子,这是不变的真理。
华金知道,可能没人会为他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听老师讲他的艺术天赋多高了。没人曾在四年级的校艺术节上为他在自己的画前拍个照,头顶上是画下贴着的蓝绶带[3];也没人在五年级时载他穿过小镇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有些养父母们尝试过,但金钱和时间都有限,而华金也早就知道了一个事实:如果他不期望,那也就不会失望。
不过他依旧留着那根蓝绶带,将它埋在袜子抽屉里面。从前,他喜欢把它压在枕头底下睡觉,但连续那样做了18个月后,蓝绶带的边缘被磨损了。
华金的人生中没有几次幸运,但他知道其中一个是他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他见过这给其他孩子带来了什么,见过他们如何努力不分开,也见过他们最终依旧被扯开时所受的摧残。他见过哥哥们如何绝望地想让那个只想收养小妹妹的家庭同时带走他们,也见过姐姐们被无情地与弟弟们分开,因为寄养家庭无法容纳三个孩子,有时候社会福利系统也会为了男女分管而拆散同胞。华金非常艰难地守住自己的身心,使自己不被这噬人的潮水淹没,而他肯定没法再支撑另一个人了。所以他很庆幸自己不必如此,很庆幸自己了无牵挂,即使有时候他会怀疑,没了这份牵挂,自己哪一天在人世沉浮中失了踪迹也没人会发觉,更没人会去找他回来。
马克和琳达可能会去找他。华金突然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太阳钻出了云霄,艺术中心出现在眼前。但他决定要拒绝这场收养。
华金曾被收养过一次。
他不会再让它发生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