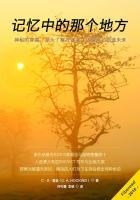运转法诀,诃冬想了想,还是确定引导第一颗银珠中的灵力,顺着赤焰金身的功诀路线在体内运行,然后再散入身体各处,滋养肉身,因为曾经以魔气锤炼过肉身,所以诃冬只是觉得身体有些酸胀,并没有其它不适之感。
“噗~”突然,原本温顺的灵气瞬间变得狂暴,窜出一丝丝赤色火焰,大片大片的细胞被这突如其来的火焰蒸发,这大厅也随之变得炽热起来,从外面看去,诃冬身上出现了一簇簇火苗,头发、眉毛以及一身衣物,都被焚了个干净,最后整个人被火焰吞噬,变成了一个火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大吃一惊,剧烈的疼痛更是让他忍不住低声嘶吼,但他一直咬牙告诉自己,不能慌,要冷静。
慢慢冷静下来的诃冬很快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灵气都化成了火焰,还有部分灵气游走在身体中,恢复受损的细胞,虽然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但离致命还差的很远,了解了这一切他才放下心来。
“辛亏没有用第二颗银珠内的灵气来修炼,否则还不得被活活烧死。”咬紧牙关,承受着这非人的折磨,同时心里也一阵庆幸,要不是有第一颗银珠的生机之力,或者是调用了第二颗银珠的灼热灵气,他今天可就危险了!
虽然痛入骨髓,但诃冬依旧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在一点点增强,比利用镇魔石的气息来修炼要快了不少。
直到灵气在他体内运行了一个大周天之后,身体的疼痛感才缓缓消失,周身的火焰也开始缓缓向诃冬的额头汇集,最终化为一道和当时玉简上一模一样火焰印记,凝聚在他眉心之上。
缓缓收功,睁眼时,看着赤裸裸的自己。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让他不禁有些无语。
“还好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要是跟羊羊在一起……”想到张羊羊,诃冬又陷入了沉思:“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逃出去了没有?”
“原来这玉简是用来储存功法的,可为什么之前却不行呢?”抬手摸了摸额头的印记:“看来应该是神识的缘故!”
“之前的精神力太过散乱,识海也未成型,根本无法储存这些功诀。既然现在已经拥有了神识,那说明戒指中的玉简应该都可以学了。”看了看手指上的戒指,想到里面那一大堆玉简,诃冬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
先取出一套备用的衣服穿上,将戒指中的玉简一股脑全都倒了出来,弄的满地都是,随便拿起一个,就开始探知起来。
“崩山劲:积大地巨灵之气于身,练至大成力可崩山。”摇了摇头,放下手中玉简,再次拿起一个。
“太上忘情录:忘情忘情,断情绝爱……”
“灵虚剑意:……”
……
不知道过了多久,诃冬才将所有的玉简全部看完,这些玉简不仅有功诀,有武技,还有一些炼丹,练气,结界布置等等,每部功法都各有特色。
想了很久,他并未选择任何功诀,而是从其中选出了两部武技。《流光星陨》以及《虚云步》,因为他已经有了蒙尘诀,就算再厉害的功诀,对他来说也是无用的,因为他本身不具任何属性,只有蒙尘诀能修炼。
这两部武技是他结合自身情况选择的。魔宗的身份会使得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追杀,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与人周旋和逃跑的手段,之前与人交手他已经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了,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就只能近身,可是又没有近身功法,就只能被人吊打。
所以,他这才选择了虚云步。云者,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实之间变化无常,是很好的近身周旋手段。而流光星陨,乃是一部遁法。施展之后,燃烧自身生命之力,可瞬间化一道流光,如流星一般,远遁千里。
世间强者何其多,总有自己打不过的人,紧急关头保命的手段还是要有的。因为已经修习了赤焰金身,所以防御他还是心里有底的,何况还有那诡异火焰能用作攻击,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可是所有的远程攻击武技都需要特定的属性与之配合,而诃冬又是一个无属性的人,所以这也成了他唯一的短板。
不过,如果能将这两种武技练好,他也不见得会比别人弱。
让他奇怪的是,这些玉简都不像之前修炼赤焰金身的玉简,被探索了就粉碎掉,好似只能一个人学一般。
越是绝学,学的人就越少,这也侧面反应出了赤焰金身肯定是诃冬手中的那些功诀无法比拟的。
再次将两部武技仔细看了一遍,诃冬才开始修炼,他先学的是虚云步,毕竟这大厅还是太小了,根本不容他练习流光星陨。
刚开始还是比较生硬的,怎么看怎么别扭,东一脚西一脚的,但随着他越来越熟悉后,动作也潇洒随意了许多,直到后来的融会贯通。大厅中出现了很多幻影,整个人飘渺不定,变化无常,一会儿在空中,却又好似在玉柱上,仔细看又觉得是站在那儿根本没动,就好似有很多个诃冬同时在大厅中奔跑跳跃一般。
“这虚云步果然不错。”当所有幻影集中到一起时,诃冬缓缓走出。
“可惜了这地方太窄,不然还可以将流光星陨一起学了。”将手中的玉简放入储物戒,又从里面取出一物。
看着手中的半截青色利剑,诃冬的眼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这是自他父亲的身体中找到的,没有人知道,若不是整理父亲的内脏,他也不会知道。这短剑上只有八个字:“魔门所图,三宗之基。”
看着这歪歪扭扭的八个字,不仔细辨认都认不出来的字,诃冬的心如针扎一般。父亲临死之时还在为三宗考虑,为这天下考虑。他可以想象父亲为了刻下这八个字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为了保护这天下,他忍着怎样的痛苦将这断剑藏入了身体。
“这样做真的值吗?有谁能知道?谁又能记得你是谁?”
抬头望着天花板,诃冬的目光似乎穿透了重重阁楼,层层雾气。穿过了千里万里,穿过了白石城的残桓断壁,穿过了矗立的墓碑土丘,盯着那具已经一动不动的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