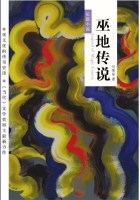爹开车载我回家,在黑夜的路上。
他手把着方向盘,嘴里问着我的近况,我漫不经心地应着。绕进巷里,爹把车停好,不忘一面指点示范在窄巷停车的要诀,一面抱怨自己的手脚因为年纪问题已然不听使唤。
“其实,”爹突然说,“我只是无法承受你们都离开了,没有人留下来帮我。”然后他伏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
我静静地看着爹的后脑,俯身自行囊里拿出斧头,对准他的后颈斫下。
爹的头滚下,掉在自己的大腿上,瞪大眼睛讶异地看着我。
我用脚把没头的爹的身体推出车外,从行囊里拿出一具崭新的躯体,把爹的脑袋安在新脖子上头。
爹在驾驶座有限的空间里试着活动了几下新身体,似乎没有适应不良的问题。我刚想开口问他感受,爹又皱起眉头:“你不明白。我要的不是这个,我需要的是你们。”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这套旧程式真不知足,早知道就不该花钱买新躯体,换套升级软体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