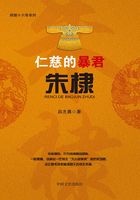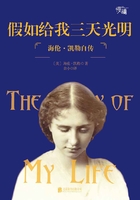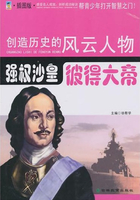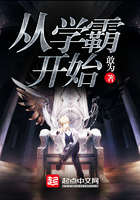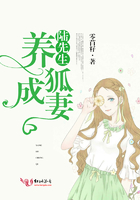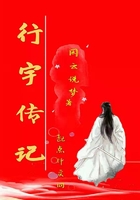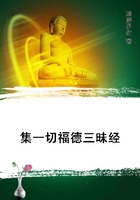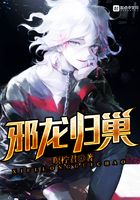“问春风哪里是长相思的地方,太湖似翡翠,二泉流韵长,梅花开罢桃李香啊桃李香,花海里走来谁的新娘,山美水美人更美,无锡是个好地方好地方,诗中的诗,画中的画画中的画,碧水家园胜天堂胜天堂……”
无锡是个好地方,画中画,胜天堂。
如诗中所言:“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回在碧流。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
杨绛就是无锡人。杨氏家族,世居无锡,是杨绛口里的“寒素人家”。杨绛的祖上都是读书人,丝丝缕缕延续着一脉书香。
这个“寒素人家”,不是食不饱饭,着不暖衣,而是君子固穷的意思——一肚皮学问和一身的资质见识,换不来红绿的四人抬和八人抬的呢子大轿,也换不来戴红黑帽子的役夫喝道。能做官的时候不好好做官,能安稳的时候不肯好好安稳,这就是杨绛的父亲,当时大名鼎鼎的“疯骑士”杨荫杭。
1878年,侵华战犯、日本外交官广田弘毅出生,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出生,“疯骑士”杨荫杭出生。
世上事千丝万缕,看似不可能,却又于遥远的时空中往一处相凑编织。
国仇带来家恨,若无日寇侵华,杨家不会败落不堪,杨荫杭的妻子不会早死,杨荫杭也不会怨怒伤身,于新中国成立前夜一病归天。
世上事就是这样,世人如蚁,只看得见眼前的一丝半线,看不见因缘际遇的整匹绸缎。
1895年,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
一次,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开除了带头的一个广东人。洋人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那参与了的一伙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杨荫杭并没有参与,却冒了火,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于是,他就陪着一起被开除了——这副骨头是有多硬。
此后留日求学,之后回国,做编辑,做撰稿人,授课,和别人组建励志会,办杂志,“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
暑假回无锡,他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得罪族人。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该枪毙。”
保守派就是这样。他们不肯接纳新的理论、新的行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们在他们的舒适圈里沉迷,哪怕这个圈已经越来越窄,束缚得他们行不敢行、动不敢动、说不敢说、想不敢想。他们身上缠着一圈圈的麻绳,却还自以为是地在这些麻绳上寻找安全感。
此后杨荫杭再次出国,留日获法学学士学位,留美出版硕士论文《日本商法》。
唐须嫈与杨荫杭同岁,二人于1898年结婚。
据说唐须嫈曾在上海的务本女中读书,这样时间就有了交错点:1902年10月24日,务本女塾开张,这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那么,唐须嫈应当是在和杨荫杭结婚后去读的书,她和自己的三小姑子杨荫榆曾经是同学。
唐女士大约是在旧式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旧式女子,温婉和悦如同寂静夜晚的星空,如今学得了新知识,好比天角斜斜地又出了一弯眉月。
论学问她于杨荫杭是不及万一的,但如今识文断字,和杨荫杭有了对话的平台。她不倔强,夫唱妇随,夫说革命就革命,夫说出国就出国,夫说回来就回来,这样的夫妻搭配,羡煞多少娶了不识字的小脚太太的民国才子。
据杨绛回忆,她的父母好像老朋友,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谈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杨荫杭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妻子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
这个做丈夫的了不起,他就是这样一个天性自由而追慕平等的人,觉得天底下人人就应当是你与我平平而坐、平平而起、平平而话、平平而视。因此当他把这样的想法用到社会上去,和当时那种尊卑分明的氛围不合,于是他就成了革命党、少数派,要被人围而剿之,不得已逃国离家。
杨绛是幸运的,父亲磊磊如山中石,母亲温婉如花下苔。
杨绛的万千花叶,以无锡为根,在北京生发、蓬勃。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其时,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
杨绛原名季康,小名阿季,排行第四。和前面的三个女儿相比,她个头最矮。杨荫杭爱猫,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见过小短腿的猫吗?短短的小腿,软软的小爪,白白的皮毛,大大的眼,走路摇摇摆摆,好可爱。
小阿季就有这般可爱。
小阿季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旧王朝如破城堡,一朝被疾风骤雨吹打,倾倒坍塌。不久杨荫杭辞职南归,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做律师,并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
当时,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把他的名字也列上去。他马上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自己对这个军阀没有欢迎的意思,被人笑不识时务,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被浙江省长屈映光挟私告状,大总统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此后,杨荫杭又被调到北京,小阿季跟着爸妈又回了北京,小小年纪,像只小猫,被抱过来抱过去。
阿季5岁开蒙,就读北京女师大附小,那时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师大工作。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凡是读过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的,都晓得这个名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杨荫榆赴日留学,学成回国,受聘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之后又赴美留学,回国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惜乎!她不顾国情,不体察年轻学子对自由、民主的热情与渴望,一味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强调秩序、学风,不许学生参加甚至过问政治运动,且排挤和她意见相左的教师。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女师大刘和珍等学生遇难。鲁迅哀痛提笔,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女师大学潮日炽,学校迫于压力,将杨荫榆免职。
有人说她就是一个守旧派。刻板、僵化、条条有理,像大理石的纹路,每一条都硬邦邦,与自由、热情、散漫不羁、花开遍野是天敌。
她早年婚姻不幸,此后一直独身。热闹是旁人的,自己是游荡的孤魂野鬼,心里又硬、又冷。
杨荫榆是治学的料,低情商,要做管理,根本不成,于是她失败了。可她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她只是太孤僻。
杨荫榆是1884年生人,那时才三十来岁,也正青春,也正好,心里也还没有长了蒙着雪的连天衰草。
孤独这个词,像圆圆的小水晶,透明,阳光一照,璀璨,却是硬邦邦。总是有人说自己向往孤独,也有人标榜自己安于孤独,那是因为他们与之和平相处的,不是真孤独。
真正的孤独——庞大、空虚、冰凉、寂寞、要人命。回头想想,女儿死后,丈夫死后,杨绛这么多年,这么孤独,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一次杨荫榆带着来宾进饭堂参观,小学生们正在吃饭,全饭堂肃然。杨绛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
杨荫榆从身边走过,俯耳说了一句什么,杨绛赶紧把米粒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杨荫榆和杨荫杭形容这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上去都和阿季相像,一段白脖子,两条小短辫;她们看见她捡吃了米粒,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捡来吃了。
“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杨绛后来回忆说。
因为是杨荫榆的侄女,当时阿季也被追捧。
女师大的学生爱带着她玩,比如打秋千;办恳亲会要演戏,又让她扮作戏里的花神:小牛角辫盘上头顶,满头插戴着花,衣裳贴了闪闪的花片;开运动会,又叫她围绕着跳绳的大学生扮卫星,绕着大女孩跳跳蹦蹦,小身体真灵性。
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执政,杨荫杭又做了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却因坚持查办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被停职审查。硬骨头碰上铁壁墙,杨荫杭愤而辞职,未等照准,即带一家人回了无锡老家。
阿季当时在读初小三年级。因房东是满人,她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花盆底鞋的满族妇女。穿这种鞋走路,前倾后仰,蛮好看。
杨荫杭有一次问阿季:“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一会儿,说:“要!”
但是现在她要离开这个有人穿高底鞋的大城了。小娃娃不是行李,能随便被拎到东拎到西。本来还高高兴兴在院里玩,忽然就被大人带去了火车站,小阿季路遇一个同学,恨不能叫这同学捎话给班上,说“我回老家了”,苦于不十分热络,开口闭口犹豫间,就错过了。
月台上人头攒动,来给杨荫杭送行的人很多。
杨绛小小年纪,离愁已如早春草、薄雨花。
一家人舟车劳顿,重返家乡,在无锡的沙巷租了一处房。厨房外有木桥,过了桥才是自己家的后门,不出家门就能站在桥上,看船只来来往往,穿来穿去。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一间大教室里盛着四个班级,八十个孩子挤作一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一个孙老师。
孙老师剃光头,用教鞭打人,学生绰其号曰“孙光头”,他把“子曰”解作“儿子说”。
女生们在卫生间的墙上画孙光头的像,对着拜,要把他“钝”死——唯有神佛先人受得起人的朝拜,若是觉得一个人不好,受不起人们的礼拜,结果人们拜他,就会把他拜得要倒大霉。
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胡村小孩吵架,先是口角,接着打起来,也有不打的,就朝对方拜,因为被拜是罪过的,要被拜杀。当下被拜者很惊慌,赶快背转身去表示不受。抑或两个小孩离得远远的,隔条大路,各人依着自己的家门口,你拜我也拜。再敌不过,则去告诉对方的母亲。
可见礼拜是非常庄重严敬的事,不当拜的人受不起人的拜。
不过孙老师从不打杨家的孩子,也许是觉得这是做官人家的儿女,也许是因为这些小儿女很乖。
杨绛和女小伙伴玩官打捉贼,她照依北京的惯例,拈得“贼”字起身就跑,女伴扯住教她静静地坐着,莫要教人瞧出来。拈到“贼”就“逃快快”不是“女老小”的事,是“男老小”的事。女孩子只要“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要不就是“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这个大约也算是封建社会的礼教,女孩子要文静有礼,不比男孩子活蹦乱跳。
终其一生,杨绛都对这一段孩提时光念念不忘,古稀之年还时常会不知置身何地,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无锡大王庙:“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彼时彼处,少忧患,没有懂得世味如纱。而后来,人情纸薄,流离丧乱,不如犬鸡。
杨荫杭病了。
因满腔忧愤,再加上那所房子的几个租户又都得了伤寒,内外夹攻,焉得不病。
他的病严重到医生拒绝开药方,家里的顶梁柱要折了。
那夜,已经很晚,大家都不睡,杨宅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来探病的人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
唐须嫈请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来,华实甫“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没想到发生奇迹,杨荫杭居然一点点活了过来。唐须嫈对丈夫无微不至地护理都被杨绛看进眼里。此后杨绛对钱锺书的不离不弃,照顾得细致入微,根在这里。
一家人应劫又逃劫,杨绛常觉幸运:“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杨荫杭病愈后张罗另租房屋,有人介绍了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杨绛跟着父母一同去看。
她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她并不知道钱家人当时也租住在这幢房屋,当日也并未和钱锺书相遇,两个人只知各自前情,哪晓将来后事,好比月亮的半明半暗,只是月老一人心照。
命运原本就没有偶然这回事。
粉墙黛瓦,方窗镂花,小河流水,无锡是个好地方。有杨绛和钱锺书这一对互不知情的小儿女,更叫它像是吞了两颗夜明珠,在光阴深处明明烁烁地放光。
小阿季的大姐当年上的是有名的上海启明女校——一所教会学校,1930年改名启明女子中学。这是所有名的洋学堂。
如今,大姐毕业留校,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去启明读书。三妹还好,可四妹,也就是杨绛,虚岁才10岁,实岁数8岁半。
杨荫杭是西式人物,重视子女教育,当然不会反对,但母亲心有不舍。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对杨绛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
她再次问:“你打定主意了?”
阿季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
小娃娃自己就做了主张,母亲也就许了这小娃娃自己做主张,没有再说什么。
阿季是开明家庭里的小孩,可越是这样,心里越难过、越不舍。
阿季眼泪簌簌地流,幸好屋里昏暗。她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哭,如今却是吞声饮泣,不愿叫母亲知道。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结束了。父亲沉疴刚起,差点一家离散,她晓得了忧愁惊恐,以前是一株长在无忧河畔的无忧花,如今下了凡。
临走,妈妈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圆。杨绛曾回忆此事道:
这枚银圆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圆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圆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
天暖了,要穿单衣,她把银圆拿出来交给大姐收藏时,已被自己捂得又暖又亮。
要说她此时就有了什么坚定信念,或者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那是附会之言,为尊者添花罢了。其实,她就是家教使然,耳濡目染: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1920年2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1920年2月,杨绛离了大王庙,到了启明,她的心里就萌生了这样一股子自豪劲,一个劲在心里跟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们显摆:“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学习外语的学生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启明生活正式开始时,她却被更新奇的事情吸引了,忘记了炫耀。
刚开学,学生返校,只听得一片声的“望望姆姆”,意思是“姆姆,您好”(修女称“姆姆”)。管教学生的都是修女。新入学的学生们纷纷猜测姆姆们高高的帽子到底是几个,那么厚的裙子到底是几条。
一次,天主教徒上山瞻礼,杨绛被准许同行,跟姆姆睡在一起,这下子可被她知道了:姆姆们戴着的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是三条,并不是之前她们猜测的那么多。
启明每月放假一天,称“月头礼拜”,本地的学生可回家。其余的每个星期日,学生们就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叫作“跑路”。
这里管绘画叫“描花”,学描花要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弹钢琴则叫“掐琴”,这个动词用得真奇怪,为什么不叫“敲琴”呢?
这里用的语言好奇怪,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作“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作“没志气”,淘气的小孩称“小鬼”或“小魔鬼”。
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报告”。
小鬼们调皮,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放行。但监守的姆姆自己在看书呢,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
小阿季大约那时还梳着羊角辫,乖乖的小模样,“问准许”会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不知道是听不清还是怎么样。几个娃娃互相错开一些时间去“问准许”,就都会被准许,几个小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既开明又有纪律,既有纪律又不严苛,杨绛在启明学校的生活也算是无忧无虑了。
启明是教会学校,杨绛虽未受洗入教,但是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她学习英文和法文,想着“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领取教会学校里老师给予的“圣餐”。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古老的《圣经》,大姐的书桌上有一本,她在桌上写作业,一时好奇,囫囵吞枣地看,觉得里面的名字好怪。
多年后,她的美籍女教师哄她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是《旧约全书》。
我没有宗教情怀,有人拉我入佛门,我亲近了佛教十来年,却始终做不成佛教徒;有人拉我信基督,我也买了《圣经》读,白亮绵密的纸张在深夜里给我的安慰,强似它里面的内容。但是有些话又教我读来深刻入骨——“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度过的千年,是你的一声叹息”……
杨绛也是如此吧,虽无宗教情怀,但会在深夜里想起那些充满哲理的话。
没有宗教情怀不等于不体认万物有灵,杨绛一生未入教,却穷尽一生,直到百岁,仍旧在认真地研究灵魂。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她的信仰就是从启明学校开始的。她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
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借此维护统治的力量。其实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
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我们好像就此能够摸到一点杨先生的脉门,她原来信仰灵魂不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能够在女儿和丈夫相继辞世后,以还算平静的姿态,度过余生漫漫数十载。那么,她是不是想着,苦熬过数十度春秋,离开这并不繁华美好的人世,可以于遥远的世界尽头,和女儿、和丈夫,重新笑泪相拥,痛诉离情?
一到月头礼拜,本市的学生都换上好看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小阿季离家远,回不去。管饭堂的姆姆可怜这些小鬼,把饭堂里吃点心时没吃完的半蒲包“乌龟糖”送给他们,直吃得他们舌厚,嘴酸,可心里还是苦。
大约过了几个“月头礼拜”,一天,大姐把阿季的衣袖和裤腿拉得整整齐齐,带着她和三姐走出校门,乘上电车,到一个地方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
当时杨荫杭病愈后,在这里当主笔。
父女们逾月重逢,杨荫杭高兴地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
“吃大菜”在顽童的世界里是“被狠狠训了一顿”的意思,不是真的吃大菜。真的大菜阿季可没吃过。
杨荫杭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他们步行,一路上小阿季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小手盖在爸爸哔叽长衫的袖管里,莫名地安心。
进了西餐室,杨绛和爸爸对面而坐,第一次用刀叉,爸爸怎么吃,她就怎么吃,小心翼翼。西餐里的汤是要一口气吃完的,她不知道,便吃吃停停,服务生看她停下,伸手想要撤汤下去,哪料她又端起来喝。如是几次,服务生只好作罢。
就因为这个,回家路上被爸爸和姐姐笑个不停。
做申报馆主笔的同时,杨荫杭又重操旧业,做律师。他一向觉得世上只有两种职业值得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
当今做律师不易,勤勉敬业是基本要素,每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只是起步。在那个年代当律师更不易,有良知的人在黑暗的社会里都不易。杨荫杭又因为做律师得罪了人,家都不稳。
他一向反对置业,因为经营家产耗费心力,一不留神自己做不了家产的主人,反而变成家产的奴隶;子女因为有了家产,就会“吃家当”,变成不图上进的废物,倒不如没有家产,也许可以有所作为。
理是这个理,只是莫说过去,如今能做到的有几位?
盛世家族往往“百年而斩”,不可能永远流传,就是因为吃老本的不肖子孙祸祸了基业,也祸祸得自己无本事,无志气。
贾府里,宝黛闲话,黛玉道:“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宝玉这个小子,还不如黛玉有志气。
杨荫杭见得明白,对孩子们说:“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是租赁的房子不稳定,做不得律师事务所,所以他还是决定买房子。恰恰苏州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
杨绛回忆道:“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全宅共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
杨荫杭用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破宅院,拆的拆,修的修,扩大后园,添种花木。屋宇太老,院子阴湿,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孩子们捉多赚多。
这个一看就是海派做法,他家的孩子们大约没读过什么《二十四孝》之类的书,但按西法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也个个孝顺。
所以国学是好的,也是对的,但不是唯一。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教人为善,但它也不是唯一的宗教一样。中也好,西也罢,能够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才好。
没多久,虫子都被捉尽,孩子们赚的钱都存在妈妈手里,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杨家定居苏州,杨绛也结束了她的小学时代,升入苏州振华女校念中学。
那年她16岁。
杨荫杭也要子女“有志气”,他从来不重男轻女,只重视品德修为。
他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假如这些孩子对某一件东西心里“种草”,想要得不行,他也常常只是说:“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言下之意一是,你要得过来吗?所以,要学会取舍,看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可要可不要的,哪些是完全不必要的;二是,想要的东西,你要自己去努力得到,不能伸手索取。
无论哪一种,对于孩子们都是极其良好的心志引导,胜似如今的父母们对小孩要一奉十,搞得小孩看见什么都想要,不给就哭,再不给就偷,就抢,就耍诡计。
世界那么大,你什么都要,你拿什么去盛?当父母的先要教小孩管束欲望。
杨荫杭的“疯骑士”之名只是庸人给他扣的帽子,骑士之名却恰切,急人之难,急公好义。在家里他一点不疯,倒是“凝重有威”。钱锺书对岳父的印象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家的孩子们有福,有一个好父亲。
女儿天生跟爸爸亲,在家的时候,爱拣爸爸写秃的毛笔去练字;早饭后,给父亲泡一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给剥皮;吃干果,她给剥壳。
饭后歇午,孩子们都作鸟兽散,爸爸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于是她就陪在午睡的父亲身边,静静看书,不出声。
冬天她给父亲屋里的火炉添煤,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大家庭里的女人最不好做。男人可以以公务为名,对家务少管甚或不管,女人却逃不得。大人孩子一日三餐,四季单棉,床上铺什么单子,地上铺什么砖,冬天烧什么柴,餐桌上谁爱吃甜谁爱吃咸……杨绛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忙人。
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母亲叫人点上个洋灯,阿季哭了,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她是识得这个“情”字了,心里感动地哭。
唐须嫈还有两个小姑子。
“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不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大姑子、小姑子最是夫家难伺候的生物,所以《红楼梦》里,嫂嫂李纨会戏嘲黛玉说:“真真恨得我只保佑明儿你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
杨家的两个小姑子算不上千刁万恶,但也是骄纵的大小姐。她们既不关心家事,也不分担辛劳。
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唐须嫈是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对这个东西倒还喜欢。于是她的孩子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就把一大包栗子干光了。二姑母没在意,三姑母杨荫榆却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杨荫榆看着嫂嫂整天忙里忙外,却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所以杨家的用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工。这个辞了,就要另找下一个,下一个谁知道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手脚干净不干净,干活利落不利落?找一个好的用人也是难的,而这又是唐须嫈的活。
父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读书、自立自强的样板,母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样板,小阿季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杨绛,成长为钱夫人,成长为杨先生。
唐须嫈是上过学的人,若难得有闲,做一回针线,也会有心情从针线筐里拿《缀白裘》来看。临睡又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新小说她也爱。
有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
杨绛笑着说:“她就是苏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