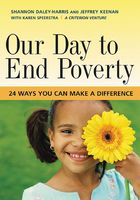苏子仪呼唤道:“桂华姐,救救我。”
“你就是个扫把星。”何桂华扔下这句话头也不回的走了。
眼前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苏子仪挣扎着要站起来,伸手要触及到她:“李嫂……”
苏子仪摸到了粗壮的臂膀,仿佛是一淳厚男声:“姑娘不怕,我带你去找大夫。”
苏子仪清醒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旁边还坐着一个陌生人,屋外是雷声风雨声。
空气中弥漫着茅草的陈腐发霉的味道,她的身上很不爽利,湿漉一片。
偶然微微睁开眼睛,仿佛受到极大的惊吓,一张黝黑的皱纹遍布的脸,不可谓不丑陋,可是眼睛明亮清澈,笑容也很淳朴。
苏子仪神思迷迷糊糊的又昏睡过去,不知几时,身上的水渐渐干了。
窗外的雨声停了,苏子仪昏昏沉沉的,这才惊觉自己高烧不退,因淋了雨着了风寒,状况不好,不知几时清醒几时昏睡,就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几时,忽而又雷声大作,苏子仪非常害怕,又兼有对家的思念,黑洞洞的室内压抑的可怕,窗外雨又开始下起来。
这一次,映入眼帘的是阿牛明静双眸,苏子仪不解:“怎会如此?怎么会是你?”
阿牛道:“不是风寒那么简单,你这是中毒了。”
苏子仪的唇边溢出一抹虚弱的自嘲般的笑容:“是……”
阿牛非常担心的样子:“她们下毒了?”
苏子仪这才细细打量阿牛眉头间的纹路,他皱眉的样子非常严肃,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他确实是在关心着她。
苏子仪不停的干呕,阿牛非常担心也别无他法,干呕的同时,苏子仪对她所处在的环境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乱,非常之乱。
阿牛准备好热汤汗巾,苏子仪感激的接过,身上的粘腻感终于消减下去,额头开始发烫,刚刚淋雨感染风寒,加上刚刚服用毒物,情况非常不好,在床上躺着,浑身都非常疲惫,神识不清晰,只恍惚听见门开的声音,身边有人在低声交谈,听见粗鄙的男声。
“拜托先生了。”
“你没钱,还请我来作甚?”
“摆脱先生通融一二了。”
“滚。”
脚步声踱出门外,门吱呀一声关了,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不多时,阿牛又进了屋,不知刚刚那人是谁。
苏子仪忽然觉得有一丝泄气:“阿牛哥,别管我了,他们都不想管我,你这又是何苦呢?”
“横竖都是一条人命,你让我如何不管。”
“看来,阿牛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呢,之前要黄金的时候可是让人误会。阿牛忽然陷入沉默。
不知多时,阿牛在床边坐下来,换了苏子仪额头上的巾子,小心翼翼的照顾苏子仪。
傍晚黄昏一直睡觉到天黑下来,苏子仪仿佛梦见身处于兖州家中从小睡的房间,一切装饰如旧,奈何房间太暗,怎么点灯都照不亮,心里萌生出思家之情,想到再也无法回去了,悲到深处五脏六腑都疼起来。
身体虚弱神思萦绕纠缠,忽而又聆听到许多人声喧嚣。
好像置身于一座佛寺之中,耳畔有流民的声音,战马的嘶鸣。
天寒刺骨,一切好像都很真实。
苏子仪推开门之后,看见了熟悉的场景。
那是十三岁那年,北伐失利,敌军挥师南下攻陷兖州,他们这些孱弱之人随着军队逃往南方的那段日子,战火蔓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不过这也是她出嫁之前仅剩的一点安乐时光,虽然颠沛流离,到底是自由之身,没有受到那般严厉的管束,没有浮沉在那权势的漩涡中心。
之后她进入广陵王府,到入宫,十年的时光,终是蹉跎了。
寺庙里满是流民,非常嘈杂,她和阿湄与几个侍卫在一起躲避灾祸。
光影重叠的院廊之后间缓缓走出来一个身影,竟然是他。
崔承嘉踱步到她的身前,他眉眼间俱是温柔,嘴角挂着微笑。
苏子仪心内大为震惊,出了一身冷汗。
疑惑于他并不是唇红齿白模样,唇色略显苍白,也不如前世最后见到的那般淡到无色,整个人看上去带着风霜侵袭的憔悴,目光却很坚定、柔和。
与他竟然还有这样的一段时光,都快要遗忘殆尽。
苏子仪知道,这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出任广陵郡太守,安抚流民是先下关头最为紧要的事情。
崔承嘉在她的面前站定:“苏小姐可有什么难处,可以和承嘉说,子卿托我好生照顾你,如今我守着此处,一定不让你出任何差池。”
苏子仪嗓音透露出敷衍:“好。”
他就那样站在他的面前,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近,仿佛触手可得,又仿佛很远很陌生,阻隔在他们之间的是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寒冬腊月的,梅花已经开了,旷阔院子里盛开着香气馥郁,与崔承嘉说着话,二人朝梅林深处走去。
苏子仪突然试探般的开口问道:“等海内安定了,你是否就可以娶我了?”
前世她说的正是这句话,只不过那时候是怀着期许的,如今只剩下绝望。
崔承嘉避重就轻道:“待回去之后,苏将军自然有安排。”
如同预料一般,崔承嘉的回答似是而非,眼中有阴翳,他没看她。
苏子仪悻悻然道:“你也别诓我了,我已然知晓。”
崔承嘉停下脚步:“哦?此话怎讲。”
苏子仪直视崔承嘉的双眸:“等海内安定了,父亲一定会为我择一门好亲事,听说承嘉认为广陵王梁毅是子仪的命中良人,承嘉说子仪这番话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