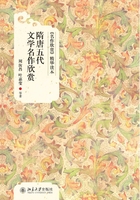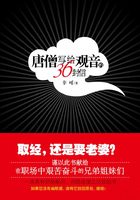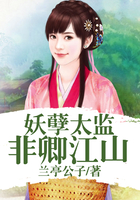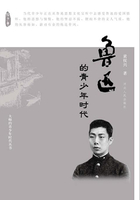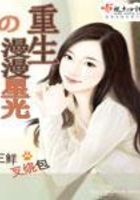就“人文”而言,亦可分而论之:“人”之自身始终都会存在“身心”问题,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关于“文”,自古就有“文心雕龙”宏论,包括了文心化文、细论文心以及文心雕人、文心外化诸说。时至现当代,这种文论思想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早在1934年民国时期就出版了《文心》一书(叶圣陶等著,开明书店),即使在海外华文文学界,也通过建立卓有影响的“文心社”和“文心”网站(www.wenxinshe.org)向伟大的“文心说”致敬。总之,人与文休戚相关,尤其是人心总与文心相关相通。
在人类的思想史或心灵史上,大致经历了“神本”“人本”和“命本”三个阶段:人类历史上经过漫长的“神本”时代,进入了“人本”时代并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然而,如今地球村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危机,人们通常将其视为生态危机,从自然生态危机包括天人关系失衡,到精神生态危机包括信仰严重缺失,都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丧钟为谁而鸣?”生命往往落入险境才会逼出更为强烈的求生意识,文化经过反复磨合才会从“神本”“人本”逐渐演进至珍重所有生命的“命本”境界。
中国现代文人创造的“新文学”便涵容“人的觉醒”和“新生命的憧憬”,从中也折射出他们的人生之梦。揭露“吃人”的历史与现实,这是鲁迅的文学主题;歌唱“凤凰涅槃”的悲壮与欢欣,这是郭沫若的文学主题;崇尚“自然人生”,展示“美在生命”,这是沈从文的文学主题……而他们共同的主题则是关注人的现代命运,促进现代文化的发展!
于是,中国有了真正的“新文学”!有了“古今中外”化成的现代文学!
方东美曾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在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1]只有应运而生的新的生命才能孕育出新的文学,而新的文学反过来也培育了新的生命。只有坚韧不拔地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和个人,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也才会创造出与旧文学迥然有别的新的文学。“人”的现代化与“文”的现代化在生命更新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这实际是几代作家共同的信念与追求,自“五四”以降的中国新文学,是我们民族与作家个人生命之树上绽开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我们瞻仰着新的生命所创造的文学胜景,也为新文学的屡遭劫难却仍生生不息而感喟不已。但我们尤其怀念那些直面人生、勇辟“崭新的文场”的闯将们,是他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鲁迅《论睁了眼看》)生命文学,为后继者做出了榜样。今天的我们,应该以生命的名义,向他们致敬!
世间有了生命,有了人对新的生命的向往与追求,才会有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才有了“热爱生命”的赤诚,也才有了“创造生命”的美好。而这赤诚,这美好,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生命机制”。然而真实的生命,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的生命之谜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具有最大的魅力,也具有最大的魔力和迷惑。倾向于“神学”或“兽学”(动物学)方面的探讨,就表明这魅力与迷惑是同样的巨大。将人仅仅单方面理解为理性人或感性人、社会人或个体人、“神人”或“兽人”显然都是偏颇的。真正完整的“生命哲学”或生命美学理应是对“人”的系统而辩证的把握,而不是仅仅关注人的本能、潜意识与非理性,或仅仅关注人的智能、显意识与理性,也不是先验地、机械地将某个方面始终视为根本的、主要的方面。相对于许多实际上是肢解了人的生命的理论,作为全息观照性质的“人学”的文学世界则更贴近人的生命真实。
注重从“生命的真实”以及相应的“心理的真实”这一基点上来看待文学,这使我们意识到了心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人生的什么景观或体验,只有进入具有审美创造功能的“心理场”,才可能转化或结晶为文学作品。正是这“心理场”将“对象”“作家”“读者”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要探讨中国现代新文学,就不能不密切注意“新文场”与“心理场”的内在联系。新生命的心灵化是创造新文学的关键,相应地,我们也只有从心理场的角度才能寻觅出新文场的矿藏。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心理分析是带有广义性的,与弗洛伊德创设的狭义的心理分析相关却并不相同。广义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对生命现象中的性、梦,生、死或潜意识的探析,但同时又关注着文学中的文化心理、时代心理、民族心理、阶级心理与个性心理等,积极借鉴各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来达到对文学现象进行心理分析的目的,通过带有综论性、比较性或透视性的心理分析,从而对新文场中的创作心理、对象心理与接受心理有所揭示。而在具体的但并非系统的分析中,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新文学的作家们对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总是那样倾心地向往,热烈地追求,无论是经受了多少痛苦与困惑,都没有失掉这种心气,都没有窒息这种心声。深情而热烈地呼唤着新的生命,这是新文学最为激动人心的主旋律。而“新文学”也与“旧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文心”方面依然有古今相通的地方。尽管笔者主要关注的是“新文学”或现代作家的“文心”,却也要在古今中外连通的视域中加以“窥探”。由此,便有了本书的构想。
《心事浩茫连广宇——作家“文心”窥探》,借用鲁迅先生诗句为本书的主题,将作家们的浩茫“心事”与存在于人之内外的“广宇”联系起来,也参照文论界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内宇宙”等观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创作,从作家到读者,以广义与狭义的心理分析为主要视角,对中外作家尤其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内宇”,结合其文学文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力求得出能够贴近真实且能激活思维、耐人寻味的论断。既从世界学术视野关注“五四”以来文学现象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文化心理,也密切关注具体作家创作心理以及文本潜蕴的意识、无意识内容,还努力从文学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拓展,致力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及“文艺性学”的建构;既关注作家们“心事浩茫连广宇”生成的人文现象,更追求“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心理窥探或心理分析。笔者秉承“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学术理念,坚持“大现代”的人文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长期追索并严肃认真地探讨不同层面人性,包括本能与文学的内在的复杂关联。同时注重结合当代实际人生体验和当代学术思潮来审视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读者所涵容的心理世界,由此体现出强烈的“当下关怀”或学术当代性。其鲜明的当代性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文学发展的当代性要求有选择性地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对象,并不苛求面面俱到;二是在具体的文学历史现象研究中,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出具有现实指导性意义的学理根据和经验教训,给当代文学的发展以有益启示;三是运用现代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透视作家“文心”及其嬗变,在现象分析、个案透视和理论探微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性强且各有侧重、互有呼应的深入研究,并给出了一些新的学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