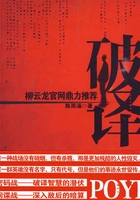“人才难得”——邓小平与毛泽东
一
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也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4年以后,二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这种检查当然是全面的调查和评估,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外,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是确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否定在瑞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当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了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邓小平同处一城,彼此接近,但是时间很短。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老百姓十分拥护苏维埃。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在当时苏区党、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同志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但邓小平所受处分之重,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做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在当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适逢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日趋紧张,对毛泽东或明或暗的指责以及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不久就一起湮没于黎川和广昌前线那震天的枪炮和喊杀声中了。
对苏区的这场党内斗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以颠倒的方式反映了其基本面貌。“小组织”和“派别活动”当然是子虚乌有的,而邓小平等人从思想到行动皆站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则是事实。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清楚。
1934年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中仅存的人物。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二
1943年10月以后,延安整风进入第三阶段。研究历史,论说功过,必然要涉及对人物的品鉴和事件的澄清。建党以来的是是非非和人事问题的种种纠葛逐渐露出端倪。
1943年11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是把邓小平当做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重要人物来维护和褒扬的。
无独有偶,同一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就当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斗争”作诗一首,抒发感慨: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至此,“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遂有定论。
整风结束时,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批判“左”倾错误路线方面的认识已趋一致,重用一批德才俱佳、忠实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的良好环境已经形成。邓小平多年与刘伯承领兵在外,披霜蹈雪,艰苦征战,加之有着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不但毛泽东倚为干城,在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中也树立起了声望。
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没有那种思情远举的文人气质和高古奇谲的诗人心态。他是一个胸有丘壑、深藏不露的实干家,胆大多谋,为人严谨,做事干练,分析问题切中要害,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恰恰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战争年代,他把邓小平与年长12岁的刘伯承放到一起,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以说毛泽东知人甚深,用人得法。从组织山地和平原游击战到开展反顽斗争,从挺进中原到指挥淮海战役,从挥师渡江直至进兵大西南,邓小平负责的工作是毛泽东非常放心的一个方面。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邓小平都能心领神会,分析情况,掌握政策,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圆满地加以完成。尤其是刘邓率军渡河南下,任务艰巨,在中原拖住蒋军劲旅,减轻陕北和山东战场我方的压力,更显出了栋梁之材的本色。所以,当淮海战役打完以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由中原局第一书记调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原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则任第二书记。这除了有统一事权,便于开展南下工作的考虑之外,也表明毛泽东信任之专。
邓小平的思维特点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38年,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讲过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这句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邓小平思想的精微。他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一连四五年,毛泽东常常提到这句话。
发源于早期的耳濡目染,并结合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悉心研求,邓小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将之作为得到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此他也欣赏能同他一样掌握这个法宝的人。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深深契合了毛泽东。邓小平长期主持一个战略地区的总体工作,因此他把对各类情况的全面把握当作一项基本的功夫。从战略到策略,从对敌到对友,从图舆战阵到兵民用度,无不了然于胸。真实的情况掌握了,实事求是的前提就具备了。这样,邓小平作为中原局书记反映给毛泽东的情况、所提的建议就能做到言之有物,参考价值极高。毛泽东非常爱看邓小平的报告,多次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如邓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对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十个问题的答复、1948年6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等,为中共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对此视之为宝。他的许多思想和著作的形成,邓小平有着独特的贡献。遇有疑难,毛泽东亦咨以函电。
此外,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作风也十分满意。邓小平生性恬淡,不喜交际,这与毛泽东的以诗文会友、周恩来的广结各路名士有很大的不同。战争年代,邓小平军务繁重,鞍马劳顿,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忙于党政庶务,即使偶有闲暇,也习惯于一个人独处静思,对于如何与人交游似乎无所用心。他对同事相待以诚,相忍为公,对下属也是约束极严,向来不肯假以辞色,对拉山头、搞宗派深以为戒。其组织纪律性和修养功夫如此之强,令毛泽东十分放心。这些特点在邓小平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高饶事件”发生后为毛泽东体察得十分清楚,也更以为难得。
因此,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
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时,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当场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向邓小平也是向全场解释:“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
接下去,毛泽东不厌其烦,反复表示要为邓小平“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毛泽东还说: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几番“比较”,爱护、褒奖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集中了党中央的共同看法。9月2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诙谐恣肆之中则另有一番深意: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对邓小平的赞赏,毛泽东对一些外国领导人也曾流露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不断摸索,大胆实践,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以其对人类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特征的深刻认识,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这个过程,充满了一种神奇、瑰丽和惊心动魄,使无数置身于其中的优秀人物坚信这项事业的伟大与神圣,也坚信其代表者毛泽东的正确与英明。邓小平便是其中的一个。1943年,他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道:“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剀切直言:“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捍卫和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是以毛泽东本人执行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路线为基础,以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盘剥和压迫,尽快走向文明和富裕为目标,这也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能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之共同前提。
三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被罢官。
当时,邓小平因腿骨骨折留在北京,没有亲临会议。但凭着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他敏锐地感受到党内愈来愈浓重的不正常气氛。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明显,开始疏远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他也一度强调民主,强调实事求是,但“左”的提法和错误决策时有发生。而邓小平更讲求实际,思想和理论上能摆脱某种原则限制而进行灵活的多向思考,因此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越来越不一致。
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要退居二线,不过问日常事务,以专心研究理论、政策。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这个提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通过。从此,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邓小平任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性工作,站在一线。于是,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当然是无所顾忌的。
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毛泽东还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泽东的叙述很生动,尽管是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可以看出毛、邓二人在工作关系上的疏远。
更为关键的是,毛、邓之间的思想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见解上。如在经济政策上,在文化方针上,二人之间都存在分歧。
这种矛盾有一个积蓄的过程。
1960年底,毛泽东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所震动,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着手解决农业问题。1961年他主持制订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但是,他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1962年,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包产到户,中央常委里的同志有的支持,有的也不予反对。邓小平的话说得更明白。他在1962年7月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在7月2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时隔5天,他又对共青团一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代表说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
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邓小平态度非常积极。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的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不留尾巴。4个月之内,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工作做得干净利落,邓小平的话讲得同样鲜明、深刻。在1962年2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这几年,在干部工作上,我们有些缺点,特别是几个大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处理不适当的。总之,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干部状况不稳定,一批一批地变动,就不是好现象,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要引起警惕。”
在职权范围内,邓小平对文化、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11月,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几年,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要大胆提拔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是共产党员但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盛极一时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1965年3月,他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他还提出可以演帝王将相,写历史剧可以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这就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批示和主张明显不同了。
不仅仅是思想倾向上的分歧,邓小平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也越来越让毛泽东感到不习惯、不满意了。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邓小平与自己离心离德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认定是“刘邓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被“打倒”是“必然”的。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仍能区别对待。
1980年10月,邓小平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在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待老干部的态度时说:毛泽东“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毛泽东阅后,挥笔写下了一段批语:(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有一个基本估计:没有历史问题,有着被错误路线打击的经历;抗战以后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作战有功;在中苏论战中持强硬态度,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在锋芒直指刘邓“资反路线”的同时,对二人作了区别。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出面干预,才未能得逞。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创痛,出于种种考虑,他让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带着他在南昌“将军楼”小院积郁三年的思考,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重新回到了国务院领导岗位,并于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为给邓小平以重任铺垫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转而对邓小平说道:“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番话,情谊绵绵。有评价,有敦促,有扶掖。最为明显的,还是浓浓的期望。
1972年5月,周恩来已查出患有癌症。作为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他深感独力难支和助手的缺乏。他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通过党的“十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并在中央核心机构窃取了更多的权力。这批人,靠造反或投机起家,才具有限,军国大事则不足与闻。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楚的。他要借重邓小平的智慧、才华和声望,起衰振弱,收拾混乱的政局。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排除江青一伙的种种干扰,先后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让邓小平放手工作,毛泽东还一度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他盛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一直到1975年夏秋季节,他对邓小平还是信任的。
但是,这种信任是非常短暂的。
毛泽东晚年,总结平生成就的事业,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片海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出于其胸怀的广阔和目标的高远,他把前者看得很淡,而后者则寄予了他毕生的理想和为实现这个理想所需的全部手段,对此他一度有着很强的成就感。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全部解除他的忧虑:社会处于动乱后的萧索和沉寂,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社会产品极度匮乏……这些问题不解决,毛泽东心目中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无从谈起。
邓小平顺应了历史的呼唤。他虽已年届古稀,而锐气不减,拿出了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气势,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全面整顿。整顿,就是要在各个领域建立正常的秩序,使国家摆脱那种盲动和混乱,使经济和政治生活走上正轨。这样,就必然与“文化大革命”以来那套“左”的政策发生冲突。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是让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以此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尤其是1975年将近一年的工作,其实质就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一步步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信号。
尽管毛泽东对是否再次打倒邓小平曾一度心存犹疑,还曾设想让邓小平“专管外事”,但是,一经认定他与邓小平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邓小平已经成了他继续推行其思想、路线的巨大障碍,他就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错误地判断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提议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把邓小平从中央领导核心“赶出去”了。这其中,“四人帮”的蛊惑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起过重大作用的伟人,都是有着博大胸怀的政治家。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出自个人之间的恩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一些重大关头能够信任、起用邓小平。而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之后,也能够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并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及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正确的评价。这些都是值得后人欣慰的。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