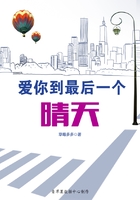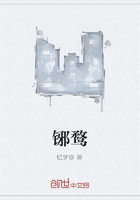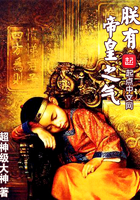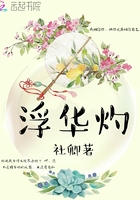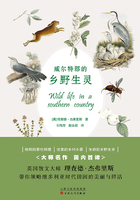老话不失据,俗话也不俗。俗话说“干冬湿年”。果然,在历史的脚步迫近春节的时候,持续一冬的干爽天气宣告结束了。李白曾经谬赞“燕山的雪花大如席。”当年徐州那场大雪,丝毫不比“燕山”逊色。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一夜未停。市民们睁开眼睛就懵了,第一感觉是“换了人间”。王处长马上想到的是伟大领袖那首万人传唱的诗词《沁园春·雪》。果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尽管如此,江山依旧多姿多彩,“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瑞雪兆丰年”。节前的大雪有利于农事,却不利于出行。街道上的公交车都绑了防滑链,长途汽车肯定也会采取措施的。王处长到办公室告假的时候,秘书长向他透露,今年天气特殊,如果本人申请,领导可以酌情考虑派公车送一下。王处长思虑再三,觉得自己级别不够,路途又远,还是不搞特殊为好。
为了安全,王处长破例搭乘去连云港的火车到新沂,从新沂转乘去郯城的汽车到店子。新沂离店子只有18公里,即便搭不上汽车也能步行回去。对于受过长途负重奔袭拉练的王处长来说,三四十里的脚程不在话下,但对于自幼养尊处优又怀有身孕的妻子而言,无疑是一场艰巨的考验,甚至说成是“磨难”也不过分。王义轩也不忍心让老婆受罪,可是时间太紧了,又赶上这么恶劣的大雪天。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适逢此时,家家户户都把灶马子贴在锅门口,往灶王爷嘴里抹上一条又甜又黏的冬瓜糖。善良的老百姓,切齿痛恨贪官污吏,却心甘情愿的贿赂神仙。
传说很久以前,冬天下的不是雪,而是精致的白面。也是农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接到天庭的圣旨,要他考察一下民风民情。灶王爷变化成一个病病怏怏的老太婆,到自己司值的主家去讨饭。主家婆不是贤良之辈,不论老太婆多么可怜,就是不给一口吃的。最后老太婆看到地下有一张煳饼,再次乞求道:“煳饼你们不吃,就赏给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太婆吧。”
主家婆怒眼圆睁,呵斥道:“我给孩子垫腚也不给你。”老太婆没再争辩,悄无声息地不见了。从那以后冬天就不再下面,改为下雪了。
爷爷还说,本村的迂腐秀才蔺友贤,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他小的时候,要到河西曹村去读书。每次过河的时候,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背他过河。他父亲料想,儿子的鞋子、库管都应该是湿的,可是儿子的服装鞋袜每次都很干爽洁净,父亲怎么询问他都不说。他和那个白胡子老头有约定,这事只能秘密进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
蔺友贤的父亲就起了一个早五更,提前埋伏在儿子过河的地方。儿子蹦蹦跳跳的走过来,往河边一站,一个白胡子老头从土地庙里飘然而至,背着蔺友贤飘过河去。是土地爷背着儿子过河的,看来儿子是福大命大之人。老爷子乐呵呵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见闻告知老伴。“母以子贵,老东西,你就等着享福吧。”
老太太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想起谁谁和自己不对付,吃完饭刷锅的时候就要发泄出来。儿子将来必是达官显贵之人,自己没有必要再忍了。她手里抓着一把筷子,一边敲击锅沿,一边盘算着“西家某某,东家某某,你们现在看不起我不要紧,等我儿子长大了……”
头年里放假回家,蔺友贤一家把他当成“至尊宝”,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悠。过完年再去上学的时候,土地爷不再背他了。他父亲赶紧化纸祷告,询问土地老爷怎么回事?晚上入睡之后,土地老爷领着老灶爷一起进入老爷子的梦中。土地爷撩起老灶爷的官袍,指着老灶爷的脊背说:“你看这么多红肿的道子,都是你老婆打的。你老婆老是用竹棒抽打他的脊梁骨,他忍无可忍,跑到天庭告诉玉帝,把你儿子的功名革除了。”
蔺友贤的父亲后悔不跌,在儿子屡次考不上举人,并决定不再进京赶考,安心留在乡梓,执教西席之后,把儿子没进庙堂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并且不住地重复:“记住了,老灶爷是千万不能得罪的。”
灶王爷一次遇人不淑就直达天聪,不多调研几家,比较一下,未免太轻率了,至少是责任心不强。再说了,那个主家婆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固然可恨,可是冬天白面遍地都是,到哪儿不能划拉一瓢半碗的,干嘛非得到人家去讨要?这不是成心吗?是不是平时没有伺候好?还是原本就有宿怨,正好借机挟嫌报复?每当议论此事,见仁见智者总是争论不休。老百姓很无奈,只有化纸祷告、抹点冬瓜糖,祈求灶王爷少说或不报人间的阴暗面。
王义轩夫妇很幸运,他们在新沂搭上了驶往郯城的末班车。但是雪天路滑,车速很慢。更要命的是,从店子到蔺王庄这8华里的路程,是非步行不可的。他们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歇歇喘喘,来到蔺王庄南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晚间7点多钟了。冬季里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就开始“金鸟西坠,玉兔东升”了,不过有一层厚厚的白雪映衬,夜晚并不黑暗。
王义轩叫老婆先行一段距离,然后从腰间拔出他心爱的“20响二把毛瑟驳壳枪”,站在村子里南北贯通的百亩水塘边沿,对着水塘“砰—砰—砰”连开三枪。这是他解放后和父母约定的联络报信方式(秘密行动除外)。他每次回家,或者是出发路过村子又不能停留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式向父母汇报的。
枪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犬吠之声此起彼伏。
儿子回来了,老两口点上灯,会心地对视一眼,马上披衣下床。他们要去厨房,给儿子张罗吃的。
同时被枪声惊醒的还有其他人,就是和彭生家连墙搭山的近门。彭生的堂叔王兴全、王兴义、王兴礼,领着年龄稍大的堂兄保国、和平和建设,先于王处长一步赶过来。王义轩还没到家,他们都已坐下来拉呱守候了。
割下一块过年备下的猪肉,煮几个平时省下来腌上的咸鸡子,挖一碗盐豆子,捞一碟汆辣疙瘩丝。两荤两素四个农家菜,很快就置办好了。酒是特意为儿子预备的,是优于散酒的瓶装酒。兄弟爷几个围坐在烟雾缭绕的锅屋里,啧咂地喝着小酒,身子也暖和了,心情也舒畅了,果真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雨生早就醒了。二年级的学生了,心里忘不了功课。她总是在灯下写完字后就钻进被窝去,一是抵御寒冷,二是说话、背诵课文都用不着点灯,她和大人一样省心,知道节省灯油。从村外传来枪声,到奶奶爷爷“窸窸窣窣”的寻找火柴点灯,雨生一直是知道的。她之所以默不作声,是担心奶奶。奶奶脚小,走路不稳,心有旁骛时容易跌跤。听到厨房里的喧嚣中有了爸爸的声音,王雨生才穿好衣服跑过来,和爸爸、叔叔还有三个哥哥一一打了招呼。
“我妈呢?”雨生搜寻了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没见妈妈的身影,心中不免疑虑,忍不住把目光投向爸爸。
“你妈她……”爸爸有些语塞,其他人也不说话了。小小的伙房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立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躲在锅框缝隙里的蟋蟀发出的“啾啾”鸣叫。爷爷说那些蟋蟀是灶王爷的马,屋檐下的麻雀是灶王爷的鸡。她一直不明白,灶王爷的马为什么比鸡小,这么小的马能撑得住灶王爷?灶王爷有多大?但她一直把秘密深埋在心里,不向奶奶爷爷发问。如果长辈被小辈问得无言以对,那将情何以堪呐?后来她似乎有点明白了,祖父母是在同情弱小,故意朝那些小生灵身上涂抹神秘的色彩,管控着彭生不会随意伤害他们的性命。
“你妈她——到你姨姥姥家去了。”爸爸略显沉重,用手抚摸着雨生的头:“明天早上就来咱家。”
雨生似乎隐隐感觉到父母之间的郁结,一缕伤感爬上心头,小小的年纪就有了忧愁。这忧愁一会在心头,一会在眉头。
翌日早晨,天气晴朗,北风“嗖嗖”的,卷起地面上的浮雪,烟雾一样地四处打旋。王福林老爷子顾不得雪路难走,差小女儿到北面6里外的盐店村,把二女儿一家叫过来,年前团圆一下子。
三女儿和女婿都在连云港146军医院,女婿是医院政治部的政工干事,女儿是内二科的护士长,都是军官。前几天女儿来信说今年要调防到临沂149医院,果真如此,离家又近了百十里,算是一桩好事情。不知手续办好没有?今年赶上下大雪,闺女还来过年吗?
中午吃饭的时候,彭生的妈妈回到婆家来了,是姨姥姥亲自送过来的。妈妈一进门,雨生就跑过去用小手拽住妈妈的衣襟,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妈妈,仿佛自己一松手,妈妈就会溜掉,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似的。
姨姥姥把奶奶拽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叽叽咕咕”地小声说话。只见他们一脸凝重,一会儿拍手、一会儿跺脚,长吁短叹。事态的发展有点严重了。
彭生的妈妈先去和姨姥姥见面,除了厌恶丈夫、嫌婆家条件差、礼数不周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想向“姨姥姥”倒一倒腹中的苦水。和生母阴阳两隔,受了委屈能找谁倾诉?合适的对象肯定不是婆婆。
奶奶等侄孙散去之后,也仔细地盘问了儿子。夫妻没有隔夜仇,小两口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呢?儿子和媳妇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儿媳妇直接用判决书上的语言形容丈夫“好逸恶劳、道德败坏”。
丈夫也是一脸无辜。“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能怨一个人吗?”人们形容夫妻失和,无非是“形同路人”。他们之间好像是积怨甚多的仇人。想起对方就感到厌恶,呆在一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久而久之,被冷落压抑的青年男人,是很容易被别的女人口中那股幽兰之气轻轻吹倒的。
中午奶奶粒米未进,汤水不尝。爷爷焦躁地骂着“通是孬种”,胡乱扒拉了几口饭。也是鸭子吞蜗牛,食而不知其味。
吃完饭妈妈还到姨姥姥家住宿,雨生按照奶奶的吩咐,形影不离地跟着妈妈。当姨姥姥追问妈妈准备怎么办时,母亲十分坚定地表明态度:离!等腹中的孩子落地就离婚!如果改嫁就和王家没账了,若是不再改嫁,老王家还欠她一畦埋身之地。雨生听到了,心中发冷、发酸,却不敢向奶奶爷爷提起。
爷爷和奶奶都是一脸忧郁,相互对视着,沉默不语。他们心中都跟明镜似的,儿子和媳妇已经势同水火,到了针尖对麦芒的地步,事情还会有缓吗?他们隐藏着心结,彼此都不说破。老人家怕一语成谶,万一不幸而言中了,后果实在不堪设想。那年月,“家破”和“人亡”挨得太近了。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不能不继续。虽然年还照样过,酒也照样喝。彭生家和全村的乡亲们一样,也放了鞭炮,贴了门神。可是,爷爷和奶奶的心中,浮起了一块阴霾,终生也挥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