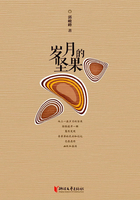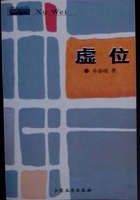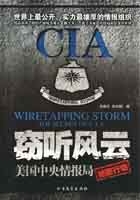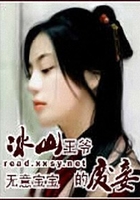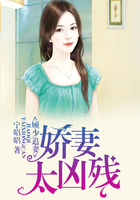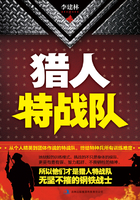《七发》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但是,关于《七发》的主旨却是一个自古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指出:“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谏吴王刘濞之谋反。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以上三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今人则多从“戒膏粱之子”一说。但是,《七发》真正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间题作出一些新的探索和论证。
一
据《汉书·枚乘传》记载,“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枚乘一生主要活动在吴国和梁国,《七发》究竟是写在吴国,还是写在梁国呢?笔者认为,《七发》当写于梁国,乃谏梁孝王之作。理由有六:
1《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楚太子。很明显,作品中的“楚太子”就是作者所要劝谏的对象。从作品中“太子方富于年”一句看,《七发》所劝“楚太子”不是指吴王刘濞,而是指梁孝王刘武。“太子方富于年”,意指太子正值盛年,未来的年岁正多。这与吴王刘濞的年龄相距甚远。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刘濞反时,曾自云“寡人年六十二”。枚乘在吴时,刘濞也当有50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而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据《汉书·外戚传》载,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享年40岁左右。其“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时,不过30多岁,正值盛年。
2从作品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享乐生活的句子来看,《七发》所劝当指梁孝王。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刘濞因吴太子入朝被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打杀故怨望朝廷,称疾不朝,谋作乱。后景帝即位,议削吴,吴率七国诸侯起兵于广陵。当时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中有云:“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见,吴王刘濞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因而说《七发》是劝谏吴王刘濞,这“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诸语就有些不着边际。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确实有“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情况。因而,《七发》若是劝谏梁孝王,才算对症下药。
3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七发》应该是写在梁国。《史记》、《汉书》都有枚乘在梁国作赋情况的记载。《汉书》的记载较详,其《枚乘传》云:“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这说明枚乘是梁国梁孝王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理应写有非常著名的作品。而《史记》、《汉书》都未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这也可说明枚乘在吴国时主要的还是“为吴王濞郎中”,在写作辞赋方面成就还不够高,不可能写出《七发》这样的特别重要的作品。
4从辞赋发展的角度来看,《七发》也当写于梁国。枚乘在吴国时,辞赋还囿于南国一隅,流行的是抒情的骚体赋,不可能出现像《七发》这样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散体大赋。现存比枚乘略早的贾谊的作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枚乘到梁国后,辞赋之风北移,使辞赋境界大开,产生像《七发》这样的散体大赋的条件才渐趋成熟。
5《文选》卷二七谢朓《休沐重还道中》李善注云:“《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据此可知,初唐李善是可能见过旧《枚乘集》的人。他可能从目录次序或其他材料中得知或推知《七发》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远比北宋以后持《七发》写于吴国说者的臆猜为可信。
6持《七发》写于吴国说者往往以《七发》中假托“楚太子”,且多写南国风物为证,我们认为这是不足以服人的。辞赋作品通常采用隐喻的笔法,多有虚构和假托,对于其中的人名和地名都不能坐实理解。战国时期楚国为大国,汉赋以大为美,故多有假托楚国者。既然假托为“楚太子”,又是“吴客”往问,当然就多写南国风物。而枚乘是淮阴人,又曾仕吴,谙熟南国风物,所以他在梁国所写的作品中多写南国风物也不足为奇。更何况与枚乘一同游梁的邹阳就曾以直谏被谗下狱,枚乘又怎敢直斥而不作此假托呢?
以上六点足以证明枚乘《七发》当写于梁国,实为讽谏梁孝王之作。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排除《七发》主旨是谏吴王濞谋反一说了。
二
既然《七发》是写于梁国,又是为谏梁孝王而作,那么,它的主旨是谏梁孝王不要过于奢侈享乐呢?还是谏梁孝王不要谋反呢?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曾经修东苑,扩城池,“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有过一段十分奢侈享乐的生活。同时梁孝王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又深得窦太后的宠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梁孝王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钦,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梁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后嗣事由此。”“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孝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可见梁孝王不仅有十分腐化享乐之劣迹,而且也曾有过欲谋反的迹象,尽管他最终没有谋反。既然如此,那么《七发》的主旨就只能从作品本身来查找了。
我们知道,《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事来启发“楚太子”,实际上就是用七种方案来给“楚太子”治病那么“吴客”给“楚太子”治的究竟是什么病呢?是由于日常生活过于腐化享乐所引起的肉体上的疾病呢?还是思想上、精神上的疾病呢?从《七发》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楚太子”患的主要不是肉体上的疾病,而是思想病,“精神”病。试想,如果是由于日常生活过于腐化享乐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疾病,那么,“吴客”提出以饮食、游宴、女色来治疗,当然要遭到拒绝,但当吴客以音乐、骏马、田猎、观涛来劝他时,他就不应该拒绝,因为这些活动是可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况且,如果是肉体上的疾病,一听圣人的“要言妙道”,就怎么能够“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呢?用“要言妙道”来治病,用“圣人辩士之言”来治病,这治的只能是思想病。而这思想病是一般的贪图腐朽享乐生活的思想病呢?还是严重的政治病呢?我们认为是严重的政治病。如果是一般的贪图腐朽享乐的思想病,“吴客”用饮宴、女色、音乐、骏马、田猎、观涛等活动来规劝他,他就决不会毫无兴趣,表示拒绝。“吴客”用这些方案来给他治病,说明他患的是严重的政治病,说穿了就是想谋反的病。他没有能够得到皇位的继承权,因而心情郁懑,所以“吴客”先以音乐、美食、车马、游观等活动来启发他,想以此来陶冶他的情致,排遣他胸中的郁闷,但他丝毫没有兴趣。后来,“吴客”又用田猎、观涛的活动来启发他,使他胸中的郁闷稍解,“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但也并没有真正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于是,“吴客”最后说:“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涣然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才最终放弃了非分的企图,解除了精神的郁懑,“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当然,也许人们要说,“吴客”所列举的“圣人”的“要言妙道”比较笼统,并没有谏谋反的实际内容。这是因为当时梁孝王虽然有篡权谋反的野心,但没有见诸公开的行动,所以“吴客”不能直言,只是暗寓讽示而己。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七发》的主旨正如李善所说,就是劝梁孝王不要谋反。应该指出的是,枚乘生活在文景时代,当时诸侯国势力很强大,谋反的事屡见不鲜,严重威胁着汉朝的统一政权。《七发》这种谏谋反的意旨在当时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七发》还有刘勰所说的“戒膏粱之子”的含义,正所谓“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从而告诫膏粱子弟不要过于奢侈享乐,而要注意修身约己,加强思想修养。这是《七发》在描写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意义,也正是文学作品多义性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枚乘写作此赋的主要意旨。至于谏吴王濞谋反一说则属后人臆猜,无可征信。这一结论是否允当,俟博雅君子正之。
(原题《关于枚乘〈七发〉主旨的商榷》,载《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后修改更名为《枚乘〈七发〉主旨新论》,载《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