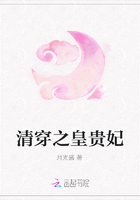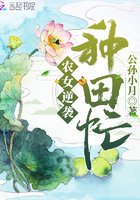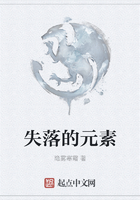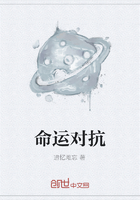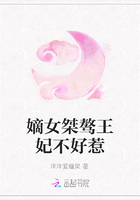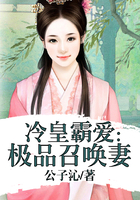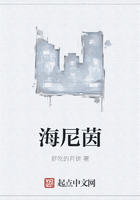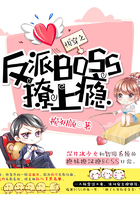楔子
明成二十一年秋,太子瞻联手大皇子、九皇子密谋毒杀先帝。
秋末,先帝暴毙,朝内大乱,广贤王率七万精锐镇压太子叛党,史称“双都之乱”。
同年冬,广贤王登基称帝,改年号建元,废黜太子,褫夺大皇子、九皇子封号,将其三人凌迟处死。
次年春,建元帝下令将三皇子、四皇子、六皇子和十二皇子贬为庶人,流放蛮夷蜀地,一年间,四人相继客死异乡……
……
建元一十七年三月春始,江陵县傅宅。
藤缠灰瓦的高墙外,打更的更夫刚敲下手中的梆子,玉堂斋的院子里便传来了疾步声。
立在廊下的九歌闻声心头一紧,下意识便将手中的灯笼提高了几分。
清朗的夜色笼着静谧的小院,疏影横斜,梨花香浅。
不过眨眼,一抹绯色的身影便踏破了沉寂,直冲九歌而来。
“如何?”见着来人,九歌提着灯笼快步迎了上去。
摇曳的灯烛下,跑上前的小丫鬟脸泛潮红,额间渗汗,气喘得根本接不上九歌的话,乌黑的瞳仁里透出的全是慌乱。
九歌见状,心中“咯噔”一记,咬牙忍下了翻腾的思绪道,“跟我进屋吧。”
厢房内月色浮窗,烛火盈盈。
罗汉床上,傅云昭正手执书卷,依窗斜卧。
摇曳生辉的明亮将她的清辞秀丽照得一览无遗,当真是美若春梅绽雪,韵似秋蕙披霜,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眉目间流露着嫣然风韵。
听见脚步声,她杏眸微抬,一管声音清冽如泉,刹那间溅碎了满室的宁静,“去看看小厨房的热水烧好了没有?”
九歌一愣,垂首应了一声,随即利索地带着小丫鬟屈膝退出了屋子。
隔着晃动的门帘,傅云昭听见小丫鬟挣扎轻喊,“姐姐拉我做什么?我还没同姑娘说那孩子……”
激动的声音渐渐散去,傅云昭握着书卷的手下意识的紧了紧。
窗外,如荼的灯光将整个府邸的西北角照得通明似昼,而西北角是个独院——薛姨娘单住的朝露阁。
即便是隔着重重院墙,傅云昭都能感觉到从朝露阁透出的漫天喜悦。
这个当年被爹爹用大红花桥正经抬进门的小户之女默默无闻了数年,竟在怀胎十月之后让傅府一夜之间陷入了暗波汹涌中。
偏偏,偏偏是个……男孩儿!
傅云昭对着一窗灯火目光涣散,青涩未褪的脸上透着深沉的凝重。
沉寂中,门帘微动,九歌端着热水再次而入,照常伺候着傅云昭洗漱净尘。
傅云昭素来自律,自从单住独院开始,每日卯时三刻起,亥时末睡,鲜少有变。可今日洗漱完毕后,她却没有按时躺下。
九歌眼见傅云昭换了身素衣又坐回了窗边,终于忍不住催道,“姑娘还不歇息?”
“估摸着要闹一夜,与其回头有了睡意再被吵醒,不如等安生些再睡。”傅云昭开口,语气淡淡,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可屋子里只她和九歌主仆二人,九歌从小就伺候在她身边,两人朝夕相伴十多年,傅云昭的一举一动九歌是再熟悉不过了。
眼见傅云昭眉目尽敛,说话心不在焉的,九歌便知她此刻已是憋了气,当即便上前虚坐在罗汉床边轻声道,“方才您没让灵俏说话,可她倒真是带回了些可听的消息。”
傅云昭看了九歌一眼。
九歌心思了然继续道,“说是老太爷只差遣梁妈妈去了一趟朝露院,他老人家在书房都没挪过步。”
傅云昭闻言不免失望,“爷爷自然不会把心思都放在台面上,更何况薛姨娘才刚生完,屋子里头怕是气味都没散尽呢,爷爷又怎么会亲自去?”
不过话一出口,她倒觉得心中舒畅了大半。
是啊,她心里确实憋得慌,偏在这节骨眼儿上,多的是人想要看她战战兢兢出丑的模样。
可她是傅家的嫡长女,怎能叫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如了愿?
九歌闻言,轻轻握住了傅云昭的手,“姑娘说的是,老太爷做事素来有章法,既然如此,姑娘又何必杞人忧天。说远了,这孩子不过才刚出生,说近了,他终究也只是个庶出罢了。”
“贵胄皇亲才看中血统纯良,我们商贾之户又哪里在意这些。这孩子落了地就没办法塞回去了,从此以后,爹爹有了儿子,傅家长房是真的后继有人了……”轻叹间,傅云昭眼底还是闪过了一丝释然。
终究还是好女不如男啊!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却也正是时候。
九歌顺势又劝道,“姑娘别多想,还是赶紧歇了吧,小少爷这一出生,明儿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来咱们玉堂斋探口风呢。”
“傅府添丁爹爹得子是好事,何惧人言?”傅云昭轻轻一笑,坐直了身子正想宽衣,忽听屋外竟响起了急急的脚步声。
进屋的是三姑娘傅云萱的贴身丫鬟霜见。
见着傅云昭,霜见顿时面露难色,支支吾吾道,“大姑娘,咱们姑娘闹了肚子,左右疼得厉害,吩咐奴婢来跟您讨副对牌出府去请个大夫来瞧瞧。”
傅云昭闻言,刚还略见温和的脸上立刻沉得如玄铁般透出了寒意。
见她有意起身,九歌一边上前,一边冲门口的霜见摆了摆手,然后虚扶着傅云昭的腕子轻声道,“姑娘歇着,我过去瞧瞧吧。”
傅云昭看了一眼脸色微白的霜见,吩咐九歌,“你去看看也好,若真的病了,就差人来拿对牌,倘若她只是闹了情绪……”
她话没有说完,九歌已应声点头,带着霜见退了出去。
谁知不过眨眼的工夫,九歌却又神色慌张的跑了回来。
“姑娘,老太爷差人请您去祠堂。”九歌性子沉稳素来镇定,但现下眼底竟也透着遮掩不住的忧心。
傅云昭闻言倒是面色不改,只吩咐九歌赶紧先去稳住傅云萱别让她大晚上的胡闹,自己则拾掇妥帖以后只身踏夜出了玉堂斋。
------※※------
傅宅里的这间祠堂是三年前才迁进府里的。
当时从老家旧屋请回这些祖宗牌位的时候,老太爷还请了修圆寺的慧宗大师来打了七天七夜的蘸,又做了三天的水陆道场,确是正正经经的祭了祖先引了香火的。
可即便如此,这修在宅子东南角的祠堂平常却鲜有人迹,隔了层层长势丰茂的青竹,堂屋里的森森阴气全掩在了那片鲜活的翠绿之中,入了夜,更显肃杀。
从玉堂斋去祠堂的路不长,穿过抄手游廊再绕过迎风亭便就到了。
祠堂外,早有婆子掌灯静候。
见着傅云昭,婆子立刻上了前,先替她拂尘净手,然后又举着灯笼给她照了路。
堂屋内高粱横悬,牌位上供,案前香燃,灯烛正旺。
傅老太爷负手而立,灰褂布鞋,脊背挺拔,硕朗的身形丝毫不见年近六旬的迟暮之态。
“爷爷。”傅云昭轻轻上前,对着傅老太爷的背影福身行礼。
“来啦。”老太爷闻声,肃然紧蹙的双眉微松,转头看了看孙女,慈祥笑道,“今儿是个好日子,你来给祖宗们上支香。”
“是。”傅云昭上前一步,仔细的焚香叩拜,起身后还用帕子将案台上的香灰轻轻的抹净。
一转身,却见傅老太爷已递上了一张纸。
傅云昭双手接过,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龙飞凤舞的“晔”字。
“这是……”傅云昭猜到了老太爷的意思,却不敢妄言。
“晔晔煌煌,锋芒毕露。”老太爷低头看了一眼孙女,话说得模棱两可,“虽是个庶出,可到底也是你爹的独子,这孩子以后总不能是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傅云晔。”老太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傅云昭没理由再藏拙,“爹爹应该也会喜欢这个名字。”
傅家按族谱起名,到了他们这一辈,不论男女都沿袭“云”字,大气雅致。
见孙女垂目静立,开口亦是面色无波,老太爷眼底闪过一丝赞许,从腰间抽出一封请柬道,“这帖子是晌午从临凰别苑送进府的,这会儿别院里怕是已经住下来张罗的宫人了。”
傅云昭探头看了一眼,薄如蝉翼的纸笺上写着两行苍劲有力的正楷——临凰别苑空置三载,甚念江陵美景。四月春盛,本王意随家眷前来小住,望设宴常欢。
落款写着“湛王”二字。
湛王,轩辕湛,当朝的五皇子,能文善武,德贤有才,深的圣心。
“说是赏景小住,只怕来者非善。”老太爷摩挲着食指上的玉戒,神色肃穆,“北方这两年是愈发的乱了,咱们南梁偏安一隅,仰仗着山川险峻的天然屏障,倒是多年不近战火的。可所谓的国泰民安也不过是一出哗众取宠的戏文罢了。自圣上登基,贪污之风愈盛,权臣谋私国库空虚,士兵娇贵威武不复,若有朝一日内忧外患一并倾覆,朝廷能抵挡几日?”
傅云昭静静听着,心里却翻江倒海一般,“总是天家颜面,难道五殿下还会亲自和您开口要……”话到嘴边,她都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天家颜面又值几斤几两?”老太爷目光微扬,往向了东窗。
东之所向,皇宫禁地。
当年明成帝初登大典,崇武重兵,志在收复山河,谁曾想却引来太子瞻的嗜权反扑。
如今建元帝偏安一隅,重农重商,志在休养生息,却依旧未能治好朝廷上下那根深盘错的沉疴旧疾。
南梁国祚已逾九十三载,可南梁皇室却早已腐在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