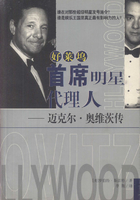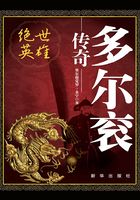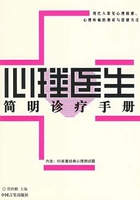叔梁纥生孔子时,已是六七十岁的高龄了,孔子刚刚3岁,他便与世长辞了。尚值童年的孔子失去了父爱,他的母亲颜征在,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矛盾复杂的叔梁纥家,从陬邑迁到了曲阜城内一个叫阙里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孤儿寡母的生活格外艰难清苦,但颜征在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她是位极有见地的女子,虽然年轻丧夫,家道没落,日子过得很不顺心,但她仍旧勤苦持家,悉心教子,在儿子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希望。她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对年幼的孔子加强教导,要他努力学习,刻苦磨练,以便将来有所作为。传说颜氏在孔子尚很幼小的时候,便常买来一些礼器给他作玩具,让儿子从小便习礼知礼。在慈母的严格教导和悉心培养下,孔子很小便表现出了他异于普通孩子的独特之处。他不像同龄儿童那样淘气顽皮,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的方形、圆形的俎豆之类的礼器摆列开来,自己练习磕头、揖让等礼仪。可见,孔子的成长是与他小时候母亲的悉心教育分不开的。
家境的贫寒使孔子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艰难。从懂事的时候起,他便帮着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年纪稍大一些时,他迫于生计,不得不参加各种劳动,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的艰辛也使少年的孔子一点点儿成熟起来。很多年后,孔子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地位低下,所以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能。这种经历对孔子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接受磨练的机会。孔子的一生,常常得益于这段“吾少也贱”的艰苦生活的磨炼。
少年的孔子便心怀大志,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的栋梁之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以,尽管生活清苦、家境贫寒,他仍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寻求着知识。他白天干活,晚上回到家里刻苦攻读;他经常参加城内举行的各种大型的礼仪活动,在一旁细心地观察和揣摸;他勤奋刻苦,不耻下问,努力从生活中汲取文化和知识的营养。一有机会进入鲁国的太庙,总爱不停地问这问那。有人轻视地评价他说:“谁说陬叔纥的这个儿子懂礼呀?看他进了太庙,什么都问,他能懂什么呢?”孔子回答说:“不懂就问,这正是知礼的表现啊!”正是依靠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和过人的毅力,孔子才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
然而,过度的操劳和清苦的生活,大大损害了孔母颜氏的身体,使她才三十几岁便垮了下来。孔子16岁左右,他的母亲也撒手西去了。母亲的辞世使孔子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日子更苦更艰难了,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独立谋生。现实逼迫他必须找到一种能挣钱糊口的工作,他先是为人当“委吏”,替别人管理仓库;后又为人作“乘田”,替别人管理牛羊。这些工作,都是当时的贵族子弟所不屑于做的“鄙事”,但孔子却把仓库理得清清楚楚,将牛羊管得肥肥壮壮,竭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一有闲暇,便更加刻苦勤奋地自学。所以,虽然他没有受过当时的正式教育,但还是以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很快,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再加上孔子为人谦恭知礼,行事谨慎细心,年纪不大,便在当时的许多人心目中,包括一些贵族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母亲去世后不久,有一件事,对孔子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那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鲁国的执政贵族季武子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宴会,用来招待国内各地的士人们。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包括大批贵族下层人物,也包括一些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而且学有专长的优秀的平民子弟。季武子宴请士,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士阶层的人们,求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也想趁机从中为自己选拔一些有用的人才。当时孔子丧母不久,孝服未除。他以为自己的父亲叔梁纥是陬邑的大夫,又立过战功,曾以“勇力闻于诸侯”,自己作为他的儿子,按出身也当属士这一阶层;再有他自幼受母家教,又刻苦好学,熟悉各种礼仪,也算是有用的人才。所以,听到消息后,他便欣然与人同往。
走到季武子家门口时,孔子被季武子的一个名叫阳虎的家臣拦在了门外。阳虎以傲慢的口气呵斥孔子道:
“季家宴请的是士,谁宴请你呢?”
孔子无奈,只好忍怒悄悄退了下来。阳虎这样做,无疑是对涉世未深的孔子的一种故意羞辱,也是对踌躇满志的少年孔子的一次打击。这件事,使孔子深切地认识到:父亲的身世并不能给自己增添荣耀,自己前面的路并不会一帆风顺,惟一的出路,只能凭自己的努力去闯荡和争取了。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少年的孔子暗下决心,一定要以自己的努力进取去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谋求一条能够真正济世救民的人生道路。
就这样,出身贫贱的少年孔子,在生活的困苦和磨难中成长起来,开始了对于人生道路的更加自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