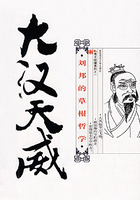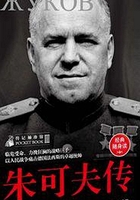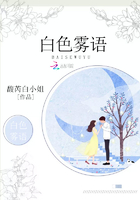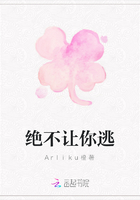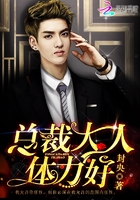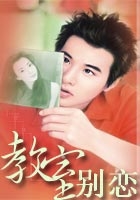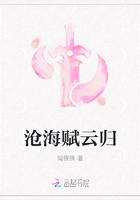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等四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对我来说井不是十分陌生,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要将她们付诸文字,却又十分踌躇,有无从下笔之感因为四大美人中除王昭君和杨贵妃正史有所记载外,西施和貂蝉则名不见经传。尤其是貂蝉,只能算是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的艺术形象,要在历史上找到原型亦有一定难度。另外,民间传说和文人作品及历史记载中四大美人的事迹也多有差异,需要有一个考察、甄别的过程。根据以上情况和本书的体裁要求,在写作过程中,我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历史背景为依托,做到人物有原型,事实有根据,尽量迫求一种历史的真实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四大美人各自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她们本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所担任的角色和本身所作所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些单靠正史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稗史笔记之类。于是,我徜徉于浩瀚史籍之中,在茫茫书海中迫寻她们的踪迹。
在我国现存最旱的地志《越绝书》中间,首先发现了有关西施的记载该书卷十二载有又种向越王勾践所献的“灭吴九术”,其中第四种即为“遗之好美,以劳其志”,也就是利用吴王夫差贪色的特点,赠送美女,以虚其身,衰其志,达到灭吴之目的。“灭吴九术”之下,接着载有:“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同书卷八《美人宫》条又云:“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教习美女西施、郑旦宫合也。女出于萝苎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邮,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
太史公《史记》载有文种“灭吴九术”之献,但未记所献美女为何许人。
东汉人赵哗所撰之《吴越春秋》,记吴、越两国史事,亦有“灭吴九术”种种,有美女郑旦之名,而未提及西施。
晋王嘉《拾遗记》云:“越谋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进于吴。又有美女二人,一名臾光,一名休明(西施、郑旦别名),以贡于吴,吴王妖惑乱政。”
南朝梁·任防《述异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洁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殆费人力宫伎千人,又别立春宵馆,为长夜饮,造千石酒钟。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伎乐,日与西施为水嬉。”
唐·陆广微《吴地记·花山》条云:“哥屏亭东有馆娃宫,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灵岩山是也。”其下注释云:“今灵岩山遗址,尚可见馆娃宫遗迹,砚池、洗花池、玩月池、吴王井、梳妆台、琴台、采香径等。”该书《石城》条下又云:“吴王离宫,越王献西施于此城。”《香山》条云:“吴王遣美人采香于此山,以为名,故有采香径。”“吴王种香于此,遣美人采之,故名。下有采香径,通灵岩山,今名箭径山。”以上记载足以将西施一生贯串起来,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昭君的事迹在正史中虽有记载,但非常零散,散见于《汉书·元帝纪》、《汉书·勾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之中。
《汉书·元帝纪》在叙述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朝见后,元帝乃“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婚为阔氏。”条后应邵注日:“王嫱,王氏女,字昭君。”《汉书·匈奴传》亦云:“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相比之下,《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就详细得多,其云:“字昭君,南郡人也。刊,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谏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救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阔氏焉。”《资治通鉴》元帝竟宁元年条下记日:“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婚字昭君赐单于。”和《汉书·匈奴传》完全一样。
上述文字虽然不多,但把王昭君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交代得一清二楚和上述两人相比,貂蝉事迹在史籍中显得特别少。
《三国志·吕布传》载:“(董)卓常使(吕)布守中阁,布与卓侍蟀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后汉书·吕布传》云吕布“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此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问,而私与侍脾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两条记载,都言及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事,而未言侍婢为阿谁。但董卓、吕布以此构衅,导致董卓被诛却是事实。以此可以推知董卓侍蟀乃为貂蝉之原型。其“七分为事实,三分为演义”,的《三国演义》对其形象的塑造也是事出有因的。
杨贵妃的资料在四大美人中当推第一。除两《唐书·后妃传》中有较详细记载外,《资治通鉴》也有大量关于贵妃的文字。此外,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唐·郑繁《开元传信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乐史《杨太真外传》等稗史小说中都有关于杨贵妃的记载,其中乐史《外传》则专为杨贵妃而作。这些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综上可知,四大美人在我国历史上不仅确有其人,而且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到当代和后世史家的重视,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历史人物,经过数千年来人们的口头传颁和文学作品的艺术加工,使得她们的形象更加丰满,事迹更为突出,生平活动脉络也更加清晰。这些都是本书撰写中的重要史料来源。
二、追求内容和情节的完整,尽量做到艺术性和历史性的合理结合。
四大美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史料记载也比较零碎。要用文学的形式把她们的一生经历表达出来,情节的完整至关重要。在达一方面,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明·梁辰鱼《沈纱记》以戏曲的形式完整而系统地表现了西施和范益定情、定计、入吴、灭吴、泛舟五湖的整个过程,是较早反映西施事迹的戏剧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施的故事》、陈民中《中国古代美人的传说》等介绍了西施一生中的几个片断。杨善群《越王勾践新传》、夏廷献《范鑫》等书也都提到了西施的事迹。
至于西施的最后归宿,说法也不尽相同。一说西施在吴亡之后,被勾践夫人装入牛皮袋子,沉江面死以绝后患;一说西施于吴亡之后,和范蠢一起泛舟三江五湖,悠然而去。
持前一种说法的以《墨子·亲士》篇中“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之语为主要依据。今日苏州城之带(袋)沉桥据说即为纪念西施而名的。唐·李商隐《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晚唐·皮日休诗日:“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弯弯欲效壑,等都是对达种说法的肯定。
持后一种说法的以《越绝书》”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鑫,同泛五湖而去“为主要依据。明·梁辰鱼《洗纱记》、明·杨慎《升庵集》、唐·杜牧《杜秋娘诗》都持这种看法。宋代大文豪苏轼对这种说法尤为赞同,其《范蠡》诗中”谁遣姑苏有糜鹿,更怜夫子得西施“、《西施》诗中他年一舰鹤夷去,应记奴家旧姓西”,及《水龙吟》词中“五湖开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等语,明确不过地表达了他对西施下落的见解。
在西施随范蠢泛舟五湖的说法中,也还存在着歧意一种认为,范鑫与西施本有旧情,功成之后,载之以去,天遂人愿,是一种美好的结局,这是西施家乡人们的传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西施的祝愿。另一说法是范蠡因西施感乱吴王,致吴亡国。怕以后西施又惑乱越王,使之蹈吴覆辙,故载之远去,以绝越国之患,给美好的结局蒙上一层阴影。这种说法,以梁辰鱼《洗纱记》和罗大经《鹤林玉露》为代表我认为此纯属卫道者之语,绝非范蠡原意,范蠢出走是看透了勾践的真实面目,而非惧西施为祸也,故此说不可取。
细察以上说法,以沉江而死者为是,因墨子为春秋战国之交人,所处时代距吴亡不远,其说当为可信。但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鉴于入们对西施的喜爱和怀念,为了表达一种善良的愿望,在情节安排上,选取了“泛舟五湖”之说,追求了一种艺术的完美。
昭君出塞和亲的史实,史籍中记载不多,但东汉以后,却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关于昭君的文学作品出现,仅诗歌就有600多首。戏剧20多种、现代戏剧大家曹禺和历史学者郭沫若先生也以戏剧的形式塑造了昭君的形象。台湾作者高阳还以王昭君为题材撰写了长篇历史小说。
在上述作品中,昭君的形象千姿百态,各有风采。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对待出塞的态度上。一种是被迫出塞,无可奈何;悲悲哀哀,惨惨凄凄,甚至走到界河上投水自杀。持此说者以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请行,使得汉胡和睦,亲如一家,此说以曹禺戏剧《王昭君》为代表。本书经过比较,认为主动请行更能体现昭君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的高尚情怀,因而选择了后者,使昭君形象更臻完美。
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问世,更由于这部名著被改为电视剧搬上荧屏,使得貂蝉之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原型当为史籍中与吕布私通之董卓侍蟀无疑。
而后董卓与吕布矛盾迭起,董卓以戟掷刺吕布,王允与士孙瑞谋杀董卓,以吕布为内应等等均有史料记载,凿凿在目,不可不信。故《三国演义》中貂蝉故事的情节虽经作者作了艺术上的加工,但来龙去脉有迹可循,所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即以此为蓝本,作进一步的加工。所不同者是在貂蝉的最后结局上,《三国演义》中没有交代貂蝉的最后下场,民间传说中貂蝉的最终结局有如下两种:一是吕布死后,貂蝉落入曹操手中,曹操为了收买关羽,即以貂蝉赠之。而关羽以董卓、吕布事为戒,怕红颜而为祸水,故硬着心肠,闭起眼睛将她杀死,使她成为关老爷的刀下之鬼。另一种结局是貂蝉被送与关羽之后,关羽斥其以色媚人,惑乱人心。貂蝉不服,义正辞严地驳斥关羽,表白自己一片爱国之心,报恩之情,说得关羽心服口服。在张飞闻讯赶来要杀貂蝉之时,关羽毅然掩护貂蝉脱险,送入尼庵修行,并嘱以其身所历付诸文字,以戒后人,貂蝉在尼庵中得以善终。
两种结果看来以后者要好得多。但笔者以为,以貂蝉其人其事,两种结局都不适合于她。因为貂蝉之所以里生死于度外,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报王允养育之恩,除国家倾覆之患。吕布死后,让她继续留在人间,似有不妥。(当然也不排除王允为了继续钳制吕布,会让貂蝉作如是选择的可能。)但据《三国演义》记载,羞卓死后,其部将李催、郭记攻入长安,与董卓复仇,在作战中,吕布失了城池,“左冲右突,拦挡不住”,引数百骑来到青琐门外,招呼王允一块逃走,遭到婉言谢绝后,遂弃却妻小,引百余骑飞走出关,投奔袁术去了。《三国志·吕布传》也载李、郭攻入长安,与吕布战城中,布败走。
《后汉书·吕布传》记李、郭攻入长安,“布与催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先投袁术,后与张扬奔河内,又投袁绍,后又奔至洛阳等等。
如上所述,吕布在长安战场上失败,落荒而走,身无立足之地,先后投靠数人而不得安身,根本不可能带貂蝉一起出逃。所以貂蝉即使不死,此时也应在被“弃却”的妻小之中,而不可能在吕布身边。吕布逃走后,王允死于李、郭之手,家小全部遇害,貂蝉当不能幸免。或许以貂蝉之美,李、郭二人对她有非分之念,免其不死。但貂蝉何等女子,岂能偷生,所以从容取义应是貂蝉归宿的最好选择。生以身报司徒大恩,死以命殉之地下,有始有终,忠贞不渝,方显貂蝉之真情义。而民间传说则为显关公见色不惑的忠义气概,却要以美女貂蝉作为陪衬,实在有貂蝉形象。故本书摒弃众说,而以“取义”结局,也是对貂蝉形象的净化。
杨贵妃事迹史料记载颇多,墓本可信。所疑者,两次出宫风波的起因,这点史书未作详细交代。《旧唐书·贵妃传》云:“(天宝)五载七月,贵妃以微遥送入杨宅。九载,贵妃复怜旨,送归外宅。”新唐书·贵妃传》云:“他日,妃以遮还第。天宝九载,妃复得遣还外第。”其他史书也都一言代过,不作详说,给后人留下许多悬念和想象贵妃进宫之后,玄宗视之如命,百依百顺,双出双入,形影不离,能遣还出宫,定有较为严重的原因。在这点上,《资治通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天宝)五载七月,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那么,“妒悍”的对象是谁呢?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人们选中了梅妃和魏国夫人,因为只有以梅妃之美、之才情,就国之艳、之倾巧,才堪与贵妃争宠,由此引发了贵妃的“曝妒”,但查诸史籍,梅妃未有其人,实为虚构而魏国此时也未封为夫人,气候尚来形成,不具备和玄宗调睛的条件。联想到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的上阳宫女“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的情况,似说明上阳宫女遭此厄运,是由于杨妃“侧目”的结果。
白居易友人元镇也有《上阳白发人》诗作,揭露了天宝年中因玄宗选美,使得民间“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爷血泪垂”的悲惨现象,并自注云:“天宝中,密号采取艳异者为花鸟使。”元、白二人系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其时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当为可信据以上所述分析,则贵妃天宝五载所妒的对象,应属当时新选来的宫女。
天宝九载被谴原因,晚唐·郑萦在《开天传信记》里作了详细叙述:“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轴轿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云云。
《资治通鉴》又提供了天宝九载因“妒媚”怜旨的具体时间线索:“(天宝)八载冬十月乙丑,上幸华清宫九载春正月乙亥,上还宫。二月,杨贵妃复怜旨,送归私第。”也就是说,从八载十月到九载正月10多天的时间里,玄宗和贵妃都在骊山华清宫度过。而返回长安兴庆宫不久就发生了复因“妒媚”怜旨的事件。看来,事情是在华清宫发生的天宝八、九载问,有资格跟玄宗幸骊山的女性,自然非杨氏三姐妹莫属。三杨中,韩国、貌国未见在男女私事上有何传闻,尤其来闻和玄宗有何瓜葛。而魏国殊艳尤态,杨柳浮萍,又倾尽机巧善事人,早年即与再从兄杨国忠关系暖昧,后来又与妹夫唐玄宗有染。故中唐诗人张枯曾以集灵台为题,作诗讽刺云:“魏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洗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平时在长安宫中尚且如此何况在华清宫中这亭台楼阁掩映、林木花草茂盛的地方,调情作爱,也是想象中事了所以可以推测,二人在骊山调情,被贵妃发觉,因而引出二次因“妒媚”怜旨被谴出宫的事件。
最后关于杨贵妃的结局,本来史籍记载已十分清楚,为赐死马鬼无疑。而后世之好事却根据白居易《长限歌》中“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扒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大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等诗句,臆造出贵妃死而复活,东渡大洋,定居日本的事迹。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尤其是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似乎真有其事一样。其实白氏《长恨歌》旨在颂扬李、杨爱情,蓬莱仙山、大真仙子之说纯属虚构,完全是为了表现王题的需要,丝毫没有贵妃复活、东渡扶桑之意。想不到却授人以口实,借此大作文章,殆非白居易之初衷。因而亦为本书所不取三、突出主题,写出四大美人“美”的价值所在,摒弃“红颜薄命”和“美人祸水”之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社会各阶层人们在身份、地位、年龄等各个方而存在诸多不同,但在对美的欣赏和热爱上却是共同的。古往今来,劳动人民在开天辟地、创造社会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因而美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大目标,是人类共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可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一面千方百计猎取美色,肆意摧残,以饱私欲。一面又假惺惺地打出一种卫道者的招牌,把受其摧残遭受不幸的女子归为“红颇薄命”之类;又把自己因贪色而误政、误国的罪过归咎于“美人祸水”,之列。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四大美人皆属国色,殊艳绝代,她们的遭遇是否也是她们的“薄命”和“祸水”之由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
前所述西施、昭君和貂蝉均为国献身,牺牲了她们的幸福生活和青春年华,把自已的冠代之美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西施、貂蝉均为义气所激,以国辜为重,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起到了须眉男儿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另一种方式为国效命,功绩卓著,彪炳史册,为千秋万世所景仰。即如昭君,也并非没有留在汉宫享受荣华富贵的可能。但激于民族大义,有志于汉胡相亲,自动请行,当是出塞之主要动因。昭君这一行为的结果,是“汉胡和好,亲如一家,边境安宁,烽烟不兴”,能说不是昭君之功吗?
凡是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至今,苏州城中灵岩山上尚有许多西施遗迹,足以唤起人们对这位美女的怀念。大型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貂蝉功成身没,随清风明月而去,不正是展现了一种高洁、纯美的道德,表达了人们对貂蝉的美好祝愿吗?昭君辜迹不仅在汉族人民中有口皆碑,在她出塞后生活过的内蒙古地区,至今青家常存,香魂犹在,当地人民经常到昭君墓前祭祀,祈望昭君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吉样,这也充分说明昭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这三位美女,或屈死袋沉,或长眠塞外,或随清风明月而去,但人们对她们的怀态和热爱却是永恒的,这能说毓们“薄命”吗?
那么,倾国倾城的杨贵妃,终于招来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一厥不振,是否就是一些人所谓的“祸水”呢?这也不尽其然首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唐代统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于政事,生活腐化奢侈,宠臣当政,使得社会矛盾激化等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而非因一女子而起。贵妃本是不预政事之人,假定她进宫以后,玄宗仍如前期那样励精图治,不懈政事,进取之心不减的话,能出现天宝末年的事变吗?显然是不能出现的。
诚然,天宝乱政与杨国忠专权有很大关系。但要看到,杨国忠受宠于玄宗,大多是因其办事精明、善于钻营所致的,并非单靠贵妃恩德所至。果如此,杨括、杨铸和贵妃关系比杨国忠与贵妃关系亲近得多,为何不见进用,却委政一个和贵妃关系疏远、推恩未及的杨国忠呢?当然,不是贵妃的裙带关系,杨国忠就无由得见玄宗,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法施展,这一点上,贵妃是脱不了千系的天大本事也无法施展,这一点上,贵妃是脱不了千系的人抢过来,满足他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的私欲,这对杨玉环本身就很不公平。这点,这个老统治者和他身边的人倒也能够体察,在马鬼事变中,他们都认为贵妃无罪,杀她不过是为安将士之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证老统治者的安全。后世好事者不察,一谈“安史之乱”,不把祸根找到玄宗头上,却硬要把一个爱害人说成“祸水”、“贼本”,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再次,作为一个杰出的舞蹈艺术家,杨贵妃对中国舞蹈艺术的贡献也不可低估。她善舞胡旋,加强了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她编排的《霓裳羽衣舞》是当时最著名的大型集体舞蹈,直接推动了盛唐舞蹈艺术的发展。她痴爱歌舞,尊重歌舞艺人,能平等对待、热情奖掖有成就的艺伎人员,她创办的宜春院培养出了许多诸如谢阿蛮、张云容之类的一流舞蹈家,在当时演艺界形成很大影响。虽然,这些都是在唐玄宗的支持、赞同下进行的,但具体施行者却是贵妃。这些不仅对唐代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舞蹈艺术发展史上,也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和平民老百姓心目中,对杨贵妃其人还是爱大于恨,以爱为主约。
《长恨歌》之所以风靡大江南北,人人争先传唱;东渡日本之说很快被人们接受,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样一种态度。“祸水”之说难于成立上述三点,是我撰写这本历史作品时的一些基本动意和所采取的方法,希望能得到方家指正。
纵观中国历史,有闭花羞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者何窗千百。夏莱妹喜、殷纷姐己、周幽褒姐、汉宫武帝李夫人、成帝赵飞燕以及改唐为周,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媚娘,哪一个不是倾国倾城的绝代美色?何以中国人民偏偏选了上述四位女性作为中国古代美人的杰出代表,这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美人之美的价值取向,肯定了她们以美对历史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四大美人的偏爱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四大美人的偏爱。
历史名人是宝贵的社会财富
所谓历史名人,就是指那些曾经闻名于世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或者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或者是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古今中外,历史名人总是受到人们的推崇和爱戴。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说不尽的故事,数不清的人物,谈不完的话题。上下五于年,风云变幻,人才辈出,既有雄才大略的领袖、运筹帷候的谋臣,又有驰骋疆场的英雄、多才多艺的贤士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为世人津津乐道。左丘明著《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编蛋通鉴》,无非是想借古论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多述古今名人在历史上的作为。历史名人,是历史所流传给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
首先,历史名人是重要的人才资源。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是名人的历史。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齐担公得管仲以称霸,秦始皇用王亥而六合诸侯,刘邦有三杰而灭项羽,汉武帝任霍、卫以定句奴;再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咸、元士祖忽必烈、明太祖未元璋等等,无不因得到匡世奇才而成功。
我们研究历史名人,也就是研究他们成功或失败的过程,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从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资料。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人才的论述。如春秋时期祁奚主张“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战国时吕不韦主张“求人勿全”;汉朝奇才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因为“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应该“举大德,赦小过”。后世如东汉的王充,三国的诸葛亮、曹操、刘动,唐朝的魏微、韩愈,宋朝的秦观、司马光、王安石,明朝的黄宗羲、颓炎武、王夫之。清朝的魏源等人都有专门的人才论著。
总而言之,研究历史名人的事迹和思想,就是考察人才的历史和探寻人才资源的过程。
第二,历史名人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上古三皇五帝,虽是传锐中的人物,却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象征;孔子编《诗经》,述《论语》,开设私学,有教无类,却创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体系偏;家又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其他如老子、庄子、孙子、垦子、韩非子、荀子、孟子、管子等等,他们的忍想也被不断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著称于世的人物,或者是社会政治的核心,或者是社会的栋梁,或者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不一而足。不过,在他们的周围都能够聚集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共同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些人物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依托,他们必然是整个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柱。第三,历史名人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旅游资源。古语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黄陵虽处偏远僻壤之处,却名扬海内外,炎黄子孙一心向往,无不以度心朝拜而为荣;曲车虽为山东小镇,却吸引了无数游客竞相游览。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有黄帝、孔圣埋在那里。至于那些名山名胜、古迹故地,更有许多和名人有关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故事,名胜古迹才显得更神秘,更有生气,从而吸引更多的探访者。
所以说,研究历史名人,探寻历史资源的优势,从而开发它,利用它,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程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并利用这一份宝贵的财富呢?历史上的名人成千上万,如果一个一个地了解,显然不可能。这些年来,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人物,而且把焦点集中在皇帝、后纪身上,这是可喜可贺的事。但是,要真正地了解历史,就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历史人物的秘密。于是,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千古数风流丛书》。
这套丛书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范围,以历史上著名人物为主要对象,不分朝代限制,不限有无官职,不论地位高低,选取那些早已约定俗成的人物群体,如三皇五帝、四大美人、春秋五霸、六君子、竹林七贤、八大神仙、大历十才子、中华二圣、汉初三杰、五虎将、唐宋八大家、香山九老、十三太保、十八学士、二十二子、二十四孝、云台二十八将、孔门七十二贤诸如此类他们虽然早已闻名于士,但仍有待进一步宣扬。因而,我们本着普及历史知识的宗旨,以正史记载为主,广泛搜集有关野史、笔记和小说及传说的资料,融汇贯通,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从而使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又生动活波。希望他们能够受到广泛的青睐。
张宁
199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