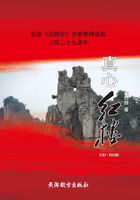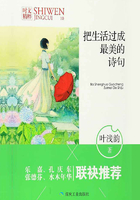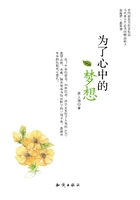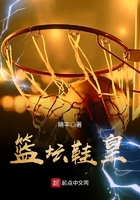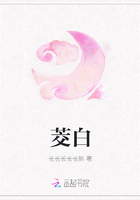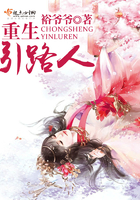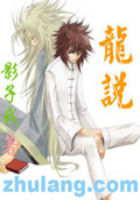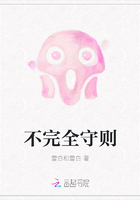【采访手记】8月间,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来蓉发表关于“大学精神”精彩演讲。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实力派学者一直颇为引人注目——他成名甚早,著述颇丰,研究领域很广,本都是一个人最该自得之处,他却从不张扬。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了他,他的安静简朴叫我们着实领略了一代优秀学者的风范……
李兵:您曾经主张一个学者应多坐书斋,不要做学术活动家。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里,你认为这个主张真的可取吗?几年前,余秋雨教授在谈到学者是应该死守书斋还是应该走出书斋时,观点似乎与你迥异……
陈平原:几年前,不记得是在成都还是在西安,余秋雨接受一个采访,引起争议。采访中,记者说到钱锺书的固守书斋,余秋雨则主张学者应该走上电视,认为现在的学者不应该再像以前那么做。这篇报道出来后,引起一场风波。很多人批评他,认为他不该对钱锺书先生的选择说三道四。后来余秋雨做了一个辩解,称当时他说的不是钱锺书,而是陈平原。批评我毫无问题,而我成了替代品,也很光荣。
你感到我与余秋雨先生有区别,这没错。在当下中国学界,我大概属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学院派,也就是比较强调学院本身的自律和学院本身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现在传播媒介变了,学者和大众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包括上电视、写专栏、做演讲等。学者可借此影响社会。但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首先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
上电视、写专栏、做演讲等基本上都是学术普及工作。对一个学者来说,最本位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学有余力,再出来做文化普及工作。作为一个学者,我自然更看重自己的专业研究。但跟一般专家不同的是,我同时也写学术随笔,即介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小文章。
余秋雨的意义,在于他在一个学术转型时期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用恰当的文体,把大众的趣味和学者的眼光重叠起来。他已经是著名作家,基本上走出学术圈了。学界现在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余秋雨是一个学问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散文家。虽然北大学生对他的散文有很多批评,但你必须承认,他完成了一个转型,成了大众文化时代的英雄。这句话本身,其实有褒有贬。因为对一个学者来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走到这一步。
专业研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代一代地积累,最后才能有一个大的成功和突破。所谓专业研究,就是很多专家固守书斋,穷其一生,做三两件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尊重这样的学者。比如有些做古文献的,一辈子就研究一两本书,但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作为台阶让我们一步一步往上攀登。而散文不一样,散文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学者的专著和散文家的集子,是两回事。现在因大众文化力量很大,电视以及其他媒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更愿意强调学者应该坐稳自己的冷板凳。
我来之前刚好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演讲,讲到现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有一种无端的骄傲,因为受众很多。我并不这么看。短期内媒体确实很有号召力。但放长视线,学术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更为深远。现在是大众文化时代,就像超级女声一样,是用掌声多少来计算得失成败的。但请记得,文化盛衰不是靠公众投票决定的。判断价值的高低,这标尺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也可以这么说,学术文化的发展,靠一批有心人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往前推进。对于这些人的工作,我们更应给予关注,即便他们和大众隔得很远,很多人根本读不懂他们的东西。做媒体工作的,有责任当好二传手,把专家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向大众传播。大部分的文化随笔,起的也是二传手的作用。我把二者分得很清楚,比如,我的专业著作在北大出版,学术随笔在三联出版,二者分工不同,各有各的受众。
马雁:你刚才说到专家的研究在平时得到的关注很少,但是在电视台等媒体访谈的时候,却容易得到更多的掌声和回应。你觉得这样的掌声和这样的回应的质量怎样?
陈平原:要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需要被大众理解,上电视或做专访是必要的。但不能太被这些掌声所陶醉。如果你以为公众掌声代表学术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欣赏的,不太可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比如北大评职称,是不太看重公众掌声的。你在社会上名声很大,不能保证你晋升职称很顺利。社会名声与专业贡献,是两回事。
作为学者,我有专业上的追求,同时也有人间情怀。希望向公众传播自家思想或研究成果,这个时候,我晓得在哪个场合、用什么姿态发言,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必须学会自我控制,不能沉湎于此。整天上电视,那就变成新闻从业人员了。现在学者明星化的倾向很严重,这让我有点担忧。很多原本做得不错的学者,一转身成了电视明星,回不来了。在电视上根据节目需要,说各种大众能够听得懂,却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话,这不是学者的主要责任。
马雁:你刚才说了,在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可得到读者的回应。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回应呢?你或许希望传媒更多地向大众传递学术信息,可大众传播本身是非常商业的,它会自己去寻找那种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
陈平原:那我就拒绝进入这种游戏。在北京工作,偶尔也接受媒体采访,但不是所有报纸和电视我都愿意上。话题必须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不能说太外行的话。稍为出了点名,媒体什么问题都来找你,你胆子也够大,不管懂不懂,什么都敢说。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万金油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没有专门研究,或没有几分把握的,我会坚决拒绝接受采访。
马雁:也就是说,你会坚定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陈平原:是的。偶尔接受电视采访,我也会问对方,你想做成什么样的节目,需要用我多少分钟的镜头。你要半个小时,我讲四十分钟;你用十分钟,那我就十五分钟。之所以不愿意多说,因为素材太多了,编导会用公众的趣味来加以剪裁。最后结果很可能是,我想说的都没有了;你保留的,都不是我特别想说的。
马雁:你对大众说话,但是媒体却用大众的趣味来修改你,让你成为一个能够受大众欢迎的人。
陈平原:所以我不愿意这样做。你可以说是爱惜羽毛,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护一个学者的独立与尊严。比如,你提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或根本不想回答,那我就直说了。这没什么,因为我不靠这出名。专业研究是我的主要着力点,至于传媒报道不报道,跟我没多大关系。有的人整天想着传媒会怎样看待自己,我没有这方面的顾忌。我甚至直言不讳,批评某些“主流媒体”无端的倨傲。我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可以说得很直率,不用看对方的脸色。
廖慧:你写过关于武侠的著作,但现在谈“武侠”显得新潮之时您却又闭口不谈了……
陈平原:这是媒体最愿意提起、而我又最不愿意接招的。因为,大概十多年前,我很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大学里讲关于游侠的专题课的。但成为潮流以后,我就不愿意再搀和了。我之所以谈游侠,因它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化精神。只谈儒释道等大传统,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国文化。中国老百姓的思想、观念、感情、趣味等,很大程度受制于民间信仰、民间传说、民间文化。20世纪90年代初,我花好多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游戏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廖慧:你主要是从研究的角度探讨这个现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武侠中的侠义、血气等已经融入到了你个人的个性之中呢?
陈平原:作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积淀及艺术想象中的产物“大侠”,寄托了中国人独立不羁的追求,以及那种自由思考、独立表达乃至快意恩仇的愿望。侠客本身也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内涵。我喜欢游侠,愿意花时间从《史记》一直讲到当代武侠小说,这样一个学术课题的选择背后,是有自己的情怀的。但要说因研究武侠而变化气质,则没有那么明显。
李兵:从你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你好像认为传统的、主流的话语圈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是偏低的。你觉得对于武侠小说而言,究竟怎样一种评价才是相对公平的?
陈平原:你说的是现代的武侠小说吧。因为,古代的侠义小说早就进入了文学史。以前我们对现代武侠小说评价偏低,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属于通俗小说。这是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的,把通俗小说看成边缘性的东西。现在不这么看了,谈现代中国文学史,一般都会涉及30年代的张恨水或60年代的金庸。应该警惕的是另外一个偏向,那就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反过来把金庸说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不对的。武侠小说是一种类型化写作,再有才华,还是受限制。你可以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写得非常棒,特别了不起,但它们依旧是类型文学。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越说越伟大,越说越深刻,那是有问题的。
李兵: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一些预先的阅读期待。但是好莱坞电影肯定也满足了一些类似的期待。我们只要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武侠小说与好莱坞电影之间有很多的可比性。比如均要对暴力、爱情、个人英雄主义等进行赤裸裸的夸张颂扬等。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大众趣味的?
陈平原:武侠小说的功能,确实像你说的,跟好莱坞的警匪片、灾难片等类似,满足了人身上一些潜在的欲望。以前我们只说升官发财是欲望,其实犯罪、嗜血也是一种潜在的欲望。现在不能随便杀人了,那我们就看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看大侠是如何惩恶扬善、虐杀大坏蛋的。人有宣泄的本能,可以理解,但不该说得太崇高。
李兵: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名字叫《多事不过陈平原》,你看过这篇文章吗?你是怎么看待别人对你“多事”的评价的?
陈平原:这文章是在为我说好话,是一个进修教师写的。大意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每过几年,我学术上就会有一个变化。而这变化本身,总会引领后面的学术潮流,很多人跟着做。有的课题做到一定程度后,就是重复生产,只有量的增加,不可能再有质的变化了。这个时候,不愿意自我复制,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做得好,借用自然科学的话,就是建立新的学术范式;退而求其次,那也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正因为有此野心,某课题做得差不多,就不做了。比如谈武侠小说,写了那么一本书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再做也就这个水平,只是量的增加。说“大侠”不敢,只是有一点文人气。做学术研究,功力及汗水之外,同样受个人性情的驱使。我在北大工作,条件比较优越,很早就不受各种评鉴的影响。我又没有仕途上的追求,不想当校长或部长,因此,可以把学问做得很有趣,也很开心。
(初刊2005年9月4日《成都晚报》,原题《陈平原:我不是万金油》,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