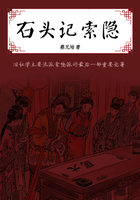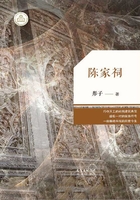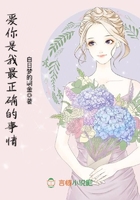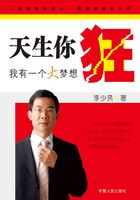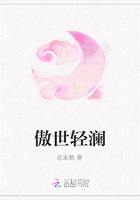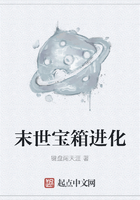与编辑界的前辈相比,我的编龄不算长,参加编辑工作的时间较晚。
我是1980年加入到编辑队伍中的,那年我已46岁;2000年66岁从被停刊的《读书人报》总编辑岗位上卸任后,离开编辑工作,走出稿件堆积如山、摆设零乱,隐隐散发着油墨味和烟草味的编辑部。
我多么怀念那种并不美妙的油墨味和烟草味啊。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最怀念的是在《花城》文艺双月刊工作的前十年。这十年我以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社分管《花城》的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一直参与及主管《花城》工作。那是《花城》创刊的十年,那是《花城》最不平静的十年,也是刊物和它的编辑部艰难奋争的十年。开放改革伊始,开放与反开放,“凡是”与“反凡是”,前进与倒退在激烈地反复较量,在我们这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度里,必然反映到《花城》这个当时已颇有些名气,在全国被称为“四大名旦”的文艺刊物上来,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上来。在中国,文艺从来被看作政治的晴雨表,这些政治上、思想上的较量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花城》那个杂乱但却紧张的小小编辑部里。《花城》坚持开放改革,不断冲破禁区,不断向旧观念挑战,不断为文学回归它的自身规律呐喊,这不能不触犯一些人,也不能不与当时的一些规则发生冲突;加之内部的观点分歧及一些无谓的争论与误会,闹得编辑部内外交困,几乎没有风平浪静的日子,动辄得咎,批判、指责、诬告,将我和两位《花城》前领导描绘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所幸,当时的省委领导任仲夷、杨应彬等同志,在对我们批评、提醒、劝慰的同时,用他们无畏的肩膀和宽厚的胸怀为我们遮风挡雨;许多作家,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等,也为我们呼号和辩护,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人对我们这个小小编辑部都怀有善意,冷漠与敌视常常带着刺骨的寒冷向我们袭来。我在编辑部的一张小铁床上住了五年,周末办公楼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像一片海——一片寂静的茫茫无边的死海,我似乎被抛上孤岛,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不期而至。
但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放弃我们的文学理想!我们坚持住了!
二十年之后的2008年,当时的编辑部负责人朱燕玲要“抢救”《花城》的历史,带着编辑申霞艳和李倩倩来找我,我口述,她们记录,后由申霞艳整理编写成篇,我再加以修改校订,是即为《风雨十年花城事》。在叙述《花城》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常常夜不能寐。一个个与我一起奋争的同事的面影在我眼前飘过,一个个作家的面影在我眼前飘过,多少风雨声,多少欢笑声,一一在摆动的窗帘上飘动。往事如影,但毕竟不是幻影,它将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风雨十年花城事》也许只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的一个插曲,但它确有许多引人回味引人深思的地方。今天,它得以出版应感谢许多人,特别是将我的口述整理编写成篇的申霞艳教授(当年的编辑早已成了教授)。
这本集子里还有几篇写改革开放的文字。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如今谁都不能不承认,即使是一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仍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并非没有倒退的危险。我的几篇报告文学,记述了一些为改变国家面貌勇于创新、不断奋进的人们,也算是为改革开放留下一些侧影。
特别要提的是本集最后一篇:《中国民主第一人——寻觅孙中山的革命足迹》。此篇原为我与章以武教授接受广东电视台和广东中山基金会的委托,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编写的电视专题片,由我执笔。我自幼就听老师讲过少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破除迷信的故事,讲过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故事,对孙中山先生崇敬有加。参加革命后,虽多次听过“孙中山批判”之类的讲话,也看过一些贬低孙中山的书刊,但我坚信不管他有多少缺点多少不足多少失败,他是号召推倒两千年帝制的第一人,是在中国最真心实意建立共和国的第一人,是最先而且百折不回地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第一人,因此,这种崇敬更是不可动摇的。我认为,说他是中国民主第一人,既不过分,亦非虚夸。
范若丁
2015年12月29日于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