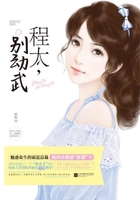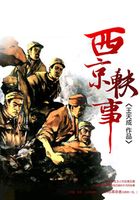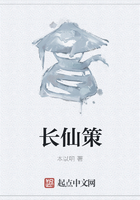李敬泽
读《问青春》,认识了张闻昕,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十一岁时,她写过《细菌国王秘密日记》,找出来看一遍,看出这孩子心细而有大志,细到了、大到了在显微镜下打一片江山、创一个王国。如今,写了这本《问青春》,她长大了,作为写作者的张闻昕获得了神奇的加速度,远超过她的年龄,她已经不是个少年才女,而像是气象不凡的作家,临近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子那些事,竟被她写出了人间辽阔、人情丰饶。
这是另外一种“青春”书写。我本以为会看见阴郁、孤独、冷酷、愤怒,书店里有太多此类拒绝走出青春期的“青春文学”,其中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市场的复杂机制,此处也不必细表。而《问青春》的青春却不是被指认、被订制的“青春”,不是姿态和表情的“乌托邦”,它越出了大众文化的成规,它被张闻昕还原为生活。
成规化的青春书写必须偏狭,必须不公正,它必须对人类生活做出粗暴删减。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拒绝领会父母的苦衷、他人的道理,他深深地沉溺于自己,封闭于内部,兀自委屈和悲伤——这并非多么不正常,而张闻昕,这个二十岁的写作者,她当然是站在青春的内部,站在自己的青春里,但是,这没有阻碍她对他人的好奇、探究和理解、体贴。她的青春不是拒绝对话的青春,相反,在她的笔下,青春之盛大正在于向着他人、向着世界敞开。《问青春》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那些孩子们之间、他们和成人之间热烈的对话,“问”青春,也是“问”世界,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甚至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问答的过程也正如小说所写,充满了困难、误解和伤痛,但是,正在这热烈的对话中,青春成为了向着更广大世界、向着未来的探索和成长,也充满欢欣和希望。
这就是艺术上和人生观上的“公正”,有这样公正眼光的小说家,看到的“青春”就不是符号,不是某种表情或姿态,青春本身就是一个生活世界,而生活是多么的难以界定,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不可封闭。看得到这些,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
而张闻昕正好有这样的禀赋。是的,我认为这样一种面对生活、面对众生和众声的公正,这样一种既辽阔又贴切的眼光对小说家至关重要,在很多作家那里,这种禀赋严重匮乏。他们远比张闻昕更有名,却很难说他们比她更成熟。当今小说中,很少见到《问青春》这样的气象:大大小小的场面纷至沓来,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场面推动,这是在人间,这是人走进和拓展他的世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呈现自己。《问青春》中充满活生生的人的关系,所以必定是有声的、说话的,众声喧哗,话说得热闹。——这些都使我想起中国古典小说和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传统,这也让我想起现在很多“纯文学”的小说:小说家不让他的人物开口,他一定要让人沉默,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啊想。那是形影相吊,是厌食和自闭,既不吃饭也不交际,拒绝与他人对话,人被切割封闭在一种被观念界定出来的“私人生活”里。他们由此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眼光和能力:在人间、在人的整全存在、在人和世界的全部关系中认识人、想象人、塑造人。
很多小说空旷无人。而《问青春》里有那么多的人,有名有姓的几十,性格鲜明的十几。张闻昕似乎是不太费力,她兴致勃勃,她是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肖像画家,她确信,人和人不一样,这种使人间变得如此有趣的差异,既是出于天性,更是出于家庭、环境,出于种种个别条件的复杂作用,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面临的考验,正在于把“这一个”、把一个个的“这一个”辨认出来、刻画出来。
说来容易做到难,张闻昕竟然做到了,她表现出在这个年龄很少能够达到的准确和娴熟。可能是,她的心里本来就有这么多的人,她对他们满怀兴趣,她用显微镜仔细研究他们。与此同时,掌握显微镜并没有使她变得骄傲专横,她爱他们,她分享每一个人的“秘密”和“真理”,怀着惊喜、敬意。
——我不想掩饰我对《问青春》和张闻昕的惊喜。在这个夏天,因为工作,我看了很多小说,深感厌倦。对抗这种沉闷和厌倦的办法是,一边看小说,手机里一边放着相声。小说看过了,未必记得多少,段子倒是记了不少。有一句话,叫做“祖师爷赏饭吃”,演员说起来顾盼自喜。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天赋”,有人就是天生该吃这碗饭的,没什么道理,你气死活该。说相声是如此,其他事也是如此,比如写小说。张闻昕当然还小,前路漫漫,还得不懈努力,但是,一部《问青春》在眼前,一边看着,一边忍不住暗叹:果真是梦中携回一支笔,细写世间万般情!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