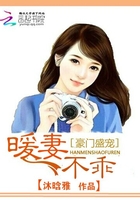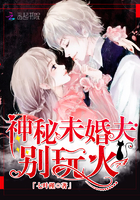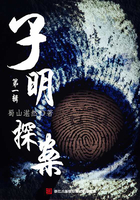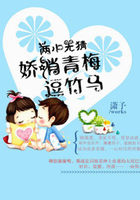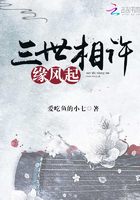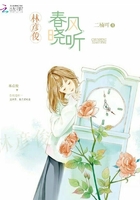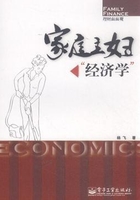“怎么,想不明白?那就自己先琢磨,饭后你还猜不到,再来问我。”
张维安说完,挥手让李夏站开点,不要影响他欣赏对面的墙上挂着的书画作品。
“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
这句诗用狂草书,做了横屏。字是标准五三五不等分的结构,启功先生独创的字体。他曾在某个拍卖会场见过一幅一模一样的作品,他记得当年是养父高价把它拍了下来。没想到时隔两年,会在这间房里又看到这副字。
这不会就是养父当年拍的那幅,启功先生的草书真迹吧。
张维安仔细品了品,这运笔的习惯,字的神韵,还有那印章。
没想到呀,启功先生的真迹,真挂在了一个小饭店的包间里。
想当年养父拍了这幅字后,他还随口问过,怎么不挂出来欣赏。养父说送人了,他还调侃了一句,不会是送红颜知己了吧。只有才貌双全,阅历丰富的才女,才配得上这份礼物,可别明珠暗投。当时养父听到他这话,象想起了什么有趣事,脸上表情荡漾,明显是春天来了的模样。
今天他才发现,当年的打趣成真。这幅字真是送给了红颜知己。不过,不是他以为的才女,而是常冬梅这个无脑妇人。这字在这,还真是明珠蒙尘。
李夏看着张维安老盯着那张字看,就带着取笑地口气问道:“这上面写得是哪两句诗,是诗好,还是字好?是大师的真迹吗?”
“诗好,字也好。这幅字挂这,以后在此厅吃饭的人,都可以加收百分之十的文化服务费。”
“啊,难道真是名人真迹?”
“书画界有北启南张的说法,这幅字,就是被称为北启的启功先生所写。启功先生,华国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雍正帝九世孙。长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京都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华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你说他的字,算不算名人真迹?”
这不可能吧,她家装修支出里可没有买名人真品字画这一项,难道真的捡漏了?这得运气逆天,可能吗?李夏还没来得及提出自己的疑问,就听到妈妈常冬梅的声音。
“这幅字,不是启功先生的真迹,是赝品,真的。启明,你看又有人把你送的这幅字当真迹了。这幅字仿得太好,有许多人人都误会这是启功先生的真迹,我跟他们解释这是赝品,人还不信,非要出钱跟我买。”
没想到,妈妈在张启明身边,说话声音是如此地欢快娇俏,象十八岁少女。
常冬梅轻快地走进梨花厅,看到站在梨花厅角落的李夏表情明显一楞,神色有些慌张,看了身旁的张启明好几眼才勉强稳住。
她轻声说道,“夏夏,你先来了!刚刚那位是?”
李夏颌首示意,说道:“妈,张伯伯,你们请坐。妈妈,这位是张维安,张伯伯的儿子,我听他说我们两家中午聚餐,就和他先过来了。”
“啊,启明,你儿子今天也过来,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糟了,我都没准备见面礼。”
张启明轻拍常冬梅的手,安抚地说道:“没事,我们家没有这些讲究。今天把孩子们都叫过来,一是想着我们两家人互相认识一下,把我们的关系正式向孩子们做过交待。二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安排,看孩子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张维安也很礼貌地说道:“常姨,你好。您叫我维安或小安,都行。我们家就只有我们父子两个,我已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不能常常陪在父亲身边,一直担心他孤单寂寞。如今好了,以后有阿姨您陪着他,我也放心了。我听父亲说,您做的菜特别好吃。每次他从华国回去,都会和我说,这次您又做了什么菜,色香味俱全等等,每次都听到我特馋,直掉口水。常姨,您今天做几个拿手菜当我的见面礼,行吗?”
“你这孩子,真会说话。只要你喜欢吃,阿姨什么时候都可以为你做。”
常冬梅边说边注意着李夏的脸色,这个女儿十分地聪明伶俐,一直来都让她很省心。就是一点不好,女儿太强势能干了,她在家里就比较没有权威,话语权很小。家里许多事都是女儿做决定,她听从。如今她背着女儿谈男友,到准备结婚才告知女儿,女儿会不会很不高兴,她要是反对怎么办。这让她很不安,心里有点发怵。
这样笑容满面,温顺纯良的张维安,看得李夏眼前一花,真是一个又乖又帅的好儿子。张维安这个千面狐狸,他要是真心想讨好谁,还真是手到擒来。
跟张维安比,倒是妈妈常冬梅更让她吃惊,她就一晚上的时间没见妈妈,就感觉她整个人又有了很大的不同。那种由内而外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住。张启明那个人就有那么好吗?强势阴险,而且跟着他明摆着今后不可能在中国常住,她这次倒不怕了。
看着李夏站在那,板着脸没做声,常冬梅面露尴尬,手足无措。
张启明见此情景,不乐意了,他直接问道:“李夏,你愿意接受张伯伯和你张哥,做你的家人吗?”
说完,他又拿眼神瞟了一眼张维安,无声地问他,这小丫头你真的搞定了吗?
李夏不得不出声表示乐意,她很敷衍地说道:“怎么会,只要我妈高兴,张伯你也是真心对我妈好,我哪会不愿意多两个家人。妈,你去厨房看看,给张哥露一手,把张哥的胃抓牢了。以后家里有什么事,让你与张伯伯有了分歧,到时候我们三票对一票,让张伯伯听你的。”
常冬梅听李夏这么说,脸上笑开了花,嗔道:“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男人是一家之主,家里的事当然听他们的。启明,小安,夏夏,你们聊,我去炒菜。”
常冬梅刚出梨花厅,张启明、张维安、李夏三人脸上的笑容,同时消失,气氛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维安,你怎么来华了?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此时的张启明,不再是常冬梅面前,那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身上多了些铁血杀气,一种历经磨难,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气韵。
“是有点事,我觉得还是我跟您说更保险。您进联合政府的事,已经确定,最迟一个月后肯定会宣布。我觉得你和常姨早点结婚的好,这对你的政治生涯有益处,也对常姨的安全更有利。我无意发现去世的李强,出身挺不简单的,还有些后续麻烦需要处理。我想常姨那,您老这次带她一起回缅甸,平常注意点,问题不大。李夏这,我来管。您放心,我不会让她的事影响常姨的心情。不过,常姨在华的产业不能留了,全部处理了吧。”
张启明意外地多看了养子、继女两眼。
没想到这个很独的养子,会在意继女的安危,刚接触,就把她扒拉到了自己的羽翼下,这小子又在算计什么。
算了,人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再没精力管闲事,只要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傻女人就行了。年轻人爱怎么扑腾,就怎么扑腾去吧。
张启明默默地点点头,父子俩就这样自说自话的达成了协议。他们谁也没想过,需要问问李夏母女俩的意见。毕竟是她们的未来生活,她们更有发言权和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