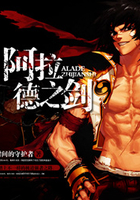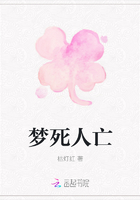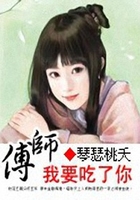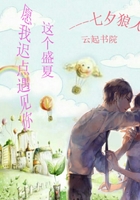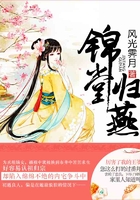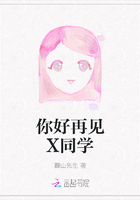元风张着嘴巴看着张杨,突然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你看”,张杨把望远镜递给元风,指着山梁上面说道:“高压输电线路上安装的都有监控、监测线路状况的辅助设备。昨晚的停电很蹊跷,今天他们检修的时候会重新给这些辅助设备更换供电系统。这些辅助设备都是利用高压输电线的电流进行感应取电,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获取电能。”
张杨眉飞色舞地说道:“利用高压输电线路感应取电是专利技术,关键点就在对输电线路电流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防过流。我需要验证这些供电装置的内部构造原理。今天他们更换供电装置后,旧的装置会被扔到变电所那边一个专门的垃圾箱里。我们搞两个就可以了!”
元风:“你要这些东西干嘛?”
张杨:“肯定有用,有大用,还记得我工作室里的那套感应取电设备线组不?有些环节的原理我还没确认。你帮我一起弄出两个来,我过会带你去我的秘密据点。这里是上半场,那边才是下半场的重头戏!”
又是秘密据点,元风暗忖道,上一个据点就害我在庆山没法呆了!不过,是朋友就该帮忙,废旧的设备弄两个也不犯法。
张杨估计得没错,铁塔上的工人确实在为那些装置更换供电系统。有一个工人把更换下来的旧设备塞进一个大塑料袋里,正往山下背。他俩赶紧跟着他,顺着树林往下跑。
他们尾随那个工人到了变电所外的垃圾箱边,等那人扔完东西后就开始了行动。元风负责警戒,张杨兴高采烈地翻着垃圾箱,不停地往双肩包里塞着“垃圾”。
这里紧挨着变电所铁丝网隔离墙。张杨突然发现铁丝网另一边的垃圾箱里塞满了一堆已经掉漆的黄色金属杆,立刻不淡定了。
元风:“还不走,看什么呢?”
“那边垃圾箱里的黄色短杆是跌落式熔断器,换了新熔丝还可以用,我那边也缺这个。但是……”张杨看看眼前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无可奈何。
元风瞅瞅四周,把身边那个垃圾箱盖好推到铁丝网边。他一跃而起,右脚在垃圾箱上一点,双手握住铁丝网上方的一个固定横杆,腰腹一发力,一个空翻跳了进去。他挑了几根品相好点的熔断器从钢丝网的网孔里塞给张杨,然后悄无声息地翻过了铁丝网,和张杨拔腿就跑。
两人翻过一个小山坡才敢停下来。张杨向元风竖着大拇指,“元风,你还会跑酷!太牛B了。万事俱备了,走,咱们去花石洞。”
一路上,张杨开始给元风介绍镇上的地理。
这兰溪镇也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盆地。西边是闹市区,接着进山出山的公路,再往西连着其他几个乡镇。西边人口相对集中,菱角沟,司马台这些地点正在被当作风景区开发。东边再往外走,过了几道山脉就是库区。这里平地和山坡上遍布农田、茶圃、桑园和果林,这片农业种植区面积较大,和库区边的锅棚店子、杨河湾连为一体。
兰溪向南连接着离山深处,这里的群山海拔陡升,分布着几条大裂谷,如虎林、薄刀峡、喇叭凼,都是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之处。南边虽然有几个大林场,但自古交通不便,尤其是冬天,只要一降雪便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兰溪北边水源众多,那晚元风夜探的河滩叫做凤凰滩,再往东北就是大泥坑和白龙荡。
在凤凰滩和花石洞之间,元风发现了一个练跑酷的好地方,叫做蚂蚁岗。这里方圆十余里皆是荒山野丘,且树木不多。灌木丛间布满了奇柱异石,有聚有散,有起有伏,地形一路向东逐渐升高。相中这个地点之后,元风心中狂喜。
花石洞在白龙荡山势渐起之处,从山路边一条岔道往里。这条岔道比山间的主路还宽,但长满了野草。岔道尽头堵着一座荒山,正面是一面高大的石壁,山脚下的灌木极其茂密。
看似无路了,可张杨偏偏往这片灌木丛里走了进去,越走越深。曲径通幽,不一会儿二人竟绕过了石壁,荒山后面现出一个巨大的山谷来。
张杨熟门熟路,带着元风七拐八拐,沿着一条不易发觉的小道进了一片树林。
元风发现这里的环境不简单。
过了树林眼前就现出一条十米宽的大路来,路上铺的沥青历时太久已经粉裂,路面已被各种野生林木和杂草占领,路两边都是几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这种树木可不是离山原生的,元风记得同样的场景只在庆山县老县委会门前的那条大道上才见过。
路的尽头是个能并排走四辆大货车的出入口,被大铁门紧锁着,两扇门板之间已被焊死。门边的水泥围墙上还围着一圈铁丝网,从铁门和铁丝网生锈的程度来看,这里已荒废了几十年。
张杨顺着一侧围墙往东走,在围墙边干涸的水渠里翻开一块旧门板,门板下面露出一个缺口来。二人钻过围墙,再走两步,一个长满灌木的大广场就出现在他们眼前。广场上铺满了方形的水泥砖,中央有一个废弃的花坛,里面还摆着一个巨大的假山。
广场东边有几排四层住宅楼房已被拆除,只有一栋还保留着一层,墙面上已爬满了藤蔓。西边和北边的建筑都拆完了,只剩下几个规格不一的钢筋水泥入口。从巨大的廊柱和用五星团装饰的顶部可以看出这里曾经耸立的是一栋栋雄伟的前苏联式建筑。尽管已是残桓遍地,但元风依然能感受到这里曾经的壮观与威严。
他俩绕过北边那栋建筑的基地,就看见一个带着超高顶棚的仓库入口。仓库就建在山崖边,门头上有一个巨型五角星。山崖上还能望见一个高大的红砖烟囱的底座。
张杨走上一堆烂砖头垒的台阶,带着元风从一个窗户翻了进去。这里面堆了很多高大的木箱,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仓库内飘着一股淡淡的机油味。
二人径直走到仓库最后边,山崖的石壁上有一座弧顶的铁门。门上当年用红色油漆写的两行大字依然清晰。上面一行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中间一行大字写着“金光机修厂7车间”。
铁门边有个盖着篷布的大台面,张杨把双肩包放在了台子上。
门没上锁,被他俩用力推开。门内十米处有一堵水泥敷面的高墙,墙面上用书法体写着“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高墙两边各有一个入口。
一路上张杨都没说话,元风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元风知道,这里肯定是张杨特别熟悉的地方,虽然这里已经破败了,但可以看出几十年前这里可以容纳几千人工作和学习。他不知道张杨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但肯定和今天他的“重头戏”有关。他说这里是他的秘密据点,这个据点的规格比金光路8号高了太多。
很奇怪,这里也叫做金光,难道老唐当年收的门牌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
他俩走进入口,7车间里黑乎乎的。张杨打开强光手电,元风看见整个车间位于一个空旷的自然洞穴里。这里的地面做了处理,还用水泥修了几条基座,远远的尽头看不分明。
张杨:“这里没电,过一会儿通了电才能看得清楚。”
元风:“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
张杨:“这里原来是个大厂,对外叫金光机修厂,对内叫做‘579厂’,建于1967年,是个三线工厂。厂里最多时有三千多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撤完了。579厂分成了三个厂,全搬到省城去了。金光厂最早是攻关和仿造苏式坦克的传动系统,后来专门生产东方红系列拖拉机的传动装置。这儿原来就是制造、组装拖拉机离合器和传动轴承的7车间。我爷爷在哈工大读的电气机械工程,后来去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动力机械制造,解放后在东北工作,1970年到这里任动力机械科总工,1985年退休。这里在90年代被拆了两次,原来一共有大小7个车间,现在只保留了这里。我爷爷在这干了15年,除了我奶奶,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爸爸当时写信寄到东北,再秘密寄回这里,那一代人的生活我们现在理解不了。”
元风静静地听着,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前在这个山窝窝里发生的一切。
张杨:“小时候爷爷经常带我过来,这就是我们爷孙俩的秘密据点。7车间当时封存了不少进口设备,作为战略物资。可是这20多年来,我们的机械制造业发展得太快,这里的设备失去了价值,这个地方就被彻底地遗忘了。我没事就会来这里看看,你是我唯一带进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