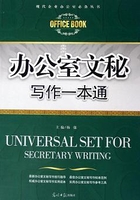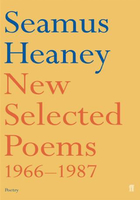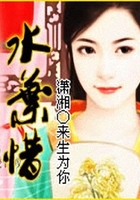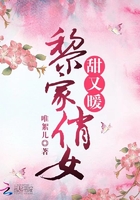美国医生特鲁多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在医学界广为传颂。
医生们往往都能理解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无论医学多么发达,在疾病面前,人类仍然有深深的无力感。
但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隐含着另外的意思,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代医学才刚刚走出婴儿期,对于那时的医生而言,所能起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简单地了解一下疾病史和医学发展史,会有助于了解医生这个职业。
一 巫术与人类早期的疾病观
汉字中的“医”字,在古代写作“醫”,这是一个会意字,由四个相互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匸(xi)、矢(shi)、殳(shu)、酉(you)。
匸,是一种按摩术;矢,表“砭石”;“殳”,表“针灸”;“酉”,表“酒”。
现代人对如上几种治疗方法多有附会,但医学史有自己的解释,即早期中国人的治病方法,大体上是按摩、石刺、针灸和喝酒。
已有的医学资料表明,酒发明以后,喝酒确实是先民们治疗疾病的主要办法之一。当按摩、石刺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酒就是最好的“药品”。
酒这个伟大的发明,在我们的先民那里成了药,用以治疗身心疾病。而不像希腊那样,酒成了一种获得生活快乐的饮料。
马克思·韦伯很遗憾地说,中国人没有酒神,所以,他们谨慎而冷静,且不爱管他人的闲事,也就是说,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热情。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先民谨慎地使用酒,把酒的好处发挥和使用,并使之与“医”结缘。
在酒没有发明之前,先民们主要的依靠就是“巫”。
我们的先民们在造字时,还处于久远的原始年代,人们对医的理解,主要是“巫”,即医术是巫术的一种,所以,那时的“医”字,是这样写的:毉。
驯化家畜家禽,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从此,这些家畜家禽可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营养保障,膳食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有了稳定的获取渠道,不必天天出发去狩猎。但在驯化家畜家禽的过程中,人类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这些动物身上所携带的一些病原体,如痘病毒、瘟热、麻疹、流感等,都会猝不及防地袭击人类。
“古人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经历建立对疾病的认识,如做梦可使人感觉似乎别人的灵魂能进入自己的身体,或观察到他人患病的过程,如癔病或癫痫,看起来也好像发作期间他人的灵魂能进入病人的身体。这种鬼神致病的观念在所有原始部落都存在,并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的早期。”
由于食物的匮乏、居住条件的简陋以及动物的威胁,先民们经常遭遇疾病的袭击,但为什么会得病,先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鬼神作祟;二是祖先示罚。
我们的先民们缺乏对疾病成因的了解,更缺乏治疗疾病的方法,在上古时期,先民们通常采用祭祀、诅咒等方法来治病,道理无外乎祈求祖先保佑和鬼神的宽宥,先民们认为,通过这些办法,疾病就会离开身体。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的隐喻具有道德劝谕和惩罚的意义。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和虚弱与疫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然后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来说不正确的事物。”
中国的先民们通过祝祷、祈拜、诅咒,渐渐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祛疾模式,由此“咒禁”、“祝由”等治病方法,成了先民们信奉的患病时通常采用的模式。
大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说,汤药、针灸、禁咒、符印和导引是医疗五法。因为普通人难以掌握,所以,这位大医编辑了“两卷,凡二十二篇”的《禁经》。
唐代太医署首次设咒禁科,与医科、针科、按摩科并列为医学四科。咒禁科设立咒禁博士和咒禁师,教授咒禁,使学生能用咒禁来拔除邪魅鬼祟以治疾病。唐内典卷四十“太医署”记载:“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隋太医有咒禁博士一人,皇朝因之。又置咒禁师,咒禁工以佐之,教咒生也。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
当然,光有祈祷和咒语,有时并不能奏效,所以,“巫师们在进行治疗仪式的时候,也运用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由此形成医药与巫术的互补,若病人服药后病愈,自然是法术灵验。”
有的学者认为,祝由后来称之为咒禁,即祝由和咒禁是一回事儿。
《黄帝内经》记载,“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另在《灵枢·贼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矣。”
清人俞樾在《群经平议·孟子一》中也说:“是巫、医古得通称,盖医之先亦巫也。”
有相关资料说,祝由之术全面地渗透到中医的每一科之中,但也有学者指出,祝由、咒禁之术,虽然在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有所记述,并经大医孙思邈给予充分肯定,但事实上,咒禁、祝由之术,后世一向由道家来传扬,精通这些方法的,也多为道士。
到了宋代,随着“儒医”的出现,咒禁、祝由之术渐渐被中医排斥出体系之外。梁其姿教授在《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一书中说,“手艺的”或迷信的,如针灸、眼科、其他外科技术和巫术。被主流医学排除在边缘的结果是,这些技艺在当时盛行的通俗传统中得以传播。
梁其姿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从公元2世纪以来,“许多重要的针灸学著作都由著名道家撰写并由道家教派传布。”
在那个时候,由于儒医成为医学界的绝对主流,眼科、针灸术、外科,已经渐渐边缘化。“现存金元针灸医家的生平资料表明,许多人同时又是炼金术士或用符治病的行家,还有一些则被明确地指认为是主流的全真派”。
梁其姿认为,从远古至六朝,巫、医一直密不可分。直到11世纪,“正如1023年和1025年禁止中国南部地区巫师治病的诏令所表明的那样,巫和医已被有意区隔。”
巫和医由此被有意区隔,但并未就此分别,从隋唐到宋元明几代,巫术都是受官方认可的治病方法,太医院里,都设有祝由科,由朝廷授予官职。
信巫术,是全世界先民们的共识。
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也像我们的先民一样,对疾病的产生有着神秘主义的看法。比如“认为所有的病痛都是由某些巫医所控制的石英石造成的。巫医的魂魄使石英石进入病人的身体里产生病痛,只能由另一个巫医用吮吸的方法将它吸出来,才能治好病。他们把自己的病痛都归咎于神灵或鬼怪。古巴比伦人相信疾病是因魔鬼所致,如魔鬼阿咂咂祖(azazazu)能使人的身体发黄、舌发黑,魔鬼阿萨库(asakku)导致虚痨症。《圣经》中有神直接降下疾病作为惩罚和训诫的记载:《出埃及记》4章6节说“上帝可使人患麻风和使人痊愈”。《列王记下》19章35节说“天神散布瘟疫,一夜间使亚述人死亡18.5万”。《荷马史诗》中说,阿波罗是鼠疫和各种瘟疫的传播者,但同时是驱除一切疾病的神。由于人们将疾病的原因以及祛除病痛的功劳都归功于神,于是在疾病得到治愈后就要去神庙献祭,向神灵表达感激。”
即使在今天,在中国城乡的许多地方,有病而求诸巫者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二 中医的勃兴
中医的概念,在今天已经窄化为某种具体的诊疗方式。
在上古,中医应该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道医、针灸、疡科、祝由、咒禁都在这个名称之下。
比如,唐代大医孙思邈,其实是个道医,他本人是一名道士,在道家的传说中,在百岁以后成了神仙。
战国时的名医扁鹊,也是一位道医——与孙思邈有所不同,扁鹊只是信奉道家的医者,在他的时代,只有道家而无道教。而孙思邈则是信奉道教的道士,在道教的名称系谱中,孙思邈被敬称为“孙真人”。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怀疑孙思邈那篇著名的《大医精诚》,并非孙思邈个人所写,而是宋元时代儒医兴盛之时的后人伪托之作——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常见,后世学者常常伪前代知名人士之名而作书,目的是传扬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怀疑有着合理的文化逻辑,《大医精诚》是一篇典型的儒医宣言,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正告医生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树立济世悯人情怀,把医生从治病的层面,上升到了治世的层面。从而,儒医也像儒家知识分子一样,拥有了道德的高度。而这一套儒家的思想体系,不可能由一位“真人”即道教的教士来说出。
但不管真正的著者是谁,都无掩这篇文献的光辉。
上古先民利用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创立了阴阳五行理论,这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医则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看待人体和疾病,从理论上,先民们把人体看成是气、形、神三者的统一体;从操作手段上,则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从药物使用上,先民们发明了中药。
上古时代的中医,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医学体系,尽管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但其完整的诊疗体系仍然需要后世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后世的医者们通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渐渐从阴阳五行学说演变成五行六气学说,后又回归于阴阳五行学说,由儒医占据主流话语权的中药,由道医和民间草医共同使用的针灸、跌打、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以及一部分巫医的香灰草药,共同构成了庞杂的中医治疗体系。
与中医有关的阴阳学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这句话——“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而另外一句“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则用人们易于理解的云雨生成过程,来论述阴阳的升降与变化。
梁其姿教授认为,五运六气学说为“宋代官方所推重”。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一》中说:“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
有宋一朝,此种学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当时有谚语如是说:“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其学术在流变中,有理论派、推算派、江湖派和大运气派等派别。
中医的兴盛,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大医的努力。
早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用中医的方法治病的医生就已经出现,且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两位,一曰医和,一曰医缓,齐国则有扁鹊。
在现有的文献中,医和最早使用了阴阳、四时、五行、五声、五色、五味、六气等中医病因学和诊断学的概念,“六气以阴阳为纲,而淫生六疾统于阴阳”的理论,对中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关于医和的故事。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生病,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去给他治病。诊断书是这么写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
什么意思?就是说晋平公因贪恋女色,已经病不可医。
《国语·晋语八·医和视平公疾》一文,详细地记载了医和与晋国大臣赵文子的对话:
出曰:“不可为也。是谓远男而近女,惑以生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诸侯。”赵文子闻之曰:“武从二三子以佐君为诸侯盟主,于今八年矣,内无苛慝,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对曰:“自今之谓。和闻之曰:‘直不辅曲,明不规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宠其政,八年之谓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
医和这一段话,主要论述国君如何端正自己的行为、大臣如何恪尽自己的职责,同时指责赵文子等不能直谏君主,以至于君主的身体和国家,都病不可治。
在这段话里,医和阐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后世持续地影响着儒家知识分子——医不仅及于民,更及于君和国。一个震聋发愦的观点由此横空出世:上医医国。
医缓是秦的另一名良医,《左传·成公十年》记载:“公(晋侯)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
有一句著名的成语,“病入膏肓”,就与医缓有关。从两个人的行医时间看,医缓是医和的前辈。
战国时代另一位著名的医生是秦越子即“扁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诊疗方法,即“望、闻、问、切”。
尽管有若干名医,但直至汉代,中医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治疗体系,也没有形成中医综合性的经典著作。医与巫,一直并肩而行。直到张仲景出,中医才有机会成为一座大山。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人。他公元205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
然而奇怪的是,张仲景在汉代声名不显,《汉书》、《后汉书》均没有他的名字,更没有他的传。
张仲景被后人所知,始见王叔和《脉经》序:“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从此以后,关于张仲景的身世及经历,被不断丰富及附会。今人多称张仲景为“医圣”,但有学者考证,金人刘完素的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里,第一次给了张仲景一个类“圣”的称呼,他说“仲景者,亚圣也”。至于“圣”是谁,研究者们的见解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医家的“圣”,仍然是黄帝。
1589年,中医错简派的创始人方有执在他的《伤寒论条辨》中,首次把张仲景升上“圣”坛,文中“……称仲景曰圣”,后世受此影响,亦渐渐称张仲景为“医圣”。
可考的资料证实,东汉大疫流行,张仲景家族200余人,竟有三分之二因瘟疫而死。近有学者发现,这次大瘟疫的流行,可能与西域通商与征服匈奴有关,简而言之,丝绸之路的繁荣,同时引发了瘟疫。现代流行病学认为,由于陌生民族间的互相接触,会把其他民族身上特有的病原体带入,从而造成瘟疫。
正缘由于此,张仲景才矢志学医,终于写就《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清代医家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到了唐代,大医孙思邈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其《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宋元两朝,尤其是元朝,儒医成为中医的中流。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参加科举,纷纷成为医生。
“儒医”与普通中医的最大不同,是把诊病体系书面化和知识化。梁其姿教授认为,儒医的出现,是由于理学的渐占优势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将部分医学“文明化”,即趋向强调理论、支持脉诊及开处方的医疗方式。这个传统涵括了许多古代医学经典和较晚近的文本,是由包括最具代表性的朱震亨在内的所谓金元四大家所建立。朱是位名医,并且是理学学者。
梁其姿认为,“这种儒医传统的确立,却是在排除了古代医学的某些方式上完成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由于“儒医”的出现,中医与巫术才渐渐分野。“自明代以来,这些被排除的方式被边缘化。”
梁其姿教授说,两宋以后儒家伦理虽然广泛渗透进了医学界,“儒医”作为一种专门的称呼亦逐渐为一般人,特别是精英人士所认可。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医”,其实是部分现代化的“儒医”,剔除了咒禁、祝由之术,传统“中医”业已不存。
三 成为正统的儒医
儒医在有宋一代成为主流医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大宋开国之始,太祖皇帝就命令编修了《开宝新详定本草》一书,刊行全国。
太宗皇帝即位后,以重医为推行仁政的重要手段,命令翰林医官五怀隐主持整理前代方书,用14年时间编成百卷本的《太平圣惠方》,并亲为作序,“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歉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贯在救民,去除疾苦。”
而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则把对医学的重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黄帝内经》与儒家其他经典一起,列为士子猎取功名的必考之书。同时,组织修订《本草》《局方》,主持编写了大型方书《圣济总录》。
有宋一代,医生也被授予了官阶,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仍然称呼医生为“大夫”或者“郎中”,这其实是宋代的医官名,“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成全大夫”、“平和大夫”、“保安大夫”为正七品;“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等为从七品。
医生从术士中分离出来,负有教学、医病等现实功能,构成朝廷管理职能的一部分,皇家对医生的重视,是儒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王安石对孟子的“圣化”,才是儒医产生的根本条件。
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曾写过一首诗《孟子》,来表达孟子对自己的重要性: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这首诗其实真实地反映了王安石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虽然有神宗皇帝的支持,但保守派的反对,也确实让他有一种“举世嫌迂阔”的孤寂感,只有孟子能够慰他的寂寥。
王安石除参知政事之后,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熙宁新政开始施行。
在文化上的“变法”,则是把《论语》和《孟子》列为士子必读必考科目。并于熙宁4年,把《孟子》正式列为官方认定的经书。
从此,孟子登堂入室,位列孔子之后,成为“亚圣”。
王安石需要孟子学说来支持自己的变法改革。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王安石则说,呜呼!道之不明邪,岂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呜呼!道之不行邪,岂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
在对道的维护上,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失道”。这样的信念,对于王安石对变法的坚持,也非常重要。
王安石把孟子送上了神坛,但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孟子对他们的最大影响,还是孟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以仁为基石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然而孔子论仁,只是就事论事,随问而答,大多是根据弟子们的具体情况而简短地论及仁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缺乏集中而详尽的论述。特别是由于思想理论发展阶段的原因,孔子尚没有将‘仁’与‘心’、‘性’联系起来进行自觉的思考。孟子则不同,以心性论仁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由于孟子注重从心性论的层次和高度来理解和阐发仁的思想,不仅使仁学获得了强有力的论证,而且也使得他的仁论新意迭出,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内容也更为丰富,对孔子的仁学作出了重要的推进。”
白奚先生说,孟子论仁,多与“心”紧密相联。
在孟子的仁学体系中,“恻隐之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思想价值。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仁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从这些表述中,都可以看出“仁”对于人的重要性。
“仁不是别的,就是人的本心,就是心的最基本的属性。孟子此说,为仁找到了内在的心理根据,从而开辟了儒家以心论仁的新阶段。”
只有人类,才会有道德意识,白奚先生说,在孟子眼里,这种道德心或道德意识也是人与生俱来的,他称之为“良知”、“良能”,并把具有“良知”、“良能”的心称为“良心”、“本心”。
孟子的重大贡献之一,是确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四项基本的道德属性——仁、义、礼、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又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白奚先生指出,孟子从心、性、仁三者的关系论仁,视仁为人心的本质属性和人性的基本内容,这不仅解决了仁的来源和根据这一孔子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把孔子的仁学推进到心性论的深度和本体论的高度,使儒家的仁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宋朝大儒朱熹对孟子的景仰,与王安石相类。他说:“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人只道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仁心上发明大功如此。看来此说那时若行,杨墨亦不攻而自退。辟杨墨是捍边境之功,发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
朱熹所说的“四端”,即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
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说,“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北宋政和七年,儒医之名已经与其他中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儒而知医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智性选择。
儒医之名,并非知晓儒学、略通医术者,均可得此称呼。“部分文人亦官亦医,或者由儒转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参与医疗活动,悬壶济世,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医’。”
薛芳芸在《宋代“儒而知医”社会现象探析》一文中说,许叔微在习儒同时,刻意方书,精研医学,为官后仍不忘行医,人称“许学士”,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治病重视辨证,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等,流传至今;又如朱肱,元祷三年进士,曾任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后因忤旨罢官。他身处逆境,潜心医学,以行医著书为事,撰写了《类证活人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此外像高若讷、孙奇、孙兆、陈高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医。
在宋朝,让儒医之名具有高远意旨的,首推范仲淹,他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语,颇得同时代及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的推崇,朱熹认为“医国医人,其理一也。”
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良医之所以与良相同等重要,是因为两者都属于“仁政”之学。
良相,可辅君安民,良医,可活人无数。
此外,学医以事亲,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普遍共识。
大儒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又说“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
为了强调学医孝亲、济民的重要性,程颢又说,“儒知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害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事亲,乃大孝之事。懂些医学知识,万一父母双亲有病,可以亲自查看病情,防止庸医害人,是表达孝心的最佳形式之一。
大儒张载也认为,儒和医为一家,医理通于文理。这些大儒借儒学研究医理,将仁义纳入医德之中,把“仁爱”、“孝亲”、“利泽生民”等儒家思想渗透到看诊把脉、开方治病的具体诊疗活动中,把“医乃仁术”从治疗层面,上升到道统层面,提高了中医的人文境界。
到了元代,因为科举暂废,一些儒家知识分子本着“济天下利苍生”的愿望,大量进入医学领域。
刘完素,创寒凉医派。张从正如为太医,不久辞归,著有《儒门事亲》一书,朱丹溪,由理学入医门,创滋阴学派。
元代名医戴良说,“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元代儒医朱震亨,理学造诣精深。不但是知名理学家,还要求弟子也医理兼修,弟子或者再传弟子中,“儒而知医”者甚多。“盖以医家要旨,非儒不能明。”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为仁术。”
李时珍还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服用丹药的风气,儒医以儒家正统观点为依归,坚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用儒家正道,排斥外道邪说。
“明清时代,儒医辈出,仅新安学派”,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府卓然成家者820人,其中421人撰集汇编医籍730种。以名医、御医、世医、儒医多见的吴中地区,历史上见诸记载的有1400余人,著作600余种。
由于儒医成为医学正统,方术、巫医、草医渐渐从主流社会消隐,在农村或者城市的贫民阶层中,去寻找生存机会。
四 草医和巫医
由于儒医不但获得皇家认可,在上层社会拥有广泛的支持,所以,为了与草医和其他低阶层医生区别开来,儒医们通过把脉、开写药方、著书立说来提高行业门槛。
什么是草医?简单来说,就是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不会开处方、不懂把脉技术,更不会著书立说的文盲或半文盲医生。
草医是一种民间医术,缺乏像中医一样的系统理论,因此,诊疗过程中少有辩证论治,多是根据经验辨病用药,即多用土方土法。所用药物也很少像中药一样,经过炮制,基本是草药,采回即用,有的地方称草医为“草药匠”。
“草医”常分文式、武式。“武式”以捶皮打棒、练武弄拳来“扯棚口”,招揽生意,属于“习武行医”,多以治疗跌打损伤、金创骨折为主,通常以推、拿、按、捏等手法,通过卖艺献技来推销药物。“文式”专长于内、妇、儿科,也讲究所谓四诊八纲,通过诊脉象、看舌象来诊断病情。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走乡串户、逢集赶场。
根据杨念群先生的研究,草医的授徒与传承方法也与“坐堂”医生颇为不同。草医在带徒礼仪上虽仿效中医行跪拜之礼、艺成谢师等程序,但在具体医术时,则讲究所谓“过苗”,即随师采挖药材,认识草药,还要讲究辨证配方。教材使用的是《天宝本草》,再辅助配合临床经验,通过自采、自挖、自制,使整个诊疗过程显得简便有效和廉价。如果遇到病家有能辨识自采之药的,可省其药资。走方游医和摆摊行医比起来则更加行踪不定,他们常年走村串户,以出诊为主。行医特色或以中草药秘验单方为主,或以末药(散剂)、膏药为主,或以推拿、按摩、气功、挑痔、割治等一技之长为主。他们常年游走他乡,送医送药上门。
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杨念群先生对草医群体有着较多关注,并且对“游医”这一草医中的特殊群体也有描述:“游医”看病有时会用手轻压患者的指甲,观察回血速度的急缓,称为指诊;有时又会用自制的针刺破病人某个穴位,从血液的色泽、浓度、数量辨别疾病,名为刺诊;有时还会让患者伸出舌头,观察舌苔、舌质颜色的变化,名为舌诊;或者令患者端坐凳上,双手抱头,俯伏桌边或椅背上,医生用食指、拇指轻压患者脊柱两侧,缓缓由上向下推动,称为脊诊。摆摊行医多为医药兼营,在闹市区摆摊看病售药。有的摆摊医是由老字号药铺分化出来。
杨念群说,四川江油的草医就有高摊、矮摊之分。所谓高摊,是以搭棚为摆摊标志,有固定地域设点,属草医中较上层的部分;矮摊者,以地为摊,游弋不定为其次。如果按照用药习俗划分,草医又分为“根根”、“粒粒”、“沱沱”、“搓磨”数种。
宋元以后,由于“儒医”成为医学界的主流,传统的医学理论又逐渐被“儒医”们渗透进了儒家学说,靠口耳相传及以师授徒来传承的草医,日渐式微。
元朝“大儒医”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的自序中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名其篇目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
为了强调“儒医”的正统地位,他又说,“《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
非吾儒不能读,就把其他行医派别驱逐出了正统医门。也就是说,像《素问》这么高级的学问,其他门派染指不得,因为他们不可能读懂。
学者龚鹏程先生认为,朱震亨这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出来说话,把医道纳入了儒者的事业中来,对于草医、巫医等其他医学门派打击很大。
巫医,古称祝由科、咒禁科。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即脱胎于《黄帝祝由科》。
祝由,有禁咒、禁术、禁架、禁法、符禁、祝禁、越方等别称。葛洪《抱朴子》中说:“吴越有禁咒之法。”学者们认为,“禁”本来是中国南方特有的法术或技术,除了医疗之外,控制人或动物的行动、魔法幻术等也都被视为禁术。施行方法则有念咒(如咒禁、祝禁)或是书符(符禁)。
禁的内容涉及禁戒、斋戒和禁忌。禁戒即对施术人提出各种行为规范,包括“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等要求,斋戒则是人们在请神之前清洁身心,戒慎行为,以表示对神明的尊敬之意。咒语部分,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威摄性咒语、祈使警告性咒语、骂詈性咒语和解释病因性咒语。其中也有符,与禁、咒结合在一起,多为避邪、威摄性的符。
学者袁玮认为,祝由是原始时代物资不丰,又对疾病缺乏足够认识时,使用语言为主并辅以一定手段的驱除病魔法;魏晋后与道教结合,也是道教传播信仰的一大助力,佛教亦有禁咒法传入我国。
学者邢玉瑞认为祝由术的本源,实际上是古代的巫术治病。由于对自然界的秘密缺乏了解,先民们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犹如现代人对科学的信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用祝由方法治病,可能是当时最常用、最使人信服而且确有疗效的一种治疗手段。
唐代太医署首次设咒禁科,与医科、针科、按摩科并列为医学四科。咒禁科设立咒禁博士和咒禁师,教授咒禁,使学生能用咒禁来拔除邪魅鬼祟以治疾病。唐内典卷四十“太医署”记载:“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隋太医有咒禁博士一人,皇朝因之。又置咒禁师,咒禁工以佐之,教咒生也。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
宋元之时,咒禁等术受到“儒医”的排斥,知名大医朱震亨的著作《格致余论》与《丹溪心法》全然不用禁咒、存思、服气、辟榖、符箓诸说了。
尽管如此,直到明代,咒禁科仍然在官方认可的范围内,清朝取消了咒禁科,但有的学者认为,有清一朝,满人因信奉萨满教,其实对咒禁之术十分信奉,也正因为信奉,所以也更恐惧咒禁术,因此,在官方的医疗机构中,不再设咒禁科。
也正是这个原因,直至民国,咒禁之术仍然在民间十分流行。
根据湖南沅陵县1949年的数字统计,全县中医、草医的医药人员共有316人(其中中医221人,草医57人,中药人员38人),在这些人员中真正坐堂应诊的只有74人,自开诊所者34人,而走访行医的人数达到98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从空间分布的情况来看,城内的医生人数只有64人,而分布于这八个区的中医药人员总数则达到了252人。分布的态势也较为平均,除军大坪区有6人外,其他几个区的人数均在20-40人之间。在这些人员中,采取半农半医方式的人员达到了85人。(注:参见《沅陵县卫生志》,74页1989。)在与之相邻的一些地区如湖北松滋县,1949年中医有331人,中药人员120人,草医82人。
根据杨念群先生的研究,“京郊的许多村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没有多少中医,西医更是难见踪影。在前八家村附近,巫医人数就比西医多,因为中医是在民国十年以后才在村里出现的,这在华北地区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民国二十四年张家口的《阳原县志》曾记载说,到当年,县境内还没有西医,“中医亦不能遍村皆有,然三百户以上之村,类有一人”。
当地的县志上说:“富者得病,率皆延医诊治;贫者往往听其自痊自死,终身未曾服药者,约占三分之二。近年赤贫者,往往衣食皆无,更难求医疗疾矣。妇女有病,亦有求医巫者,痊则信其灵,死则由其命。”
由此可知,1949年前的中国乡村,草医和巫医所占的比例仍然不低。
有关报道称,由于传统文化的空间没有受到太多挤压,在中国台湾,民间的祝由咒禁医疗依然广泛存在。一些寺庙、宫观为民众收惊、驱邪、治疗,民众去庙里求香灰、符水等治病都是非常多见的事情。
由于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且近年来“新农合”报销比例提高,农民大体上病有所医,看民间草医的越来越少。一些居住在高山峻岭上的山区农民,仍然传承一些特殊的地方草药,比如“苗药”、“侗药”,还有一些民间奇效中草药,草医们采取传统的药浴、拔火罐、刮痧、推拿和针灸等形式,来为当地民众服务。
然而,新农合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大病和长期慢性病问题,所以,在一些边远山区,“巫医”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6年5月15日报道,在中国的四川,发生了一起“巫医”治病致人死亡事件。
报道称,两名“巫医”把一名妇女放进木桶,悬在一大盆缓慢沸腾的水上面。当灼热的蒸汽开始进入木桶时,妇女的丈夫被两名“巫医”支使去取一根针用于驱鬼。
妇女在桶里痛苦地嚎叫时,她的丈夫向两名“巫医”提出抗议。但“巫医”未予理会,并告诉他,叫声是魔鬼离开他妻子身体的声音。所谓的治疗结束后,那名妇女的身体已经发黑,脸也已经变紫了,最后死在丈夫的怀里。而那两个“巫医”借机溜走,跑到周围的山里去了。
这则报道说,在四川省发生的这件事显示,对超自然现象和古代仪式的信仰在中国农村仍然根深蒂固。在死去的这名妇女所在的村里,很多人相信灵魂治疗,有些人把健康问题归结为身体里的“幽灵”或“鬼魂”。一个当地男子说:“有病的通常也是信得最厉害的。”
五 西医的胜利
西医的胜利,有许多缘由。但主要的缘由,是西方探险家或者征服者们,从世界各地带回了超级病毒,从而造成西方世界大规模的传染病和瘟疫蔓延。
人类的迁徙史和扩张史,也是疾病的传播史。据历史学家统计,1492年哥伦布首次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时候,它的人口估计有八百万之多,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岛上的原住民已基本消亡。
郑和下西洋,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印度取经,这些文化史上的辉煌,曾带来过多少疾病史上的灾难,中国学者虽有所关注,但尚缺乏有价值的研究。
西方的医疗史和疾病史学者,十分关注人类的探险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给封闭地区带来的灾难性的传染病。
比如,有西方学者做过可靠的统计,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在与欧洲人接触不过十年之后,便减少了1/3,从大约2500万人降低到不足1700万人;在75年的时间里,土著人口总数下降了95%。
学者们认为,比起杀戮,对当地居民影响更为酷烈的是传染病。
学界普遍认为,欧洲入侵者给美洲大陆的最大祸患,就是带去了天花。
科尔特斯率领300名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最后征服了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天花起到了关键作用。战斗中,阿兹特克人俘虏了一名新染上天花的西班牙士兵,由于阿兹特克人从未接触过天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于是天花迅速蔓延开来。
在10年内,阿兹特克的人口急剧减少,一个强大的帝国也随之走向消亡。
印加帝国也是因为天花流行而被皮萨罗带领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的。在天花的肆虐下,各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
对于东汉的灭亡,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将其归结为治乱循环。
但从疾病史的角度来看,或许另有原因。
张大庆先生在《医学史十五讲》一书中说,“大约在公元初年,横越大陆的商队和外海航行的船只,分别由东向西及由西向东,把贸易拓展到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地,并将这个新的商业网络的两个远端——中国和罗马——联系起来。贸易交往也伴随着疾病的传播。”
一些学者认为,不可避免地,当地的居民对一些原有的疾病产生了“抗体”,但对于一些外来的疾病,却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张大庆说,“因此,在商业贸易扩展的过程中,印度和中东没有表现出疾病引起的人口重大变化,而中国和罗马却被搅得天翻地覆。公元2世纪晚期,中国和罗马都遭受到大疫袭击。在罗马,165-180年的所谓安东尼大疫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就又爆发了遍及全帝国的一次疾病大流行。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是什么疾病侵袭罗马,但大多学者认为,大疾病流行的起因是天花,或某种与其类似甚至更古老的疾病。中国在这个时期同样也出现了多次大疫,如著名医家张仲景宗族二百余口,三分之二死于疫病。”
《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二年,人畜饥疫,死伤大半。”
《五行志》注引张衡所上封事说道:“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
《陈思王集·说疫气》载,“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大疫流行,中医与古代“西医”究竟哪个行?医学史家并没有可靠的疗效比较,我们姑且认为古代的中医比古代的“西医”要高明一些——之所以这样说,完全出于我个人没有理由的民族文化优越情绪。
也就是说,“古代西医”同样对于瘟疫等流行病束手无策,因此,现代医学才姗姗出场。
在17世纪以前,西方的医院只是一个“照料”场所,“一些社会史学者认为基督教对病人强调的是关怀(care)而非治愈(cure);在基督教中,疾病的发生被设定为超自然的原因,治疗则被视为一种病人心理由躁动趋于平和的超自然式的安抚方法”。
这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疾病是祖先和神灵的惩罚,因此,才借助咒禁和祝由,来祈求神灵和祖先的原谅。
张大庆说,当时的医院“不是病体治疗的专门机构,然而却是病体有可能得到关怀的场所。病人栖居于教堂,由此被明显赋予了‘委托’的特征,交付身心以减轻痛苦是一种非世俗的行为。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医院与教区的教堂几乎是一体的。”
正是因为西医在大规模的传染病预防和治疗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能力,所以,在西方,“西医”打败了传统医学,成为主导性的治病方式。所以“迟至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城市仍是一些充满疾病、剥削、饥饿和死亡的污水池。”
中世纪时期的外科医生地位也很低下。文献记载,彼时巴黎的医生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种是内科医生,其治病方法几乎是千篇一律地采用泻下与灌肠。第二种是穿长衫的外科医生,一般采用烧灼办法治疗创伤,或用药物涂敷脓肿,或对膀胱结石患者施以结石截除术。第三种是理发师兼做些“小外科”。他们穿短衫,除了为顾客理发,还根据需要,为某些人施行放血术、吸角术(类似拔火罐)、包扎小创伤等小手术。
学界普遍认为,“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医学崛起的诱因。原因在于,“文化复兴”开始了对“人的发现”。
因为有了对人的重新发现,所以,现代解剖学兴起。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结构》一书,使人们对自身构造有了真切的了解。
有了人性的解放,许多有创造性的医生纷纷出现。比如,法国外科医生巴累。
在巴累改革外科治疗方法之前,外科医生的地位在西方很低,通常把他们称呼作“理发师外科医生”。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在自己的小理发店为人理发,偶尔,会为那些需要的病人做一些简单的外科处理。
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认为致病的原因是人体内有了多余的“元素”,因此,需要通过放血,把那些多余的“元素”排除。然而,医师们认为这个活儿是下等人做的,自己不愿意亲自动手,就委托给理发师来做。1540年,英格王批准,成立了理发师、外科医生联合会,从此,理发师正式打出了外科医生的招牌,并选了三色柱作为自己行医和理发的标志。三色柱中,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纱布。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理发店仍然用三色柱来作为标志使用,其来源即出于此。
1745年,理发师与外科医生合作整整205年之后,英王乔治二世批准成立皇家外科医学会,外科医生才与理发师就此分道扬镳。
巴累于1552年担任军医期间,对一个下肢被炮弹炸碎伤员的治疗,采用结扎血管止血施行截肢手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之后,由于结扎血管止血法的推广应用,截肢手术得以改进并提高了疗效。1564年,巴累在法文专著《外科学教程》中,写下了结扎血管止血法的专论。
巴累在医学上的其他贡献还有很多,如制作“人造四肢”示意图、论述股骨颈骨折、描述齿槽脓肿切开排脓、阐述前列腺肥大对排尿的影响、介绍脱臼整复术、改良兔唇修补术等。集中巴累成果的法文版《巴累全集》于1575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被翻译成英、德、西班牙等数种语言出版,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巴累生于1517年,逝世于1590年,也就是说,虽然他为外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声誉,但是直到他去世,外科医生仍然与理发师在一个招牌下行使自己的职责。
有的学者认为,哥伦布探险归来,带来了新大陆的消息,从此开始了航海大发现,但也带回了梅毒。
当时,法国与意大利开战,梅毒在法国军队蔓延,导致法国军队失去了战斗力。
1546年,意大利医生伏拉卡斯托罗写出了《论传染和传染病》一书,提出了传染病传播的三种渠道。
文艺复兴的另一大贡献,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让人们的目光从神学身上离开,转而去探求科学,从中发现知识。另外,笛卡尔提出的精神与躯体分离的思想,对现代医学的进步,推动甚力——实验医学就此兴起,现代西医也由此肇始。
17世纪,生理学开始发展,人们发现了血液循环现象。随之,医物理学派和医化学学派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医学就是在不断发现新理论和不断纠正谬误中前进的。
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17世纪的医生们曾经用牛血、鸡血和马血等来给人类输血,许多人因此而丧生。英国、法国立法禁止输血。
直到1901年,人们发现了血型的秘密,用输血的方法来救人才流行开来。
在中世纪,由于医生成功救治病人的例子并不多,所以,成了各类人嘲笑的对象。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比如蒙田、莫里哀和伏尔泰,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对医生进行过嘲讽。
然而,临床医学马上诞生了,医生们的春天来了。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汤其群教授说,意大利的摩干尼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死前情况和尸检发现,把“病灶”与临床症状联系起来,提出了疾病的器官定位学说,建立了器官病理学。
摩干尼做了700多例尸体解剖试验,写出了《由解剖观察诸病位置与原因》一书,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深远影响后世的观点:病灶。
直到今天,西医们用种种检查方法,目的就是在病人身上找到“病灶”。张大庆先生说,“直到现在,西方医学的基本原理还在找病灶方面。”查“病灶”的工具,有CT、核磁共振、X光等等。
法国大革命之后,医学教育被广泛推广。但西方的医学教育也经历了野蛮生长阶段。以美国为例,最早的医学院都是强调效益为先的“文凭制造厂”,办学的投资者和相关的教授,关心的只是钱。
1813年,美国的耶鲁大学举办了首期医学课程班,并规定学时为6个月,但因为其他大学的课程班只需要上4个月,致使耶鲁生源困难,不得不把学时改成4个月,以迁就市场。
当时,有一件事被传为笑柄。1887年,一名8岁的小姑娘寄信给多家医学院,要申请去上学,结果竟然同时被一半的医学院录取。
“在19世纪,美国的医学生一直被看作一群粗暴、不守规矩的家伙。”
著名医生迪克逊,将纽约大学医学系的课堂描述为“肮脏的房间,弥散着烟雾,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异味”,下课时“剧烈的喧嚣声震耳欲聋,学生们像疯狂的公牛冲出教室”。有人悲观地认为“知识界中包含医务业(medical business)是一个错误”。
19世纪的下半叶,对医学院进行改革的呼声渐起,芝加哥医学院率先把医学生的学习时间从4个月变为9个月,后来又要求必须3年才能毕业。
对美国医学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是1869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他力排众议,让哈佛大学引入了三年制的医学教学计划,并在生源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坚持这个方案不退步,最终为哈佛大学赢得了声誉。
有了哈佛大学的示范效应,耶鲁大学也跟进,影响了一批知名大学都把医学院纳入了大学教育。
美国医学教育的标志性事件,是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办。
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尔市银行家、贵格会教徒约翰·霍普金斯去世时,留下了一笔价值7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遵照他的遗嘱,其遗产分别捐赠给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霍普金斯医学院为美国的医学教育确定了新的标准,要求取得学士学位以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开始医学学习,一下子把美国医学教育的起点,提高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但教学生知识,还注重医学实验和临床研究,很快在美国声名鹊起。
“1907年,卡内基基金会受美国医学会委托,指派弗莱克斯勒全面考察美国的医学教育。弗莱克斯勒经过两年的努力,于1909年完成调查并于1910年出版了题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的报告。报告首先回顾了北美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然后分析了各个医学院的现状,提出了改善医学教育的措施。报告指出,在所调查的医学院中,仅有50%符合‘现代医学教学’的标准,30%条件很差,另外20%‘名不副实’,应当资助那些有发展前景的医学院并关闭不合格的学校。在弗莱克斯勒报告的影响下,许多质量差的医学院逐渐被淘汰。在报告发表20年后,也就是到1930年,美国医学院的数目从148所减少到66所。当时美国最主要的两大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都开始大力资助医学教育,使得美国的医学教育迅速崛起。”
这段史料说明,直到1930年,美国的医学教育之乱,仍然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者说,今天十分发达的美国医学教育,也曾经有不堪和混乱的昨天,也因之增加了我们对中国医学教育的信心。
随着教会势力的入侵,医院和西医也随之进入中国,并逐渐扎根。
1840年以后,教会医院在中国迅速扩张,为了让宗教具有“神迹”,即相信宗教可以让变坏的身体好起来,许多传教士都是医生。
正如坚船利炮从海上来,教会医院和传教士医生也从海上来到中国,最早落户广州。
现今比较有名的几所医院,比如湖南的湘雅、北京的协和、四川的华西、上海的瑞金,都有教会医院血统。
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开办,不久,即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但西医的进入,对中医造成了巨大冲击。一些人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儒家的中庸思想,使李鸿章等一些权臣并不支持这一偏激的观念,“中西汇通”,成为当时的普遍看法。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从1913年5月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10年内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投资中国。由于对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情有独钟,超过一半的钱用于这方面,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据协和医院方面1956年统计,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前后总计投入4800万美元左右。根据协和医校的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的回忆,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
协和医院的到来,只是让西医以医院为载体,开始了对中医的冲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医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文化空间,而成为集体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的附庸。
1921年,兰安生来到中国,成为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
1925年,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卫生事务所挂在警察厅之下而不是卫生局。在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医疗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结合,一开始就非常紧密。
“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为整个示范区的十万居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一所”重视妇幼保健,还对垃圾、粪便、污水等处理制订了监督办法,减缓传染疾病在社区内的传播,这些努力使得“一所”居民死亡率从22.2%下降到了18.2%。
由于能够对抗大规模传染病,更由于“社会医学”的兴起,西医渐渐成为中国医疗界的主流,而中医却日渐式微。
胡定安先生认为,在当时,公共卫生的实行变成了民族主义目标的一种制度化表述,因为“由体育观念和预防医学中之卫生观念、一切的改革心理与趋势观察起来,就可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
西医负起了民族复兴的责任,在当时甚嚣尘上的“进化论”,也因之以“进化”的观点,认为西医取代中医,乃是历史的必然。
刘理想在《试论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影响》一文中说:“然而在新学与旧学、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二分法的话语模式下,作为中学一部分的中医,在当时几乎是唯一能在技术层面与西学中的西医相抗衡、互较短长的一门中国学问,自然受到批判者的格外关注,被戴上旧医、封建医、玄学医等帽子,价值认知从先前中西横向比较的空间观向新旧纵向对比的时间观转变,中西医价值比较的天平迅速向西医倾斜了。站在预定的立场上,作为‘旧医’的中医与作为‘新医’的西医相比,‘落后’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当时不仅医学家倡导医学革命,即一般海内的学者,也极力地在那里提倡新医学的发展;他们都说是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新旧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
文化名家周作人在《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一文中说:“中西医学这个名称实在是讲不通,应该称为新旧医学之争才对。世间常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东方文明高于西方文明,我总不能了解,我想文明总只有一个,因为人性只有一个,不过因为嗜好有偏至,所以现出好些大同小异的文化,结果还总是表示人性的同一趋向。”
哲学家冯友兰在《论中西医药》一文中表示:“中国的医学、药学,亦同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一样,缺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一般人常以中医西医中药西药对比。中医西医的对比是错底。因为普通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所谓“国医”》,文章说:“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学者毛子水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着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
刘理想说,在当时,“随着进化论思想的深入人心,有了时间上的视野,人们看待中西的文化差异就有了新的发现,从存异的事实出发,直达求同的目的地。‘全盘西化’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科学就是这样以时间的名义一统江山,从此环球同此凉热。有了时间上的视野,西学变成了科学,作为西学之一的西医自然是科学,西医成为新医、现代医学,自古华山一条路,那么西医自然也就是世界各种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曾于1902年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主张废除中医。1929年,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其举出的四条废止中医理由中,第四条理由,就是按进化论的思想,中医必须淘汰。他说:“要而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本委员十余年来研究我国医学革命,对于旧医底蕴,知之甚悉,驳之甚详;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刘理想认为,“其实,早在‘五四’前后,随着科学精神的高扬、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话语权已经逐渐地掌握在现代科学派手中。”
那场关乎中医生死的中西医之争过去数十年了,中医仍然好好地活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凌锋认为,当年的中西医之争,在今天看来意义并不大。中医取代不了西医,西医也消灭不了中医。在精密的神经外科领域,中西医结合,一样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凌锋教授提出的“整体自洽”理论,就是中西医相结合的一种治疗新理念,即整体自治疗法需要打破专业界限,实行科际间的合作。
她说,在神经外科特别是西医抢救中用到的中医,大多离不开西医诊断、中医开药这一思维模式。而在整体自洽疗法看来,中西医结合要真正有效,必须打破这一习惯思维模式。因为中医和西医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型看同一人体的问题。如昏迷,中医辨证是醒神开窍,其神和窍在哪里?西医无法得到解剖学的证据。但在功能的协调方面中医却的确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中西医如何才能结合呢?实际上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黑箱,中医理论只是宏观调节的模型。我们理解到这一点的做法就是在中西医两者不冲突的前提下,中医针对全身情况,西医针对具体问题,在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双管齐下,共同作用。
凌锋教授认为,由于现代医学的分科过细,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讨论和合作日渐减少。我们常常会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而忽略了整体。
“人是一个整体并具有有力的调节机制以保持生命的稳定,我们称之为内稳机制。人的健康状态是内稳机制的稳态,而疾病状态为某种亚稳态。我认为所谓治疗并非是手段和结果那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手段影响内稳机制的调节过程。外界对人体的任何影响都是通过系统稳定性机制起作用的。任何颅脑外伤所造成的神经组织的损害,都不是靠外界给予什么物质去直接替代,而是提供维持这些功能修复的条件。”
凌锋教授说:“所谓整体自洽疗法,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医疗的本质。今日通行的治疗理念是基于一种直线型因果关系的模式。它可以简单概括为寻找病因和鉴定病因,然后针对病因和去除病因。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忽视整体而把人看作简单的机器,实际上人体是一个具有强有力的调节能力以维持生命的内稳定自组织系统。任何医疗手段都不足以通过干预这个自组织系统对疾病起作用。病人的康复,实为人体内稳机制和医生适当干预耦合的结果。所谓整体自洽理念,就是医生的干预手段与机体内稳态的高度耦合,以形成完整的自相关系统。这种干预手段不仅需要医生有高超的技术,更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才能实现整体自洽。”
因此,无所谓中医的失败或西医的胜利,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医学的胜利、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