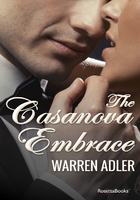“兄台贵姓?”
“尹姓,陵城人;这是我师弟,方姓。不知道友作何称呼?”
“鄙姓洛,乾城人。”
陵城位于乾城东北方,只有春冬之分,多数时气候寒冷。但因多山脉,近泠水,天杰地灵,许多修行门派建造在陵城。故陵城,又为剑城。
“尹兄,方兄。”洛亦旪获救,起身作揖。
尹世尤颔首回礼,占勇跳到前面,绕着亦旪转悠一圈:“你这公子哥的小身板,不在城里头好生呆着,跑着荒郊做甚?你这,刚探门吧,搁这成心寻死呢。”
……
瞧瞧他,多凶。但是亦旪坦然一笑:“我探过了,且已入下士。”
自是意修。
占勇面上过不去,余光突然瞟见亦旪袖口露出的纸张。
原来是去祭奠先人。
方占勇尬了片刻,他除了看物件准,看谁谁不准,尤其是测修为一类……
“那你…意修,也不能在外面瞎跑!”占勇梗着脖子,被尹世尤拉到身后。
“道友莫要见怪,我师弟眼力不好。”尹世尤浅浅一笑,像他这样不偏袒同门的大师兄,已经不多了吧。
亦旪侧过身子,“无妨。我比二位小不了多少,却低了你们五个阶等。”
洛亦旪全然没有察觉自己这话有什么不对,他意修下士,尹姓公子意劫上劫,可不是差了五等?
占勇也没觉得有什么,倒是尹世尤愣了片刻。
“有何不对?”
“并无,”尹世尤自觉失礼,尴尬一笑:“洛兄年纪尚可,只需勤加修习,来日必大有作为。”
“借贵人吉言。”
“折煞。”
一番谦词后,洛亦旪与二人道别。他们要进城,而他,要先找到大饼。
“出来。”
……
“人都走了。”
……
洛亦旪凭着感觉走到一处枯草堆前,果然,那里有一小撮白毛。
“别装死了,”亦旪揪着白毛戏弄它,“自己出来,不然我踹你了。”
“好嘛好嘛,兔子不躲了。”
大饼整个身子窜出来,洁白的毛发上掺了零碎的杂草,亦旪不太想抱它了。
“下回找个干净地儿躲。”
……
……
又走了几里地才发现一座孤坟,墓碑歪斜,不知道经历过什么。
坟头长着几撮草,亦旪上前去给它拔掉。旧坟挂的白钱他们也给移过来了,也不晓得换新的,上面占满泥土。
“娘。”
亦旪扶正墓碑,重新给它埋进去,又把什么的泥巴扣干净。
“那些人还值得您挂念吗?坟头长草了都没人来清理,洛家那么大,就没有真正在意你的?”
“也对,”亦旪吹燃火折子,给他娘亲烧点东西:“迁坟这么大事情,他们没经过我直接下了决定。”
他顿了顿,又自嘲道:“不过我一个庶子,你一个姨娘,估计也没必要。”
洛亦旪跪下磕了几个头,“儿子今儿个来看您,是想说,儿子回来了,估摸着以后就不会走了。”
“祁炀收了我当徒弟,您放心了,有这个大靠山在,儿子怎么着也不会受委屈。”
快入冬了,受一点风都满身寒气。洛亦旪拢了拢袖子,他带的东西不多,这次先来找个位置,之后再花钱把这地方修缮修缮。
“路上出了些意外,本该早些到的。”
“噌噌。”大饼咬着几支野花过来了。
“这个时节还有这么多花?”亦旪接着,放到碑前:“这是大饼,一只兔妖。是我的好伙伴。”
“姨姨好,兔子叫大饼,是亦旪取的名字!”
……
磨磨又蹭蹭,一个晌午过去了。
“回去吧,”亦旪抱起大饼,回头看了眼墓碑:“儿子走了,过天儿再来。”
过几天来给你修坟。
在城郊吃了一碗素面,又买了两根胡萝卜才进城。
近城门口的酒楼被围的水泄不通,影响到亦旪通行,还不断有人推搡着往那边去。
他不是个爱凑热闹的人,所以抱着兔子打算从小巷穿行。
“洛兄。”
肩膀被人拍了下,洛亦旪不用回头也听出是谁。尹世尤,几个时辰前见过的。
“尹兄。”
占勇不在他身边。
尹世尤见他瞟了一眼,笑着解释:“占勇第一次出陵城,对什么都稀奇的很。”
哦,瞧稀奇去了。
兔子早一步溜了,丢下他在这被人搭话。
“洛兄,不知这乾城有什么信誉高的酒楼?洛兄给个推荐。”
哦,忘说了,陵城不属于奕国,而是玉龙国。
“甚少出门。”
一走就是三年。
“这样……”尹世尤笑笑,面上不察,慢捻的手指却暴露出他的尴尬。
亦旪收回目光,颔首:“家里有规矩,外出不得超过六个时辰。”
尹世尤明白过来,人家这是要走了,“那,后会有期。”
“告辞。”后会无期。
亦旪拐进小巷,躲进竹笼的大饼钻了出来,蹦哒到亦旪脚边。洛亦旪弯腰抱起。
“你以后少出门。”
“兔子知道了。”
乾城高阶修士不多,但温火的修士倒是不少,大饼修为底下,被抓住了,只有等死的份。
“回去了。”
“好嘞。”
哐当一声轻响,似是配饰坠地的声音。洛亦旪腾出一只手摸了摸腰间,玉坠子还在,那就与他无关了。
……
……
元臻趁黑把祁三召进宫,也不说为什么,让去的人直接领他过来。
一路紧赶慢赶,在下宫禁前进了宫。
“老师,老师辛苦了,来坐。”
祁三还以为怎么了,来的路上鞋都差点跑掉,结果一进门,始作俑者完好无损地坐在殿中央品茶。
“你你你!”
“老师快坐呀!”
瞧元臻笑得欢喜,丝毫不知自己得罪了祁三。
“有什么事不能明早说,非得在宫禁前把我弄进来?我怎么回去!”
祁三憋着气坐下,端起半满的瓷杯。
“只消一道宫令,您不就能出去了?再不济,您就搁我这儿住一晚。”
元臻来拉祁三的袖子,被他扬手躲开:“去去去,谁稀罕你这宫殿。”
“快说,”祁三打了个哈欠,“有什么事非得叫我来。”
元臻收起笑,正襟危坐,“北原,派使者来了。”
第二个哈欠卡在喉咙眼里,被祁三吞了下去。
“那个,被雪山环绕,一年到头也不与他国来往的神秘北原?”
“对。”
这事可大可小。祁三也正经起来思考问题,“有传言说,北原刚死了君主,举国哀痛。这种时候还派使者出门,意欲何为?”
元臻摸着下颚,想了想,还是问出来,“老师……老师可知炼石?”
祁三移过目光,“炼石可是稀罕物,只有焰山口才有的东西,你问这做甚?”
“有人讲,北原是为这而来。”
祁三一想,奕国境内确实有座焰山,距离乾城颇远,没个把月到不了。
可是玉龙国也有焰山,且离北原更近。北原的人过来还得穿过玉龙国的尾巴角。
“就这么巧?”祁三问,他也没想什么。
“您说,这是不是,有什么预谋?”
祁三白了他一眼,“你说说你,从你小时老夫就教导你,凡事无绝对,预则立。但不明来意,肆意妄猜是再愚蠢不过的。”
“是,”元臻跪坐他面前,低下头。
“先差人准备着,不论来意如何,我们作为东道主的礼数得全。至于后事,等人来了,再召孟谞等人商议。”
“听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