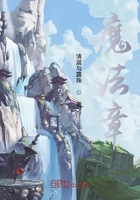“这太容易办到了,”主人回答说。这时,他抬起了头,盯着旅客,说:“……要付钱的呀。”
“那自然。”说着,那人从他的布衫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
“好,我就来伺候。”主人说。
迪涅地处山区,10月的夜晚寒气袭人。那人收起钱包,将行囊放在门边,手中却仍然握着那根木棍。他在灶火边的一张矮凳上坐了下来。
旅舍主人来回忙碌着,眼睛却禁不住总是打量这位旅客。
“能马上吃东西吗?”那人问。
“得稍等片刻。”主人回答。
新来的客人转过背去,好让火烤一烤。趁这时,那位大模大样的旅舍主人从衣兜里摸出一支铅笔,又从丢在窗台旁小桌子上的那张旧报纸上撕下一小角。他在那片撕下的报纸上写了两行字,把它折好,没有装进什么信封,便递给一个好像是他的厨役同时又像是他的跑腿的小伙子,并在那小伙计的耳边嘟囔了一番。小伙计听完,拿着那条子,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那旅客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我很快就能吃上东西吗?”他又一次问。
“还需稍候。”旅舍主人说。
那小伙子回来了,同时带回了那张纸条。主人在等待,立即打开纸条。他细心读了一遍,随后又点了点头,想了想。最终,他朝着那心神不安的旅客走过去。
“先生,”他说,“请原谅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为什么?怕我不付钱?要不要我先付账?钱我是有的。”
“不是钱不钱的事。”
“那是因为什么呢?”
“您有钱……”
“不错。”那人说。
“但是我,”主人说,“我没有空闲房间了。”
那人和颜悦色地说:“我睡在马房里就行。”
“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
“马房里也没有了空地。”
“那,”那人又说,“阁楼上的一个什么角落也成。一捆草就够了。等我吃了饭……”
“我不能给您饭吃。”
这句既强硬又有分寸的话,使外来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站起身来。
“哈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一出来,我就上了路。足足走了12法里一法里相当于四公里。。我不白吃,我付钱。我要吃东西。”
“我一点吃的也没有。”旅舍主人说。
那汉子听了放声大笑,朝那炉灶转过身来。
“没有!那是什么?”
“那些东西全是客人定好了的。”
“谁?”
“那些车夫先生。”
“多少人?”
“12个。”
“那些东西却足够20个人吃。”
“那都是预先定好的,且付了钱。”
那个人又坐了下来,并用先前的那种口吻说:“我既到了这里,且饿了,就不想离开了。”
那主人俯下身子,凑到客人的耳边,以一种让他吃惊的口吻说:
“快走。”
外来人俯下身去,用他那棍子的铁梢拨着火里的红炭。他猛地转过身来,还想开口争辩。可是,这时,那旅舍主人的眼睛盯着他,还是和刚才一样低声说:
“听我说,别废话了。您要我揭您的老底,是吗?您叫冉阿让,对吧?您进来时,我一看见您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问过了。这是那里的回话——您识字吗?”
说着,他把那张纸——从旅舍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转回旅舍的那张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不管是谁,我一向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还是离开这儿吧。”
那人低下头来,抄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外来人好像是受到了侮辱。他满腔委屈,沿着那条大街,紧靠着墙,走着。他的头一次也没有回过。假使他回头的话,他就会看到,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主人正在门口站着,而旅舍里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正围着他,在那里比比画画,议论纷纷;从人们的惊疑的目光里,他还可以猜想到,不久就会由于他的出现搞得满城风雨了。
由于没有回头,这些他统统没有看到。也难怪,情绪沮丧的人是不会回头的,因为他总觉得,厄运紧跟其后,是甩也甩不掉的。
他径直朝前走着,大步穿过许多他从未见过的街道。此时,他忘记了自身的疲乏。人在颓丧时常常如此。这样走了一阵子之后,忽然,他感到饥饿难忍了。天要黑了。他向四周张望,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
在那家华丽的旅馆里吃了闭门羹,那么,找一家简陋的酒店,找一所穷苦的破屋是否能成呢?
在那条街的尽头,有一盏燃着的灯。半明半暗的暮色之中,露出了一根松枝。这松枝悬在一根曲铁之上。他向那里走去。恰好那是一家酒店。这是沙佛街上的一家酒店。
外来人停了下来,透过窗玻璃向酒店一楼餐厅望去。桌上点着灯,壁炉里炉火正旺。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也守在火旁。一只铁锅挂在吊钩上正被火焰烧得发出响声。这家酒店同时也是一个客栈。它有两个门,一个临街,另一个开向天井。天井不大,满是粪土。
那人先是溜进天井,好像不敢走临街的门。待了一会儿,他轻轻地提起门闩,打开了门。
“哪一位?”老板问。
“我,一个想吃饭又想住宿的人。”
“好,在这儿吃住都很方便。”
当他进屋时,他一面被灯光照着,一面被炉火照着。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打量了他好一会儿。当他解下他那只口袋时,老板对他说:
“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先来烤烤,伙计。”
他走过去坐在炉边,把两只疲惫的脚伸到火前。他闻到了从锅里冒出的香味。他的脸仍然藏在低低的帽檐下,但人们看到,这时,在他那张由于长期的苦痛而布满了愁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的神情。
那人的侧影坚强有力而又忧郁。这一相貌很是少见,乍看上去像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感严肃。眉毛下,眼睛炯炯发光,正像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当时,围着桌子坐下的客人当中,有一个鱼贩子。他在来沙佛街这家酒店以前,先到了拉巴尔的旅舍,在那里的马房里寄下了他的马。当天早晨他恰又在阿塞湾和……(地名不大记得,可能是爱斯古布龙)之间碰见过这个面凶的外来人。那外来人当时曾请求允许他坐在马屁股上,因为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那鱼贩子边支吾着,边扬鞭离开了他。半小时以前,那鱼贩子还围着雅甘·拉巴尔,并且把他当天早晨那次不愉快的遭遇对聚在柯耳巴的人讲述了一遍。这时,鱼贩子来到酒店老板身边,向他窃窃私语了一阵。那个赶路的客人还在那里低着头想他的心事。
酒店老板回到炉旁,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
“您得离开我这儿。”
那个生客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
“唉!您都知道了?”
“是的。”
“他们从那里把我撵了出来。”
“我又得把你从这儿撵出去。”
“您要我到哪儿去呢?”
“这不干我的事。”
那人只好提起他的棍子和布袋,走出酒店。
走出店门,有几个孩子拿着石子冲他扔过来。那些孩子从“柯耳巴十字架”旅店跟到这里,专在门口等他出来。他狼狈地转过身,举起棍子,做出要打的样子,孩子们才像一群小鸟似的散去了。
他走过一所监狱。监狱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拉了拉那铁链。
墙上的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一面说着,一面恭敬地摘下便帽,“您能不能开门让我在这儿住一夜?”
传出一个人的声音:
“监牢不是客栈。你要进来,得先有人逮捕你。”
那墙上的小洞合上了。
他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有不少花园。其中的几处只用篱笆围着,使街道显得更为生动。在这许多的花园和篱笆中,他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射出灯光。他透过窗玻璃朝里看,正像刚才他看那酒店一样。房子刷得很白,床上铺着印花棉布床单,屋的一角有摇篮和木椅,一支双管枪挂在墙上。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食物,一盏铜灯照着那块宽大洁白的台布,上面是一把闪光如银的盛满了酒的锡壶,还有一只热气腾腾的栗黄汤钵。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桌子旁,正笑着颠动坐在膝头的孩子。一个年轻的妇人正在他的旁边给另一个婴孩喂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这是一幅多么温柔宁静的景象啊!过路人不觉愣了一下神儿。这引发了他怎样的思绪呢?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得出。也许他正想着如此一个快乐的家庭该是肯待客的吧?在眼前的这片福地之上,也许他找得着一丝恻隐之心吧?
他在玻璃窗上非常轻地敲了一下。
屋里的人没有听见。
他敲了第二下。
这时,他听见那妇人说:
“当家的,好像有人叫门。”
“不会吧!”她丈夫回答。
他敲了第三下。
那男子站起来,举着灯,走过来开门。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有点半工半农的模样,腰里围着一件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他的左肩。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红手巾、一只火药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由一根腰带兜着,这使他的肚子显得鼓鼓的。他头朝后仰着,一件翻领衬衫满敞着,露出了又白又光的牛脖子。他眉毛浓黑,一大片黑色的络腮胡子,眼窝不深,下颏突起,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先生,”外来人说,“劳您的驾了。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子的那间棚子的角上睡上一宿吗?请问,假使我出钱,这可以吗?”
“您是谁?”那主人问道。
那人回答说:
“我打壁马松来。走了整整一天,12法里。成吗?假使我出钱?”
“我同意让一位肯付钱的正派人留宿,”那男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那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今天既没有杂技表演,又不是赶集的日子,绝不会没空房子住。您到拉巴尔那里去过吗?”
“去过。”
“结果呢?”
外来人感到为难,回答说:
“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不肯留我。”
“您到沙佛街上那个叫什么的人的旅店里去过吗?”
外来人更加窘迫了,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也一样。”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现出戒备的神色来。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那陌生人,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道:
“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
他又朝那外来人看了一眼,然后向后退了三步,把灯放在桌上,随手从墙上摘下他的枪。
那妇人听丈夫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之后,立刻抱起她的两个孩子,赶忙躲在她丈夫背后,惊慌失措地盯着那个陌生人。她胸口还敞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低声说:
“佐马洛德。”佐马洛德,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野猫的意思。
她的这些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屋主仿佛面对着一条毒蛇,于是,立在门口,吼道:
“滚!”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好吗?”
“还是给你一枪更合适些!”主人说。
说罢,主人使劲地关上了门,外来人还听见推动两条门闩的声音。随后,板窗也关上了,一阵上铁闩的声音也传到了街上。
夜色沉沉。阿尔卑斯山中又刮起了冷风。从苍茫的暮色中,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草棚子,看上去仿佛是草墩搭起来的。他决心越过一道木栅栏,进到那园子里。他朝那茅棚走去。门很窄,像一个洞,似乎是筑路工人在道旁临时搭起来避风雨的。他当然也确实认为那是一个筑路工人歇脚之所。现在,他感到又冷又饿,实在难熬。吃的东西他已不再指望得到了。但得有个避寒的地方。眼前这类棚子晚上通常是没人住的。他俯下身,爬了进去。里面挺温暖,地面上还铺有一层麦秸。他躺了下来。疲倦使他一点也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了背上的口袋压着他的背,使他很不舒服,而这不正是一个现成的枕头吗?他解那捆口袋的皮带。正在这时,忽然,他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定睛一看,黑暗中的茅棚洞口露出一只大狗的脑袋。
这原本是一个狗窝。
他本是胆大力壮,勇猛无敌的。他抄起棍子,当做武器,拿着布袋,当做盾牌,慢慢地,从狗窝里爬了出来。这一弄,他那身本已破烂的衣服就变得越发脏破不堪了。
他离开花园,被逼得朝后退步,并运用棍术教师们所谓的“盖蔷薇”棍法去对付那条恶狗。
他竭尽全力越过了木栅栏,返回了街心,孤苦伶仃,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避风之所,连那堆麦秸和破烂不堪的狗窝也不能成为他的容身之地。于是,他就让自己落(不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有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叫了一声:“连狗我也不如了!”
不一会儿,他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出了城。他希望能在田野里找到一棵树或是一个干草堆,靠一靠。
他低着头,走了一段路,直到感到自己已经与那些人家离远了,才抬起眼睛,四面张望。他已经身处田野。在他前面,有一片矮矮的土丘,土丘上覆盖着齐地割了的麦茬,这使那些土丘就像被推光了的头。
天边已是漆黑一片,那不只是夜的颜色,好像那是极低的云层,它压住土丘,继又升浮,满布天空。但是,由于月亮正在地平线的下方,将要升起,这样,在万顷苍穹之中仍还留有一点暮色的余辉,而这余辉便使这些微微带有一点白色的云构成的巨大的拱形物反射出一丝微光。
这样,地面比起天空来反倒明亮些。一片特别阴森的景色;那片荒凉枯瘦的矮丘的轮廓,被黑暗的天边衬托得模糊不清,色如死灰。一切都显得丑恶、卑鄙、凄惨、毫无生机。在这丘陵和田野之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树,歪七杈八,在与这流浪人相距几步的地方,蜷曲着枝干,摇曳着。
显然,在智慧方面和精神方面,这人全无喜欢挑剔的习气,因而对于事物的神秘之处是谈不上敏感的;可是当时,在那样的天空中,在那样的矮丘上,在那样的原野里,在那样的树梢头,却有某种东西深深地令他感知了。因此,他在凝神伫立一阵之后,便猛然折回头,朝原路走去。某些人的直觉常会感到大自然对他也存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