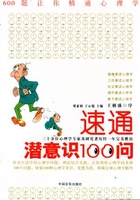阿斯汉不明白程晨为什么突然不再矜持,亲自送上门,把自己给了他。那天,阿斯汉大汗淋漓地冲进卫生间,仿佛是遭人强暴,使他如此狼狈不堪。等他换上衣服,程晨已经站在他家阳台上,双手捂着滚烫的脸,泪光闪闪,强装镇定地看缩成圆球的黑脑袋麻雀在树枝上瑟瑟发抖。
阿斯汉轻轻走来,几乎用整个上身裹住她,喃喃地说道:我妈不让我欺负女孩儿,除非我想娶她!
程晨眨巴着眼睛说:没听见,再说一遍......
他没原路返回,而是深情地在她的耳边吴侬软语:我爱你......
程晨突然哭了,简直泣不成声。她不是那么浪漫的一个人,再说他也不是第一次说这句三字箴言,第一次吻她时也说过。她哭是因为我她怕辜负了他,蒙古人特有的那种待人接物的真心与单纯。
程晨人在阿斯汉身边,心却在她爸那里。她觉得她爸很快会打电话来。他会且该第一时间安慰她:原谅你妈的不讲道理,这不是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可以不受,媒妁之言可以不从,自己的婚姻爸跟你妈不插手,只要是你自己看中的,我们都接受......
她每天坐在电脑桌旁,心不在焉地扒拉几下电脑,回忆着她爸妈的这些年:从某种程度上讲,妈的咄咄逼人是爸的贫穷和仁慈给惯成的,相对应的,妈后来的逆来顺受也是爸的日系益发达给震慑的。
大概在她程晨七八岁间,有一次,她在家里炕沿边摸呼噜呼噜睡觉的猫,忽然听见院子里她妈忿忿地呵斥她爸“我圪蹴下都比你尿得高”!程晨转身跑出去,揪着她妈的衣襟问,“是吗?妈妈你已经试过了吗?你帮我尿,我也要......”程母气急败坏,甩开这个王八羔,恶狠狠抓起墙边一把锄头,丢上右肩膀,走了。
他们前脚一走,程晨后脚便学起邻居小男孩儿们,学他们把裤子退到膝盖窝,一开始很顺利,也是那样弯弯的一股,收尾时就不由她了,丝丝顺大腿下来,流了一裤子,第一次以半失败告终。但这个倔强的女孩儿没有放弃,她觉得肯定有办法尿得很高。第二天,等他们再一下地,她就开始伏在瓮沿上,舀起半瓢水,仰头一口气喝下去,再舀半瓢水,再喝下去,直到想吐才丢回空瓢,肚子鼓成西瓜一样。小小失败就要放弃,爸爸可不是这么做的,妈妈骂了那么多次,拷问了自己那么多次“我要你能做甚了?连个主都做不了”,晚上回来,爸爸依然给妈妈打洗脚水。终于,在屡战屡败,再败再战之后她发现,喝了水也不能即刻就尿,要等快憋不住了再尿,尿得就比邻居小男孩儿都高,没过多久,她就能随心所欲地射在墙上,射在树荫下正撇着膀子闭目养神的鸡身上,她甚至替众母鸡报了仇,撵着降服了桀骜不驯总凌驾于母鸡之上的大公鸡,把它浇成了落汤鸡。直到后来她爸到处借钱碰壁,最后还是她二姨借了之后,她才恍然明白,妈之所以尿得高,是因为娘家人给了台阶。
程晨总寄希望于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程父身上,所以她不停地替她爸做着换位思考,她想她爸会这么教训她妈:这就对了,上个高度换个角度看问题。这就好比说你,如果我平视过去,你长得还凑合,可我要低你一截看你,那我看到的,就是两只黑魆魆的鼻窟窿,也丑得够呛,她妈哈哈大笑着,也就同意了她爸的意见。
程晨微微扬起了嘴角,在静寂无人的房间里,她想起她爸打趣她妈,那样子是可爱孰不可爱!
可一等便是一天,一天对于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的人们来说,那是有多么漫长啊,希望该有多么渺茫啊。程晨又想起,他爸给她大姑家大哥说过,求人办事,打一个电话就行,如果不回话,要不不想办,要不办不了,不要打第二个电话,自讨无趣。
有些话在自己平心静气万事如意的时候听来没什么,但唯让你有醍醐灌顶的幡然醒悟,就是你终于处在说话人的境况里。所以到那一刻,她才觉得她爸那话说的岂无道理。
为了避免自讨无趣起见,她依然是等,等着为好。可又转念一想,这种概率很小,她了解她爸,在她爸的眼里没有坏人,凡事他都觉得“能理解”,所以还是要等着,等他笑嘻嘻打电话给她,她要她爸亲口跟她说,“只要是你喜欢的,爸爸都接受......什么时候领回来让爸爸见见......爸顾不上回去,要不你们来煤矿?……”
等待真是耗费精力的事,阿斯汗加班,程晨便想着各种方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给自己画上希特勒的胡子,再画上胡适先生的眼镜,跟阿斯汉聊QQ,然后跟他说想他了,让他打开摄像头,他先出现在屏幕上,问她:“人呢?”她“哧溜”抬头,一本正经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阿斯汉先是一愣,随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程晨告诉阿斯汉说,她给他制作了护眼罩,电脑盯久了戴着小憩小憩,问他要不要看看,他惊喜地打开摄像头,疑惑地低声喊到“人呢?”他吃过一亏,这次特别小心谨慎。她给自己的眼睛戴上胸罩,缓缓移动,几次大声问他:“看见了吗?”她听见他的椅子“哐当”倒在地上,想必他起得太猛,边笑边小声喊:“程晨,你赶紧拿走那玩意儿!”等她取下胸罩时,摄像头那边一片黑,原来他抻胳膊挡在前面;她穿上阿斯汉的衣服,头发高高扎起,对着背景墙走猫步;有一天,他发信息问女朋友:亲爱的在干什么呢?她回复:给你缝秋裤!他弗晓她意,一连串发了三个问号,她再淡定地回复他:秋裤小腹部位开了个洞,我给缝上了……
最让程晨忍俊不禁的是,阿斯汉让她抽空去检车,于是发信息给她:
“抽空把车送4s店。”
“好的,没空。”程晨回复。
“所以才叫你抽。”阿斯汉回复。
“好的,我一会儿抽。”程晨回复。
“抽的时候注意力度,今天风大。抽飞了我心疼!”
......
思绪如飘蓬断梗,在嘻嘻哈哈过后的百无聊赖里飘荡着:她愿意过步履公交的日子,她愿意要物穷于欲的日子,与他人无关。可即便爸同意,妈这关怎么过?真的如她所想,她妈就和颜悦色接受阿斯汉了吗?渐渐地,她的心幻化出一个透明窟窿,无论干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无法将之填补起来。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程晨毫无准备地拿出一张十万的储蓄卡,递给阿斯汉,他一愣,问她干什么?她在慌乱中收起卡,说自己拿错了。
爸不就是白手起家吗?他的一笔嫁妆不就够阿斯汉一辆车了吗?他只有她程晨一个女儿,他的财产不由她来继承吗?为什么非要阿斯汉也一样拥有很多呢?在阿斯汉的管理经营下让财产翻倍不也一样好吗?再说阿斯汉也不白吃白拿,他们只有她程晨一个孩子,阿斯汉必定要为他们养老送终不是?
有好几次,程晨都以为她爸很忙,白天顾不上打电话,所以在自己不小心睡着时会猛然坐起,翻看手机。她总觉得好多个时刻都是父亲该来电话的时刻:百合香气拱满一室的时候,月亮躲在楼房一角的时候,吃过一顿美味的鲫鱼汤的时候,看过一位踽踽独行的老人的时候,可事实上是,这些或温暖或失落的时刻,都成为她记忆中的一个小小的点,很轻,但只要想起这件事,那些小小的点就随之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当时那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或者,如果爸听到阿斯汉的情况时,他该同情阿斯汉,应该说,是阿斯汉这类人。如果一个物质过度匮乏的人变得富有,那么他会走两个极端,要不病态的骄傲,要不病态的同情,其实两种情况都出自一颗敏感的心:那个骄傲的他,刻意将自己与卑贱隔离,享受自我抬举的快感,骄傲便是他的保护伞,而那个贫穷的他,刻意将自己与卑贱一起,是贪恋被人抬举的快感,称赞便是他的墓志铭。所以,也只是同情。
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程晨终于下决心拨通了她爸的电话。程父貌似很开心,一声轻飘飘的“闺女”就说明了一切。她嘘寒问暖,问他过年要不要先去七大姑八大姨家走一圈,她爸说他都安排完了,想去玩也可以,她问他要不要陪着他买衣服之类,他说衣服都买了。
既然没有需要我的地方,我这个电话就算打完了吧,电话这头的程晨绝望地想。“对,对,我都安排了,张处长昨天跟我吃过饭,范局长那我也去了,你都嫑管,嗯......国家越来越重视安全,今年实行矿长下井带班制度,过年估计回不去,嗯,嗯。行,那挂了吧?”她没有说行,支吾着没挂断,程父听出女儿有事,赶紧问,“咋了?闺女?啊?”“没事,爸爸,过年不回来不行,家里就我跟我妈......”
程晨还是没能说出口,电话就已经变成了“嘟嘟”地忙音。
程晨看错了妈,她根本没有跟爸提及阿斯汉。
好事成双。
第二天早晨,程晨还在被窝里睡觉,王杰希的电话就来了,他劈头盖脸恭喜她,祝贺她,说程科长要多关照。程晨问他是不是梦游,他说:别装。“我这科长是你提的?”那同事一愣,疑惑道:你真不知道啊!程晨也一愣,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我懂了。
惊喜总是在不经意间。那天早上阿斯汉起床很早,亲手打扫了家,准备了热牛奶和三鲜水饺,准备了两碟小菜。程晨隐隐觉得,尘埃就要落定,是时候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