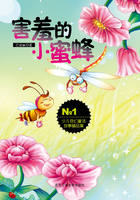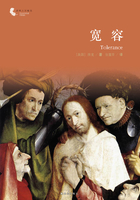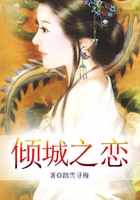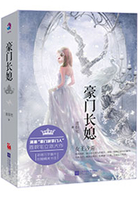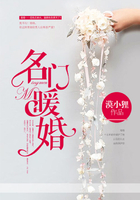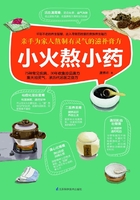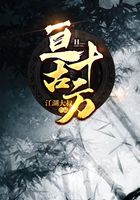如今在中国文坛提起刘庆邦的名字,简直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他的短篇,早已自成境界,多数作品像《鞋》《梅妞放羊》《响器》等等已成名篇。这些都是批评家们该发的言论,无须我们这些写印象记的人赘言。
印象当中,庆邦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平常他的话不多,一般在人多的场合,无论是集体出游还是聚会饮宴,总听不到他的声音,仿佛他这人并不在场。但每逢开口,必有妙语警句或噎人之语。就像他的小说,总是不声不响,却总是那么地道,透着股厚重底蕴和顽强坚韧性,还有眯缝起眼睛笑的那么一股聪明、狡黠的劲儿。
庆邦的祖籍是河南。关于河南人,北京当地多有恶评,最著名的要数董存瑞炸碉堡的段子,英雄人物最后喊的一句话是:“不要相信河南人。”但是对庆邦,相熟的朋友见面总爱逗他说:“你不像个河南人。”如同人们对上海男人说一句“你不像个上海人”那样,调侃之中是实在的褒奖。庆邦听了这话,每每也不言语,只是一味地坏乐。河南籍的刘庆邦实在是个老实人,偶尔还有一点蔫儿坏,笑时不露齿,两腮憋出酒窝,眼睛眯成一条缝。出门总是背一个军挎,夏天的时候是军挎配白衬衫,冬天或者春秋季节就是军挎配小立领的唐装。草绿色的小军用书包几乎成了刘庆邦的标志性装扮。这个纪念物,是否在表明他在怀恋当年——他青春年少时代挤在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中间去韶山、去北京大串联的经历?不得而知。只知每逢他给我们这些后生讲起他那段“准红卫兵”历史时,往往都是眉飞色舞,深深自我感动和陶醉。
跟庆邦相识一晃已经有些年头。他是北京作家里受众人爱戴的一个。为人和善,有师长之风。庆邦是个喜欢喝慢酒、说慢话的人。每逢有几个对脾气的朋友把酒围炉而坐,推杯换盏,酒热耳酣,庆邦就脸色微酡,情绪渐渐入港,话也就慢慢绵长。有一年,一个文友送了他一箱“酒鬼”,我们几个爱喝酒又平常说话慢的人就跟他沾了光,跟着足足喝了一秋天又一冬天好酒。那真是幸福的好时光。闲来无事庆邦就喊我们喝酒,有时提拎着酒到作协林斤澜老人家里喝。林老也是慢慢说话、慢慢品酒的人,再加上庆邦的慢慢悠悠,我们就一边小酌,一边听他们讲古道今,味道十分醇厚。有时也抱着酒到“九头鸟”去,跟湖北的辣子叫劲;有时就随便捡就近的小酒馆,要几个没什么名堂的下酒小菜,朋友间慢慢叙旧,话时短时长,酒时慢时快,不知不觉,四五个人,两瓶酒喝光了。散时,醉醺醺的,有点明白“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的意趣。
2000年,我有幸跟庆邦同时签约于北京作协,成为“合同制作家”,差不多属于是“一个单位”的了,在大会小会上更经常碰面。每年年终述职时,庆邦总是高产大户。听他叨咕他的那些巨大的创作量,每年总是十几个短篇,外加中篇,外加每篇小说几乎都被各家选刊转载一遍,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可不就频频闪烁、每每闪耀“刘庆邦”这个光辉名字嘛!那时候他还要边写作边主持煤矿文联的一部分工作,其工作的辛苦及其写作的勤奋程度可想而知。
庆邦的文章也跟他的人一样,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徐,浓描细画,充满了艺术上的悠久耐心。把他的作品连成序列,就会发现,除了写矿工题材,写那些生活在地球底层人们的人性、人情以及彼此间的仇杀与宽宥等等之外,再有就是写女性题材他也是个大拿。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男性作家中,写女人写得好的还真就是寥寥无几。2003年年初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小说选刊》发奖会上,《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两个小女记者手捧刊物到处送人,而且提出专门要找写女性题材的作家赠送。选刊的老师就把小女记者领到台前领奖的苏童和毕飞宇跟前,说:“喏,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关心妇女题材的老师。”接着又四下寻摸着,说:“庆邦来了吗?刘庆邦来了没有?”
呵呵。不知后来庆邦接到那份反映妇女生活的刊物没有。看来他关心妇女题材的创作,已经为人所认可。
说他是男作家中最会写女性题材的几个人之一,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周作人曾经说过,考察一个男人的品性,一个是看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是看他如何对待女人。庆邦文章中对女人有充分的体恤、关爱、善待,有悲悯之情和同情之心,往往将她们形同自己的姐妹。他的众多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而且是乡村原始生命力旺盛、个性充分发展的女性。像《嫂子和处子》《姐妹》《不定嫁给谁》《相家》《女儿家》等等中的女主角,都是这类角色。故事都是在男女关系中展开,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紧张感,并调动起读者对结局的预期。
《嫂子和处子》中的两个女人——二嫂和会嫂在民儿面前的强悍、盛气凌人、恃强凌弱、强迫就范,让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失去了童子之身,这简直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女权的性政治文本。在这里,“强奸”的主角是由女性担当的,男性是被欺凌与被强奸的弱者。《姐妹》里来自同一个庄上的福梅和福兰,先后嫁到外乡以后开始还好得跟姐妹一般,后来因为彼此不经意说了各自的底细,一个说另一个小时候到了12岁还尿床,另一个说对方小时候曾偷过队里的红薯,因而两人交恶,事态进一步扩大之后两人发展成仇人。所谓“姐妹情谊”就因为彼此揭短的一句话而崩塌。庆邦在此得出的最深刻的结论是,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后,都不愿意带着自己过去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属于阴影的部分。因此福梅后悔把福兰也引荐嫁到庄上来,“她把陈庄的闺女拉扯到卞庄,等于把她的底细也拉扯过来了。一个人走到哪里,你的底细老是像影子一样跟着你,终归不是什么好事”。(刘庆邦:《姐妹》《十月》2001年第2期刊载)文中写的虽然是两个女人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写“政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政治。
在这些意旨深远的小说中,庆邦似乎总是适时地对女权主义的理论进行不动声色的反诘。甭管她们叫嚷的什么“姐妹之邦”情谊之类的,实际上纯粹都是瞎扯,在人的行为因素中,“利益”才是至关紧要的,不管男人女人,谁欺负谁,谁强奸谁,谁跟谁好或者不跟谁好,最终都要服从于利益原则。
而另一类至真至纯的乡间女子形象的刻画,则充分表明了刘庆邦的美学原则。像《鞋》里给对象做鞋的姑娘守明,《梅妞放羊》里边的梅妞,《响器》里吹大笛的姑娘高妮,她们都天真未凿,充满人性的善良和质朴。几个故事本身不让我们惊异,我们惊异的却是作家对于女性心理的细腻把握和逼真描绘。若说《响器》和《鞋》里人与音乐合一、人在恋爱阶段的思维还算比较好展现的话,那么梅妞在与小羊羔亲昵嬉戏时产生的身体萌动就不那么好表达了。庆邦却也能给写得惟妙惟肖,还稍微有那么点“情色”色彩,真不知道他对女人的全身心的深刻理解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最早读的刘庆邦的作品是他的《家道》和《走窑汉》,那是充分显示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刻写力度的作品,已经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称赞,获得过多方面的好评。接续《家道》这一系列的是《葬礼》和《户主》等与作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的作品,它们是从作家血液和血缘深处流淌出来的东西,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而接续《走窑汉》系列的是《神木》《幸福票》《在牲口屋》一类,那也是作家生活经历的又一种见证,而且是刻骨铭心的生活往事。对于矿井和矿工生活的描写,将会是他终生挥之不去的题材。相比之下,他的那些描写女性生活的题材,倒像是顺手拈来,毫不费力,想表达什么意思,就借着这些女人们的形象表达一些什么意思,一般不会让自己的感情和别人的情绪伤筋动骨,在艺术上也是纯熟、老到,倒有点像炫技的意思了呢!
在新的一年的总结会上,庆邦的身份已经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了他那更加巨大的创作生产量之后,他抚今追昔,不由自主发感慨:倘若不努力工作,便无以对得起这份职业。他说他甚至连每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起来,也还是照常要坐到书桌前进行创作。勤奋工作不光成为了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同时也在表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善良的人总会有好的回报的。祝愿庆邦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万事大吉!
2003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