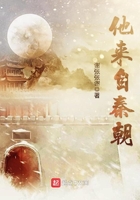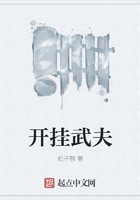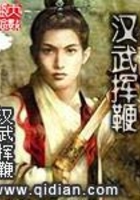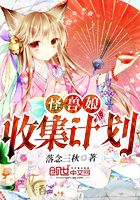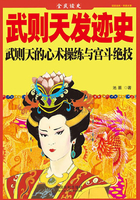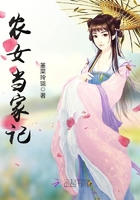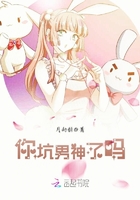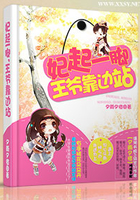武帝因了与匈奴和战之事,奶孙两人闹得别别扭扭。回到昭阳宫后,本想与阿娇诉诉心中委屈,不料那小阿娇却因武帝没得心思欢好而心血沸腾,口出脏言。心道:自家端底成了孤家寡人,在朝廷之上,守旧势力堵塞前进道路;廷宫之内,又有老太婆截住后退之径;俩口之间,兀是那阿娇胡搅蛮缠。所以,他一怒之下,独步宫院,茫茫心事一发融入沉沉夜空。和亲之事已成定局,只好容后徐图,致于改除其他旧制,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武帝仰观太虚,晓星烁烁。审视夜海,晨曦将露。黎明曙光,隐约可见。忧郁之心稍有好转,凝眸又思道:欲图兴国霸业,必须社稷良材。欲擢良材,当选良儒。欲选良儒,必罢百墨。欲罢百墨,必犯祖母。忠孝两全之策,搜索苦肠,实难想出。何人能够为朕分忧?谁人能够解朕疑难?思想及此,又添烦乱。索性摇头定神,摒弃私心杂念。忽然来了诗兴,信口吟诵道:濡露繁星夜,洒银晓月天。一想到“天”字,武帝连声重复:天,天,瞒天过海。有道是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外,太阳太阴是也。为何不以举荐文学之士为名,招选精儒治世之人?意欲罢黜百墨而暂容之,要想独尊儒道则渐行之。诚然如此,必能瞒过太皇太后,取得她的应允。一想到朝政将有转机,抱负即将实现,不由自主的高兴起来。
武帝为了使太皇太后失去防备,早晚问安之际,总要与太皇太后拉家常聊闲话,因势利导。大赞黄老学说是绝世高论,偶尔也稍稍提及《论语》风雅文笔。甚至颂经如流:天下事皆有自然之理,顺之则事简,逆之荆棘生。所谓象时顺节气,安静顺鸿蒙。治国之道贵乎清静,与民休闲乱不生等等,而且盛赞太皇太后德才过人。只夸得太皇太后飘然欲仙,反过来也称赞武帝是治世明君。
九九重阳佳节,正是太皇太后六十五岁寿诞。文、景两帝在位之时,因皆奉行节俭,即皇帝寿辰也未太过操办,太后、皇后生日从简更是自然之事。如今太皇太后已是花甲零五,余生尚有几何?非唯武帝心下了然,即太皇太后自己亦有自知之明。而且太皇太后身体又每况愈下,若在有生之年,能够欢度余生寿辰,万千臣民祝她万寿无疆,老祖母必然欣喜若狂。趁此良机,天大事情老太太也会应允。武帝主意一定,便好言劝得太皇太后恩准,颁诏天下,大贺三日。满朝文武,诸王侯国都要为太皇太后祝寿。又令文人儒生为大寿赋联征对。到得重阳这日,举国上下爆竹声声,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宫娥嫔妃盛装浓抹。诸般王侯将相三公九卿,早早入朝,列于两班。宫内诸妃俱在未央偏殿等候,只待太皇太后驾临。一切准备停当,却是良辰将至。武帝便到长乐宫请太皇太后临驾接受朝拜。
一大早,皇后阿娇即赶至长乐宫中,与太皇太后一干侍女一起,为太皇太后沐浴更衣,梳妆打扮。太皇太后虽已年过花甲,总归是天下第一家出身,一生里何曾受过劳作之苦?几曾里有过日晒雨淋?何况平时还有参、芪、冬虫大补之类服用,再加上本来就是雍容华贵气质高雅之人,一番精心打扮之后,端底却是与众不同。但见她:
一只金凤落云额,?两挂翠珠耳下悬。
发髻可可插玉簪,?满头乌发如墨染。
片片红霞脸上照,?两弯月下星娇娆。
绣凤彩缎飘春风,?柳腰环佩响叮咚。
太皇太后被一干人等打扮齐毕,不由自主对镜自怜道:“老了老了,真是光阴似箭,韶华易逝,眨眼之间老身已是垂暮之年,没有几载阳寿了。”
王太后笑道:“太皇太后一生积德行善,自有上天保佑,福寿双全,万寿无疆。”
众人一发随声附和,都道老人家必能得道为仙,与天同寿,长生不老。正说笑间,武帝来到长乐宫请太皇太后临朝受拜。太皇太后一边夸奖武帝孝顺,一边满面春风蹬上御辇,直向未央宫中进发。
英帝刘彻扶着太皇太后御辇,一路吹吹打打,前呼后拥,来到未央宫正殿后,太皇太后满面春风,正襟危坐于御座之后,司仪官一声高喊:“太皇太后六十五春寿诞现在开始。”
刹间,爆竹声声,古乐齐鸣。武帝率先跪拜道:“皇孙祝太皇太后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众人皆跪拜山呼,声震九天,煞是壮观。
如此盛典,太皇太后有生一来何曾见过?风烛残年之时,亲历寿诞大殿,喜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一连声道:“甚好甚好,奇观奇观。”言尤未了,武帝又传旨道:“有为太皇太后喜寿吟出佳章绝句者,即刻呈上,由老寿星亲揽选定佳作后,再由乐府即刻作曲排舞,当廷演唱。”
圣旨刚宣,一班早已跃跃欲试文人,争先恐后,搜索苦肠,要在武帝和太皇太后面前展示文采,邀得主宠求得前程。不一刻钟,佳联绝句纷纷呈上。太皇太后一一过目,连连称赞,并在其中选了一首佳作,众人看时其文乃道:
王母诞,天下欢。
瑶池宴,聚金殿。
朱火扬烟雾,博山吐微响。
清樽发朱颜,四海乐且康。
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
诗文一定,早有汉家乐府乐师李延年,按角、徵、宫、商、羽五音谱就绝世音乐一曲。乐府歌女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听音乐便即心领神会。金殿之上,就着那琴瑟钟筝蹦出之叮咚仙符,曼开金喉,轻舒长袖,翩翩起舞。真真乃是“舞袖飘金殿,歌声绕凤台。莺啭鸟啼声,仿是春风来。”轻轻搔着寿星老人心房。直看得太皇太后目不暇接,如醉如痴。其实像这般规模庆典,歌舞岂是临时排就?都是武帝预先安排停当,只不过恰恰的瞒过太皇太后昏花老眼便了。
正值太皇太后高兴之际,武帝笑着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何为太皇太后来。我大汉盛德泽及四海八极,天下文人雅士多如牛毛,择其皎皎者为我所用如何?”
太皇太后笑着边看歌舞边漫不经意道:“依你依你。你是皇帝,说了算数,君无戏言,君无戏言。”真格聪明不过帝王。当下便传诏天下道:
朕闻:
欲治国而不用之材,尤欲其入而又闭其门。方今,普天之下沐先皇遗德,国泰民安,人才辈出,朕不敏睿,目蒙耳塞,未能择用,真深后悔。今诏令丞相、御史、列侯、郎守、诸侯相秩二千石者,必须推举贤良、文学、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当廷问对,择优选用。凡二千石不举荐者,以蔑视朝廷罪论处。
太皇太后寿诞已过,武帝诏书也已传遍天下,诸官那个敢于怠慢圣旨?纷纷推荐本地圣贤。于是,广川人董仲舒、甾传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等名儒学士统共七百余人,被推荐入都,参加廷试。廷试这日,武帝早早正冠端袍,坐于御案之前,亲自监考。考场四周,皇家卫士戒备森严。考场之上,七百考生齐坐案前,文房四宝一应物什业已备齐。监考官卫绾一声开考令下,只听“窸嗦嗦”一片弄笔之声,犹如山溪溅石,风吹桦叶。众考生开题看来,原来是讲论治国安邦之道的文章。题目一出,所有考生统皆凝神细思,笔走龙蛇,施展出平生所学,要博得皇帝恩宠,求得一官半职。武帝在御案之前,看着考生作卷,慢睁龙目,恰好看见一位老者,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甚觉诧异,便手指老者轻声问卫绾道:“那公是谁?”
卫绾道:“此人叫董仲舒,是广川人。”
武帝听了便步下丹墀,踱到身后观看此董仲舒答卷。此时恰好作完住笔,但见其文道: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复含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以溥(音仆pu广大)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仁者君之所以爱。夏者天之所以长,德者君之所以养,秋者天之所以杀,刑者君之所以罚。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应人之所为,其善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天之一端也……。”
看了仲舒文章,武帝甚是高兴,连连颔首称是。正好日已正午,都到收卷时间,武帝即回到未央宫宣室草草用过午膳,展卷逐一细审。谁料满怀希望,却是事与愿违。考卷多是黄老刑名老生常谈,全无半点新论新意。无奈又将仲舒文章拿来细读。越读越觉得文中那些天人相应观点,木、火、土、金、水五行生克制化之理,阴盛阳衰,阳盛阴衰,互相斗争,永无止境的治化之理,实为治国安邦大道。不禁拍案叫绝,连道奇文奇才。看到仲舒文章,武帝决心要重用此人,又怕太皇太后制肘,武帝不禁长叹一声,陷入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