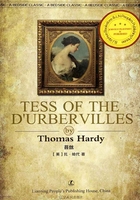“沈卿,一切可还顺利。”太后背对着他,背影看起来依旧威严,这个女人陪在先帝身边三十载,数次被厌弃,她却能次次逆转局势,从一位王妃做到楼兰太后,心机与手段可见一斑,朝中根深蒂固,话说良禽择佳木而栖,自己也是无法选择,如今的王上是万万动不了这个女人的,他俯下身子,毕恭毕敬道:
“都已安排妥当,王上查不到任何痕迹。”
“好,沈卿如此得力。”她手中握住一樽酒,说话间洒了出来,她将酒缓缓倒出,在空中划出一条水柱,透过水柱她仿佛望见那个女人的脸,有的只是痛苦、哀切,不由得扬起了嘴角。
“城防缺个差人,我出去后你便做公车令吧。”
这可是美差,专管宫中的防卫,整个王城的安危都受他管辖,面对如此殊荣,他将头俯得更低了些,掩盖住嘴角贪婪的笑容,答道,
“谢太后。”
“我早说王儿为了一个女人着迷,冤枉母后的用心,我所做的事,都是光明正大的,倒是你,竟敢让金吾卫调查母亲。”
一月后,她终于被放了出来,一处宫门就直奔大殿,质问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儿。
“母亲没做过就最好,这样也算是让外头的人知道母亲没有滥权,没有与外戚勾结,私自联络他国。”
“你……现在果然不听我的话了,只说些这样狠心的话来伤母亲的心。”她顾自用帕子掩住眼睛,十分凄苦。
“母亲,”靳朔上前握住她的双肩,微微用力,算是安慰她了,他不愿看见母亲流泪,
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儿依旧是在意她的,擦过眼角,平静道:
“但有一件,王儿可去打探好那个褚氏的底细了,当日三军统帅力保此人,你又轻易放权,母亲担心的很。”
“问过了,属实是南甸人,颇有些才学胆识,是征战沙场的好苗子,此次在军中也是屡立战功,近日征讨西楚的事也该将歇,他们已讨回了城池,想来不日便该班师回朝了。”
“西楚军刚刚溃败,为何不乘胜追击,我们也夺去他十座城池,叫西楚也尝尝这切肤之痛。”
“不可,母亲,”他打断,
“己所不欲,何况此次战役打得实在艰辛,能大获全胜已该十分庆幸了,不可再盲目自大,再打下去只有耗损自身这一个结果。”
“政事上,母亲这后宫妇人确实不该过问,做主的只能是孩儿你。”
她声音落寞,只是个孤立无援的老妇人,靳朔不忍心,替母亲整理了下散乱的发髻。
“而母亲,定会助你坐稳这江山。”她激动地抓住儿子的手,
“母亲今日气色看起来怎么这样差,发髻也梳的这样散乱,定是底下的人不用心,我必要好好责罚。”靳朔却不想回答,只岔开话题,
“不,不是他们。”太后拦下就要走出去的儿子,
“是母亲自己最近夜夜难眠,晨起昏昏沉沉,走路晃荡,顾不得仪态,这才仪容有损,这几日我心头好像压着一块巨石,总喘不过起来,叫了几次太医令的人,却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似乎有些难言之隐,犹豫着说道,
“司天监昨夜来报,说是星象有变,有煞气直犯我宫中,说母后不日便有血光之灾。”说着又要落下泪来,
“这……那该如何化解。”靳朔信以为真,
“说是戍卫宫中的公车令与我生辰相冲……”
“木匀,你去安排。”靳朔不疑,吩咐下去。
“绿意,你说我的孩儿是男是女?”
“定是个小公主,像公主您一样美。”
“可我却觉得是个男孩,他在我肚里调皮得很,夜里总是不安分。”
“小公主或是小王子都好,到他生出来,我一定好好跟他说说,公主你怀他如何艰辛。”
“你去为我办件事。”
“喏。”
大易三十六年隆冬,塞外十分严寒,冻死的牛马横七竖八倒在大漠上,今年的楼兰处境尤为艰难,冬至日那天,本该易市的波斯商人也无人冒险穿过尤其凶险的白龙堆,未楼兰带来西方的珍宝,楼兰失了最后一刻生机,蠢蠢欲动的易国铁骑正踏过真主的神祠,带着寸草不生的杀意而来。
“如何?”
“至此已过两日了,王后若再无法诞下公主,王便要下令,留下公主或是王后了。”
“这是何种选择?孤要你们何用!”
“王上,臣等已经尽力了。”太医令背上的冷汗已浸透了衣衫,花白的发间也汗涔涔的,
昨日元辰,她便受此痛苦,产房外,他只眼睁睁看着一盆盆血水出来,殷红刺眼,又无计可施。
“王儿莫要心急,哪个女人生孩子都必要到鬼门外走一遭,此刻你该在前朝,而非后宫,你守了她两日,外殿的大臣等了你两日,你将我楼兰陷入何地?”她无奈,
“前朝后宫,何处有孩儿的立锥之地?母亲事事为我好,为楼兰着想,此时,母后也不该在此,还是代孩儿去前朝协力政事罢。”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她捂住胸口,倒下前身后的大嬷嬷扶住了她,撑着身子,
“朔儿,我知你现在如何都不肯信我,今日母后以自己的性命发誓,绝不害她,若违誓言,便让母后受尽烈火酷刑而死,灵魂不得归天。”
靳朔望着眼前的母亲,目光坚定,有如孩提时牵着他的手将他送上王位时那般决绝,他选择再信她一次,
转身,在此刻先放下她。
“来人,给我围住王后宫,不准任何人出入。”太后下令,眼中已没有刚刚的诚恳,恢复平日的狠绝,
“公车令,将萨巫放入宫来,今日我要这贱妇及她的孽种在神的诅咒中死去,让她永远不能再来害我的孩儿。”
长平门外,一个列队悄悄接近王后宫,脱下宽大罩袍,里面是七色的巫衣,上面绘着上古的恶灵,传说只要有人正视萨巫便会得到诅咒,生死寂灭,永不存在,魂魄也只能堕入地狱。
听见萨巫手中的摇铃,无不从心底最深处升起一股阴冷的寒气,只叫人瞬时便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摇铃摄人心魂,叫听见的人想起心底最恐惧的事,列队而来,像是招人魂魄的恶灵降世,在院中施着咒人的符法。
一院子的人都已陷入恐惧中,个个瑟缩在墙角中,
大嬷嬷为太后掩着耳目,一行人早已掩身进入西厢暂避,
产房内的女子已三魂尽失,只留着最后一丝气力,听得她沉吟一声,
“安南,我随你去了。”
身后传来一声啼哭,冬至日里的孩子降生了,女子闭上了眼,邢国的芍花片片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