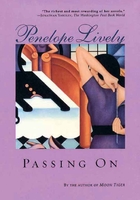位于哈德逊街的白马酒馆成了他们愉快的聚会场所。他们通常四人——比尔、戴安娜和达文波特夫妇——偶尔有些时候,保罗会带佩基到上城来,跟他们一起围着张湿乎乎的褐色圆桌而坐,喝酒谈笑,甚至唱歌,这些夜晚更快乐。迈克尔一直喜欢唱歌,能记住一些不怎么出名的歌曲的完整歌词,而且通常他知道适可而止,为此他颇感自豪。尽管有些晚上,露茜得朝他皱眉或捅捅他才能让他安静下来。
这正是狄兰·托马斯之死令白马出名前不多久[9]的事。(“我们从没在那里见到过他,”迈克尔后来好些年还在抱怨。“那不是最倒霉的事吗?我们几乎每晚都坐在白马里面,居然从没见过他——怎么可能错过那样一张脸呢?天啊,我甚至不知道他死在美国。”)
诗人之死带来的后果是,似乎所有纽约人晚上都想上白马酒馆来喝酒——结果这地方反而没什么吸引力了。
到那年春天,连这座城市对达文波特夫妇也失去了吸引力。女儿四岁了,看来在郊区找个地方更合理,当然,得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他们选的小镇名叫拉齐蒙,与他们去过的其他小镇相比,露茜觉得这儿更“文明”一点。他们租下的房子正好满足他们当下的需要。它很不错:是工作的好地方,也是休闲的好去处。后院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劳拉可以在那里玩耍。
“郊区人!”比尔·布诺克夸张地大叫起来,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挥舞着波旁酒瓶,那是他祝贺他们乔迁之喜送的礼物。戴安娜·梅特兰两手挽着他的胳膊,笑脸紧贴着他的外套,仿佛在说他这种搞笑正是她最爱之处。
当他们四人一路欢声笑语从拉齐蒙人行道拐上去新家的短短一段路时,比尔似乎不愿打破自己营造的欢闹气氛。“天啊,”他说,“瞧瞧!瞧瞧你们俩!你们像电影里刚结婚的年轻夫妇——要不就是《好主妇》杂志里的!”
达文波特夫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尽量笑着。倒完酒,四人在客厅里落座后,迈克尔但愿这种玩笑快点结束,可比尔·布诺克还没完:他端着酒杯的那只手的食指伸出来,先指着露茜,然后指着迈克尔,他俩并排坐在沙发上时,比尔·布诺克接着说,“勃朗黛和达伍德。[10]”
戴安娜几乎从座位上滚落下来,这是迈克尔第一次不喜欢她。更糟的是,当晚她还有件事让他再次反感。那是在谈话转到别的话题,大家也没那么拘束后,布诺克仿佛对他早前说的话略感抱歉,认真表示很想看看这个小镇的全貌,于是四人在茂密的林荫道下漫步了很久。迈克尔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游玩拉齐蒙的最佳时刻:黑暗中,刺眼、压抑的整洁软化柔和了,从林荫道的斑驳绿意中望去,亮着灯光的窗口给人宁静有序、富足祥和之感。安静极了,连空气闻上去也很美好。
“……不,我当然明白它的魅力,”比尔·布诺克说。“没有任何差池、一切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如果你结了婚,有了家庭,我想,这正是你想要的。事实上,肯定有无数人不顾一切想住在这里——比如,我以前在工会工作的许多同事就这样。然而,对于某些气质的人来说,这儿不适合他们。”他朝戴安娜挤挤眼。“你能想象保罗住在这种地方吗?”
“天啊,”戴安娜轻声说,哆嗦了一下,迈克尔似乎能听到哆嗦声,害得他的后脊梁也跟着抖了一下。“他会死的。保罗绝对、绝对会死在这里。”
“我说,难道她不知道那样说很他妈不得体吗?”客人们走后,迈克尔对妻子说。“见鬼,她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那个愚蠢的‘勃朗黛和达伍德’笑话让她笑成那样,我也不喜欢。”
“我知道,”露茜安慰他说。“我知道,好了,今天晚上过得很——很尴尬。”
他很高兴他首先爆发,如果今晚他控制自己不发作,那可能就是露茜首先发作——而她的发作,不是生气,很可能是掉眼泪。
在拉齐蒙家里的阁楼一隅,迈克尔做了个书房——不是很大,却是完全私人的空间——他天天盼着独自在那儿的几个小时。他再次觉得他的书初具雏形,就快完工,只要他能完成最后那首统领所有诗篇的长诗。他给那首诗取了个恰当的名字——“坦白”,但有几行诗一直缺乏生气;结果整首诗似乎要崩溃或消失在他笔下。大多数夜晚他在阁楼上工作,累到浑身酸痛。也有些时候,他找不到感觉,只得抽烟枯坐,浑身麻木、精神涣散,鄙视自己,最后只好下楼睡觉。即使他睡眠不足,没休息好,第二天大清早还得混进拥挤的人群中赶去上班。
从家门在他身后合上那一刻起,他便卷入赶往火车站的汹涌人流中。他们跟他年纪相仿或比他年长十几二十岁,有些人甚至上了六十,他们似乎对彼此的一致颇为自豪:挺括的深色西装,保守的领带,擦得锃亮的皮鞋,迈着军人似的步伐,走在人行道上。只有很少几个人是单独走着的;其他人几乎都有一个说话的同伴,大部分人三五成群地走着。迈克尔尽量不东张西望,免得招来友好的微笑——谁他妈需要这些家伙?——但他也不喜欢孤单,因为这很容易勾起他在军队中的痛苦回忆:在谈笑风生、适应性好的战友中,一言不发。当他们列队成群走进拉齐蒙车站后,这种不自在最为强烈,因为在那里除了站着等车之外别无他事可做。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倚墙而立,透过不锈钢边眼镜,乜眼盯着香烟发呆,仿佛抽烟需要他集中全副注意力。这人个头比迈克尔小,看着更年轻,他的穿着不太得体:没穿西装,而是穿着坦克手夹克。在欧洲战场上时,这种结实耐穿的防风夹克曾让许多步兵羡慕不已,因为这种军装只发给坦克装甲部队的士兵。
迈克尔挪近些,好跟这人说话。他问:“你是装甲部队的?”
“啊?”
“我说战争中你是不是在装甲部队?”
年轻人看上去有点迷惑,镜片后的眼睛眨了好几下。“哦,这件夹克,”他终于说,“不不,这是我从一个家伙手上买来的,如此而已。”
“噢,我明白了。”迈克尔知道如果他说:嗯,这是桩好买卖,它们值得拥有,他会觉得自己更像个傻瓜,所以他闭上嘴,转身要走。
但是这个陌生人显然不想独自待着,“不过,我没打过仗。”他说。那种快速、下意识的道歉式口吻是比尔·布诺克常有的说话风格。“我直到四五年才参军,我从没到过海外,甚至从没离开过得克萨斯州的布兰查德基地。”
“噢,是吗?”这下话匣子打开了。“嗯,我四三年时在布兰查德待了一段时间,”迈克尔说,“打死我也不想留在那里了。他们让你在那儿做什么?”
这个年轻人脸上突然露出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乐队,伙计,”他说。“他妈的行军乐队。参军时我犯了个错,告诉面试我的人说我以前打过鼓,所以,你瞧,等我完成基本军训后,他妈的,他们把军鼓挂在我身上。行军鼓,咔嗒、咔嗒,降旗军鼓、正式行军军鼓、颁奖仪式,所有那些米老鼠类的东西。天啊,我差点以为自己无法活着从那里出来了。”
“那你是搞音乐的?参军前?”
“哦,不完全是。还没拿到工会卡[11],但我一直喜欢摆弄音乐。那么你在布兰查德做什么?基本训练吗?”
“不,我是个机枪手。”
“是吗?”那个年轻人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露出小男孩般的热切神情。“你是空军机枪手?”
接下来又是一场愉快的谈话,就像在哈佛、在《连锁店时代》的办公室时一样,他只要尽量简洁地回答问题就行了,他能感觉到自己在听众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嗯,是的,二战时他在空军——第八空军;从英格兰起飞,没有,他从没被打下来过,也没受过伤,可是有几次他怕得要命;噢,是的,当然是真的,英国女孩真的很棒;是的,不;是的,不。
像以前一样,在听众兴趣消退前,他赶紧转换话题。他问年轻人在拉齐蒙住了多久——才一年——结婚了吗。
“噢,当然;谁没有?在这儿你认识没结婚的人吗?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来拉齐蒙的原因,伙计。”他有四个孩子,全是男孩,每个相差一岁左右。“我妻子是个天主教徒,”他解释说,“她很久以来对那个一直固执得要命。我觉得现在总算说服她了,不过——不管怎样,希望如此。我是说,孩子们很好、很可爱,但是四个足够了。”于是他问迈克尔住在哪里,知道后他说,“哇,你拥有那一整套房子?真不错。我们刚买了一套楼上的公寓。不过,比在扬克斯时过得要好。我们在扬克斯住了三年,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等火车轰隆隆进站时,他们已经握手交换了姓名——这个陌生人名叫汤姆·尼尔森——他们走出来,到了月台上,迈克尔才发现他带着一卷纸,用根橡皮筋松松地捆着。但那纸看上去不够软也不干净,不像是纸巾;上头有些斑驳、反复拿捏过的痕迹,让人觉得像是辛苦画好的零件或工具的“说明图”,也许是汤姆·尼尔森的老板(修车铺的老板?包工头?)今天要的东西,尼尔森可能得在长岛某间阴暗的仓库里花上好几个小时去找那些零件。
如果不再发生别的事,跟汤姆·尼尔森一同坐火车进城可以成为今晚的谈资,告诉露茜几件可悲、可笑的事情:这个倒霉的、虔诚的、太过年轻的四个孩子的父亲,这个悻悻然在布兰查德基地咚咚咚敲着军鼓的家伙,甚至连件坦克夹克都没混到,更别提工会卡了。
一路上他俩坐在一起,刚开始两人都沉默着没有吭声,仿佛在找新话题;后来,迈克尔说:“布兰查德基地举办过拳击锦标赛,那时候你在那儿吗?”
“哦,是的,一直都有固定的比赛时间,很是鼓舞士气,你喜欢看吗?”
“嗯,”迈克尔说,“事实上,我参加过比赛,中轻量级的,打入了半决赛;后来,那个后勤中士用左刺拳把我打趴下了——从来没碰到过那样的左刺拳,他也知道怎么使用右手。第八回合时,从技术上讲他把我击倒了。”
“真要命,”尼尔森说,“当然,因为眼睛不好,我从来不去做这类事;不过,即使眼睛好,我可能也不会去试。差点打入决赛,你可真行啊你。那么你现在做什么?”
“哦,我是个作家,或者说至少我在试着写诗写剧本。有一本诗集就快写完了;有一两个剧本在小范围内上演过,就在波士顿这一带。不过,现在,我在城里找了份商业写作的活——你知道,得买柴米油盐呀。”
“是的。”汤姆·尼尔森侧脸看了他一眼,善意地眨眼笑他。“天啊,空中机枪手、拳击手、诗人和剧作家。知道吗?你真他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不管善意与否,这种玩笑让人很受伤。这个小杂种是谁?最糟糕最痛苦的是迈克尔只能承认这是他自找的。尊严与克制是他最为看重的,那么,为什么,他总是,他总是信口开河,随口乱说呢?
虽然保罗·梅特兰那种人并不会真的“死”在拉齐蒙,但显然他绝不会在拉齐蒙的通勤火车上将自己向某个傻瓜和盘托出,还招来他的取笑。
不过汤姆·尼尔森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给迈克尔造成的伤害。“其实,诗歌对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他说。“我不能写诗来养家,可我一直喜欢读诗。你喜欢霍普金斯的诗吗?”
“非常喜欢。”
“是的,他多少能触动你的灵魂深处,是不是?就像济慈;叶芝后期的某些诗作也一样。我爱死了威尔弗瑞德·欧文,伊文·萨松也还行。我还喜欢一些法国诗人,瓦雷里那样的诗人,可我觉得除非懂法语,否则很难领悟他们的东西。我以前很喜欢为诗歌配插图——这样大干过好几年,以后我可能还会做回去,但我现在主要画些普通一点的画。”
“那么,你是个画家?”
“噢,是的,是的。我以为我跟你说过了。”
“没有,你没说过。你在纽约工作吗?”
“不,在家工作。有时候把画好的东西送到城里去而已。一个月两三次吧。”
“那么你能——”迈克尔正要说“你能靠画画养家吗?”可他打住了,问一个画家如何挣钱养家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于是他说,“——那你能全职画画吗?”
“哦,是的。不过,以前我得回扬克斯教书——我在那儿教高中——但后来情况有所好转。”
迈克尔小心翼翼、冒险地问了个技术问题:尼尔森画的是不是油画?
“不,我试过,我对油画没太多感觉。我画水彩画,用笔墨勾勒轮廓,然后刷色——就这么简单,我在画画上仅限于此。”
那么,也许他局限于广告公司的艺术部门,因为“水彩画”很容易让人想起泊在岸边的小舟或展翅的群鸟等怡人小风景。他也可能局限于那种沉闷窒息的礼品画,在礼品店里,那种画跟昂贵的烟灰缸、粉红色的牧羊人牧羊女雕像,还有印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先生夫人肖像的餐碟摆在一起出售。
再问一两个问题即可把事情完全弄清楚,可迈克尔不想再冒险。他沉默了,直到火车把他们带进喧闹拥挤的中央火车站。
“你往哪儿走?”当他们走进城市刺眼的阳光下时,尼尔森问。“往南还是往北?”
“往北到五十九街。”
“好;我可以跟你走到五十三街。得去那儿的‘现代’报到。”
他们一路走,迈克尔一路想,等他们拐到第五大道时,迈克尔总算弄明白“去现代报到”是什么意思了,那是说他跟现代艺术博物馆约好了见面。迈克尔希望他能找到什么方法跟尼尔森一起去那里看看——他想看看尼尔森去那里到底做什么——最后,当他们走到五十三街时,还是尼尔森提出了这个建议。“想跟我一起进去吗?”他说。“几分钟而已,然后我们可以再朝北往你那儿去。”
当穿制服的人为他们拉开厚厚的玻璃门时,看门人的脸上似乎闪现出一丝敬意,开电梯的人也是,虽然迈克尔无法确定这是否只是他的想象。但到了楼上,走进一间安静的大房间后,远在房间那头的接待处,看见一名绝色美女摘下角质架眼镜,可爱的眼睛里闪耀着敬慕与欢迎之情时,迈克尔知道这不是他的想象,这是真而又真的。
“喔,托玛斯·尼尔森,”她说。“现在我可知道了,今天是个好日子。”
换作普通女孩,可能还是待在座位上,拿起电话,摁下一两个键罢了,但这位姑娘可不普通。她站起来,飞快地绕过桌子,握着尼尔森的手,展露她苗条的身段和漂亮的穿着。当尼尔森向她介绍迈克尔时,她视若无睹,嘟囔了几句,仿佛才发现他的存在;然后她又飞快地回到尼尔森身边,两人快乐地谈笑了一会,迈克尔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噢,我知道他在等你,”她最后说。“你不如直接进去好了?”
里间办公室内,一个肤色黝黑的秃顶中年男人独自站在桌前,两手按着空无一物的桌子,看来确实在等着这一刻。
“托玛斯!”他叫道。
见到尼尔森的朋友时,他比那个女孩要礼貌点——他给迈克尔拿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迈克尔谢绝了——然后他回到桌前,说:“托玛斯,现在让我们看看你这次带了什么好东西来。”
橡皮筋解开了,透着墨痕的一卷纸松开来,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轻轻卷一次,再平铺在桌上,六张水彩画摊开来等着这人的检视——又像是为了享受这个艺术世界。
“我的天啊,”那晚迈克尔说到这里时,露茜说。“那些画怎么样?能跟我说说吗?”
他对“能跟我说说吗?”这句话有点生气,但没有过多计较。“嗯,它们肯定不是抽象画,”他说。“我是说它们是具象类绘画——画上有人、动物和其他东西——但是它们不完全真实。它们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说到这里,他非常感激尼尔森在火车上提供的唯一技术信息。“他用笔墨勾画出模糊的草图,然后刷色。”
她赞同地慢慢点了下头,显得很睿智,仿佛在表扬一个小孩有如此惊人的成熟见解。
“所以,不管怎样,”他接着说,“博物馆里的家伙开始绕着桌子慢慢走起来,他说:‘好啊,托玛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如果我放走这张画,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然后他又踱了一会儿步,说:‘我也越来越喜欢这张,我能两张都要吗?’”
“尼尔森说:‘当然,艾立克;请便。’他站在那里,平静得要命,穿着那件该死的坦克手拉链夹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么,他们收这些画是为了——季节性展出,还是别的什么?”露茜说。
“我们出来走在街上后,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不,这些画是永久收藏的。’你能想得到吗?永久收藏?”迈克尔走到厨房台面处,又加了一些冰块和波旁酒。“噢,还有件事,”他对妻子说。“你知道他是在什么上面画的吗?抽屉衬里纸。”
“什么纸?”
“你知道的,人们垫在货架上,然后在上面摆放罐头食品等东西的那种纸。他说用这种纸作画有好多年了,因为它们便宜,后来他觉得‘自己很喜欢这种纸对颜料的表现力’。再告诉你吧,他在他家厨房地面上作画,他说他在厨房里放着一大块四方平整的白铁皮,是很好的台面,说是把一张浸湿的衬里纸铺在上面,就开始撅着屁股画画。”
迈克尔回家后,露茜就一直在尽力准备晚餐,但老是分心,结果猪排烧得太干,苹果酱忘了晾凉,绿豌豆煮得太软,而土豆没有烤熟。然而迈克尔一点没发现,要么压根就不在乎。吃饭时,他一只手肘支在桌上,手搭在眉毛上,盘子边上摆着第三或第四杯威士忌。
“于是我问他,”他边嚼边说。“我问他,画一幅画要花多长时间。他说‘噢,运气好的话,也就二十分钟;通常一两个小时,有时花上一天多。一个月大概我会仔细检查两次,扔掉许多画——大约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留下的就是我带到城里来的这些。现代总想第一个挑,有时候惠特尼[12]也想看看;最后剩下的我就带到画行去——你知道,就是我的画廊。’”
“他的画廊叫什么?”她问道,他又重复了一遍名称后,她又说了一遍“我的天啊”,因为那家画廊上过《纽约时报》艺术版,非常有名。
“他还告诉我——他没有吹牛;看在老天份上,这个小杂种说的全是实话——他告诉我他们至少一年为他办一次个人画展。去年他们为他办了两次。”
“嗯,有点难以——难以置信,是不是?”露茜说。
迈克尔把他的盘子推到一边——他甚至没动烤土豆——拿起他的威士忌,仿佛那是主食。“难以置信,”他说。“二十七岁。我是说,天啊,当你想到——天啊,亲爱的。”他不可思议地摇摇头。“我是说,想到化难为易,”隔了一会儿,他说,“噢,他说他很乐意改天晚上请我们过去吃饭,说会问问妻子,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真的吗?”露茜很高兴,像孩子盼着自己的生日一般。“他真的这么说了吗?”
“嗯,是的,但你知道这种事,也可能只是他一时说说而已。我是说这种事靠不住。”
“那我们给他们打电话呢?”她问。
他有点恼火,没有吭声。作为一个出生于上层阶级的姑娘,她应该有非常良好的教养才是。不过话说回来,首先百万富翁也许根本不太具备良好教养;普通老百姓怎会明白这个?
“好了,不行,宝贝,”他说,“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好。我可能在火车上再次撞上他,我们会把这事办妥的。”他又说,“听着,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当我最后到办公室时,头晕乎乎的。我知道我无法干活,所以我到布诺克那里混了一阵,我告诉他汤姆·尼尔森的事情。他听后说‘嗯,有意思,我想知道他爸爸是谁。’”
“噢,他就是这种人,对不对?”露茜说。“比尔·布诺克总是不停地说他有多讨厌讥讽他人,不管什么样的讥讽,可他真是我见过的最爱讽刺他人的家伙。”
“等等,更糟的是,我说,‘那好,比尔,首先,他爸爸是辛辛那提的一名普通药剂师,其次,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而他说‘哦,那好,行了,我想知道他拍的是谁的马屁’。”
露茜吃惊恶心太甚,腾地站了起来,双唇哆嗦着发出“啊”的一声。她站在那里,两手抱着自己,好像骨子里也在发冷。“噢,真卑鄙,”她发着抖说。“这是我听过最卑鄙无耻的话。”
“是啊,嗯,你知道布诺克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几周心情都不好。我想他跟戴安娜之间出了问题。”
“好,我一点也不奇怪,”她边说边收拾桌子。“我不懂戴安娜为什么不早点甩了他,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受得了他。”
一个周六的上午,比尔·布诺克打来电话,难得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那天下午他能不能一个人到拉齐蒙来。
“你肯定他说的是‘一个人’吗?”露茜问道。
“嗯,他有点含糊,只是一带而过,但我肯定他说了,我也肯定他用的不是‘我们’这两个字。”
“那好,结束了,”她说。“好。只是现在我们逃不掉了:他会在我们这里坐上几小时,向我们诉苦。”
结果不是这样——至少,布诺克刚来时不是这样。
“我是说,我喜欢短期的关系,”他坐在沙发上,倾身向他们解释,准备就自己来一场严肃的讨论。“我知道的,因为我过去一向如此。我似乎无法对一段关系长期保持兴趣,时间久了我会厌倦这姑娘。而我觉得腻了时,我会心烦意乱,就这么简单。我的意思是,如果长期关系对你们适合,那很好——但是,那是你们的事,对吗?”
他向他们汇报说,过去几个月来,戴安娜一直“吵着要结婚,哦,开始时是这里暗示一下,那儿暗示一下——这还容易对付——后来情况严重起来,最后我只好对她说,我说‘听着,亲爱的: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好吗?’结果她答应从我这里搬出去——跟另一个女孩找了间公寓——我们见得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也许一周最多两次。上次我们来你们这儿时就是这样了。她参加了演艺班——你们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处是这种小规模的‘技术’班,大部分是由那种想挣几个钱的过气演员办的,对吗?好,听上去像个好主意;我觉得这对她挺好。可他妈的,一两个礼拜前,她开始跟她们班上的一个家伙——一个男演员、混蛋演员——出去约会了;那家伙在堪萨斯有个有钱的老爸,他出钱让儿子到外面闯荡。三天前的晚上,我向你们发誓,这是我这辈子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带她出去吃饭,她异常冷静、咫尺天涯似的——她告诉我她跟那家伙住在一起了,说她‘爱’他,他妈的!”
“老天啊,我跌跌撞撞走回家,感觉被大卡车撞了一般,我一头栽倒在床上”——说到这儿,他往后靠回沙发,一只手抬起来遮住眼睛,悲痛欲绝的样子——“我哭得像个孩子,我停不下来,哭了几个小时。我一直说,‘我失去了她。我失去了她。’”
“嗯,”露茜说,“听上去不像是你失去了她,比尔;听上去更像是你甩了她。”
“嗯,当然,”他说,他的手臂还是遮着眼睛。“当然。这难道不是最最坏的损失?等你扔掉它后才发现它的价值?”
比尔·布诺克那天晚上住在他们家的一间空房里——“我早知道,”露茜后来说,“我知道他会在这儿过夜的”——第二天吃过午饭后才走。“你有没有发现,”等只剩他俩后,她说,“当别人说他们哭得有多伤心,哭了有多久时,你对他们的同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是的。”
“好吧,他总算走了,”她说。“可他还会再来,可以肯定还会经常来。但你知道最糟的是什么吗?最糟的是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戴安娜了。”
迈克尔觉得自己的心抽了一下。他怎么没想到这点,可从露茜说的那一刻起,他知道这是真的。
“当一对情侣分手时,他们总指望你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她接着说,“可那几乎完全是出于偶然,这难道不可笑吗?因为,如果戴安娜先给我们打电话的话——很可能——那么她就成了我们的朋友,那就很容易将比尔·布诺克从我们生活中赶走了。”
“啊,我可不担心,亲爱的,”迈克尔说。“不管怎样,也许她会给我们打电话的。她可能随时打电话来。”
“才不会。我很了解她,别指望她打电话了。”
“好吧,见鬼,我们也可以给她打电话。”
“怎么打?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噢,我想我们可以查得到,但即使那样,我觉得她听到是我们也不会太高兴。我们还是任其自然吧。”
过了一会儿,当她终于洗完午饭的餐碟后,她难过地站在厨房过道上擦干手。“噢,我曾对跟她交朋友抱有很大希望呢,”她说,“还有跟保罗·梅特兰。你不是吗?他们都是那种很——很值得结交的人。”
“迈克·达文波特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电话那头传来拘谨的微弱的声音。“我是汤姆·尼尔森。听着,不知道这个周五晚上你们有没有时间,我和妻子想请你们过来吃晚饭。”
看来,达文波特夫妇永远不缺值得结交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