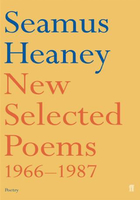小男孩骑在他想象的机车“库姆唐金特别号”上,车轮擦得很亮,令人目眩,在小小的后花园中嘎嚓嘎嚓直响。后花园散落着喂鸟的面包屑,铺着昨日的白雪,烟雾稀疏地升起,像寒冷午后的气流那样轻淡。小男孩在晒衣绳下面枭叫着,踢着洗衣房停车站旁边的那个狗餐盘。机车活塞越转越慢,喷烟的间隔越来越大,而女仆把竹竿放低,将摆荡的汗衫取下来,露出腋窝的污渍,头伸到墙上方喊道:“艾蒂丝,艾蒂丝,来这儿,我需要你。”
艾蒂丝爬到院墙另一边的两个洗衣盆上面,回应道:“派翠西亚,我在这儿。”她的脑袋在破玻璃上方晃动。
男孩把“飞行的威尔士人号”从洗衣房倒退至敞开的煤库大门,用力扯着他幻想中的刹车——口袋里的一支槌子。穿制服的助手们拿着燃料跑出来。男孩跟一位敬礼的消防人员讲话,机车沿着那些阻挡猫儿、装有倒刺的中国城墙拖拽而行,抵达藏污纳垢的结冻河流,在煤库隧道进进出出。他置身在尖叫声和汽笛声中,却一直仔细听着派翠西亚和隔壁刘易斯夫人家的仆人谈话。两位女仆丢开工作,在谈天闲扯,称呼男孩的母亲为T夫人,言语间对于刘易斯夫人也很无礼。
他听到派翠西亚说:“T夫人要到六点才回来。”
隔壁的艾蒂丝回答:“老L夫人到尼兹去找罗伯特先生了。”
“他又在闹事。”派翠西亚低声说。
“闹事,喧闹,吵闹!”男孩在煤库里嚷嚷。
“你把脸弄脏了,我会宰了你。”派翠西亚心不在焉地说。
他爬上煤堆时,派翠西亚并未试图阻止他。他安静地站在顶端,像“煤堡之王”,头碰屋顶,倾听两个女仆忧心忡忡的声音。派翠西亚几乎是在流泪,艾蒂丝则在啜泣,站在不稳的洗衣盆上摇摇晃晃。“我站在煤堆顶端。”男孩说,等着派翠西亚生气。
派翠西亚说:“我不想看到他,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我们必须、必须一起去,”艾蒂丝说,“我必须弄清楚情况。”
“我不想弄清楚。”
“派翠西亚,我受不了,你必须跟我去。”
“你自己一个人去,他在等你。”
“拜托,派翠西亚!”
“我俯卧在煤块上了!”男孩说。
“不,这是你跟他的日子。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想让自己认为他爱我而已。”
“哦,别胡说,派翠西亚,拜托!你来还是不来?我必须听听他怎么说。”
“好吧,半小时后,我会在墙头喊一声。”
“你最好快来!”男孩说,“我脏得吓掉耶稣的下巴。”
派翠西亚跑到煤库。“乱说话!立刻从那儿下来!”她说。
洗衣盆开始滑动,艾蒂丝不见了。
“你不许再那样胡说八道。哦!你的衣服!”派翠西亚把男孩带进屋内。
她让他当着她的面换衣服。“否则不准讲话。”他脱掉裤子,在她四周跳舞,叫道:“派翠西亚,瞧我!”
“守规矩点儿,”她说,“否则不带你去公园。”
“那么,我们是要去公园吗?”
“没错,我们要去公园。你、我和艾蒂丝。”
他把衣服整整齐齐地穿好,不去惹恼她,在手上吐口唾沫,梳开头发。她似乎没注意他居然一声不吭,衣服也穿得颇齐整。她两只大手握在一起,凝视胸前的白色胸针。她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姑娘,手很笨,指头像脚趾,肩膀像男人一样宽。
“你满意吗?”男孩问。
“这单词挺长,”她说,满含爱意地看着他,把他抱起来,搁在矮柜顶端,“现在你跟我一样高了。”
“但没有你大。”他说。
他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下午:雪可能下得很足,可以用盆子滑雪;叔叔们可能从美国远道而来,带来手枪和圣伯纳狗,尽管他其实没有叔叔在那儿;费古逊的商店可能失火,东西一包包地全掉落在铺道上。当派翠西亚把沉重、留着黑色直头发的脑袋靠在他肩膀上,对着他的衣领低语“阿诺,阿诺·马修斯”,他并不惊奇。
“好了,好了。”他说,用指头摩挲她头发分叉的地方,在她后面冲镜子眨眼,看着她背后的衣服。
“你在哭吗?”
“没有。”
“有,我可以感觉到湿湿的。”
她用袖子擦干眼睛。“不要告诉别人说我在哭。”
“我要告诉每个人,我要告诉T夫人和L夫人,我要告诉警察、艾蒂丝、我爸爸、查普曼先生,告诉他们说,派翠西亚像母羊一样趴在我肩上哭,哭了两小时,眼泪足够装满一个水壶。其实我不会这样做。”他说。
他、派翠西亚和艾蒂丝刚往公园走,天上就开始下雪。硕大的雪花意外落在多石的小山上。虽然才下午三点钟,天空已暗得像黄昏。房子后面的菜园里,另一个男孩在最初的雪花飘落时大喊大叫。欧奇·伊凡斯夫人打开“春草地”顶端的凸窗,探出头,伸出手,好像要凌空抓住雪花。男孩乖乖等着派翠西亚说:“快,赶紧回去,下雪了!”他等着派翠西亚阻止他前进,以免踩湿鞋袜。他在小山顶上猜想,派翠西亚说不定没看到雪,哪怕雪下得很大,打在她脸上,盖住她的黑帽子。他们转过街角,走上通往公园的道路,但他不敢说话,唯恐惊醒她。他落在后面,脱下帽子,用嘴接雪。
“戴上帽子,”派翠西亚说,转过身,“你想感冒死掉吗?”
她把他的围巾塞进他外衣里面,然后对艾蒂丝说:“你认为,下雪了他还会在那儿吗?他一定会在那儿,不是吗?我星期三去时,他总是在那儿,无论晴天雨天。”她鼻尖红红的,两颊像煤炭一样发光,在雪中看上去比在夏天更美。夏天时,她头发垂在湿漉漉的前额上,背后一大片热气不停扩散。
“他会去的,”艾蒂丝说,“有一个星期五,雪下得很大,他还是在那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去,他总是在那儿,可怜的阿诺!”她穿着一件装饰着皮毛的外衣,看起来白白净净,身体比派翠西亚矮半截,走过厚厚的雪,好像要去购物。
“奇妙的事情永不会停止。”男孩自言自语。派翠西亚牵着他在雪中迈进,他跟两个姑娘在暴风雪里大步行走。他在马路上坐下来。“我在雪撬上,”他说,“派翠西亚,拉我吧,像爱斯基摩人一样拉我吧。”
“你这个无赖,站起来,否则带你回家。”
他看出她并不当真。“可爱的派翠西亚,美丽的派翠西亚,”他说,“拉我,我用屁股滑行。”
“再说脏话,你知道我会告诉谁。”
“告诉阿诺·马修斯。”他说。
派翠西亚和艾蒂丝走得更加靠近。
“他什么东西都会注意到。”派翠西亚低语。
艾蒂丝说:“没搞到你这份工作我真高兴。”
“哦,”派翠西亚说,抓住男孩的手,压在自己的手臂上,“用他来换这个世界,我也不干!”
男孩跑上沙砾小径,抵达公园的远端走道。“我被宠坏了!”他喊道,“我被宠坏了!派翠西亚把我宠坏了!”
不久,公园到处都会是白雪,蓄水池和喷泉四周的树木已经一片模糊,金雀花小山上的训练学院隐藏在一片朦胧之中。派翠西亚和艾蒂丝走上很陡的小路,往遮棚前进。在禁止践踏的草地上,男孩紧随其后,又快速滑过她们身边,直接冲入裸露的树丛,撞击和尖刺促使他大叫,但他没有受伤。此时,两个女孩忧伤地交谈着。她们在荒凉的遮棚里抖衣服,雪散落在长椅上。她们坐下来,仍然靠得很近,座位在保龄球俱乐部的窗子外面。
“我们刚好赶上,”艾蒂丝说,“下雪很难准时。”
“我可以在这儿玩吗?”
派翠西亚点头。“要安安静静地玩,不要玩雪。”
“雪!雪!雪!”他说,从阴沟里掏雪,捏成一个小球。
“也许他已经找到工作。”派翠西亚说。
“阿诺没有找到。”
“如果他没有来呢?”
“派翠西亚,他一定会来,别那么说。”
“你带信来了?”
“在我包包里。你收到几封?”
“没有。艾蒂丝,你收到几封?”
“我没数过。”
“让我看一封。”派翠西亚说。
男孩此时习惯她们的谈话了。她们很大,很蠢,坐在空荡荡的遮棚里,无缘无故啜泣着。派翠西亚在读一封信,嘴唇动着。
“他总这样告诉我,”她说,“说我是他的星星。”
“他用‘亲爱的心’开头吗?”
“总是‘亲爱的心’。”
艾蒂丝实实在在地大声哭出来了。男孩手里握着一个雪球,看她在座位上摇晃身体,脸孔藏在派翠西亚沾雪的外衣上。
派翠西亚轻拍艾蒂丝,安抚她,摇摇头说:“他来的时候,我要好好骂他一顿!”
谁来的时候?男孩把雪球抛进无声无息的降雪之中。在沉寂的公园里,艾蒂丝的哭声显得清晰、细弱,一如口哨。男孩想要否认他与这两个温柔姑娘的关系,于是他站在离她们一段距离的地方,唯恐一个陌生人,一个穿着长筒靴的男人或一个来自“高地”、面露嘲笑神情的高年级男孩经过。他把雪堆在网球场的电线上,把手伸进雪中,像做面包的师傅。他把雪塑成面包状,轻声说:“各位女士先生,这就是做面包的方法。”艾蒂丝抬起头,说道:“派翠西亚,答应我,不要生他的气。我们要很沉静又很友善。”
“写给我们两人都用‘亲爱的心’,”派翠西亚生气地说,“他曾经脱下你的鞋子、拉你的脚趾以及——”
“不,不,你不能这样,不要说下去了,你不能说这种话!”艾蒂丝把指头放在颊上,“没错,他这样做过。”她说。
“有人一直在拉艾蒂丝的脚趾,”男孩自言自语,在遮棚的另一侧又跑又笑,“艾蒂丝去市场。”他哈哈大笑,停下来,因为他瞧见一个没穿外套的年轻人在角落坐下来,双手捧在一起呵气。这个年轻人戴着白色厚手套和一顶格子帽,看到男孩时,把帽舌拉到眼睛上方。他的手呈淡蓝色,指尖泛黄。
男孩跑回派翠西亚身边。“派翠西亚,那边有个人!”他喊道。
“哪儿?”
“遮棚的另一边;他没有穿外衣,这样吹着手。”
艾蒂丝跳起来。“是阿诺!”
“阿诺·马修斯,阿诺·马修斯,我们知道你在那儿!”派翠西亚在遮棚附近呼喊。过了一阵,这个年轻人脱下帽子,微笑着,在角落出现,靠在一根木柱上。
他光滑的蓝色裤子底部很宽大,肩膀很高、很硬,两端形成尖形,尖头的皮鞋闪亮亮,胸前的衣袋塞着一条红手帕。他并没有站在雪里。
“你们两人竟然认识。”他大声说,面对两个眼睛发红的姑娘,以及张着嘴、一动不动的小男孩。男孩站在派翠西亚身边,裤袋内满是雪球。
派翠西亚甩了甩头,帽子在一只眼睛上方歪着。她把帽子戴正后,以洗衣服时的声音说:“阿诺·马修斯,来这儿坐下,你要回答一些问题!”
艾蒂丝抓住女友的手臂:“哦!派翠西亚,你答应过的。”她扯着手帕的边缘,一滴眼泪滚下脸颊。
阿诺轻声说:“先让小男孩去玩吧。”
男孩到遮棚外走了一圈,回来时听见艾蒂丝说:“阿诺,你手肘上有一个洞,”也看到年轻人踢着脚旁的积雪,注视着刻在姑娘脑后那面墙上的名字和心形。
“你星期三都跟谁出去?”派翠西亚问,笨拙的手把艾蒂丝的信紧抓在靠近胸部的装饰皱褶上。
“你,派翠西亚。”
“星期五你都跟谁出去?”
“派翠西亚,是跟艾蒂丝。”
他对男孩说:“来,孩子,你能做出跟足球一样大的雪球吗?”
“能,像两个足球那么大。”
阿诺转向艾蒂丝,说道:“你怎么认识派翠西亚·戴维斯的?你在布尔米尔工作。”
“我刚开始在库姆唐金工作,”她说,“之后我没有见到你,所以无法告诉你。本来今天要告诉你,却发现了这件事。阿诺,你怎么能这样?在我休假的下午与我见面,在星期三与派翠西亚见面。”
雪球已变成一个矮雪人,肮脏的脑袋歪向一边,脸上满是树枝,戴着男孩的帽子,抽着一根铅笔当烟。
“我没有要伤害你们的意思,”阿诺说,“你们两个我都爱。”
艾蒂丝尖叫一声。男孩跳向前,背部断裂的雪人崩塌了。
“你不要说谎,你怎么可能两个都爱?”艾蒂丝喊道,对着阿诺挥动手提包。它忽然打开,一束信掉在雪上。
“你敢捡起那些信!”派翠西亚说。
阿诺没动。男孩在塌陷的雪人中寻找他的铅笔。
“阿诺,你要在此时此地选定一个人。”
“她或者我。”艾蒂丝说。
派翠西亚冲他背过身去。艾蒂丝拿着打开的手提包,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大雪掀开了一封信的第一页。
“你们两个,”他说,“都动气了。坐下来谈谈吧。艾蒂丝,不要哭成这样。数以百计的男人不只爱一个女人,你会经常读到这方面的事情。艾蒂丝,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姑娘。”
派翠西亚看着墙壁上的心、箭以及古老的名字。艾蒂丝看到信卷起来。
“我选择你,派翠西亚。”阿诺说。
派翠西亚仍然站在远离他的地方。艾蒂丝扯开喉咙大哭,他则把一根指头放在嘴唇上,做出“嘘”的样子,但声音太小,派翠西亚听不到。男孩看到他安慰艾蒂丝,对她千承百诺,但她又一次尖叫,奔出遮棚,踏上小径,手提包在身体一侧碰来碰去。
“派翠西亚,”他说,“转过来看着我,我必须说明白,我选择你,派翠西亚。”
男孩朝雪人弯下身,找到了穿过它头部的铅笔。他站起来时,看到派翠西亚和阿诺手挽着手。
融雪渗出他口袋,雪在他鞋里化掉,雪渗进他衣领,透入马甲。“瞧你,”派翠西亚匆忙跑到男孩身边,抓住他的手,“你全身都湿透了。”
“只是一小片雪。”阿诺说,遮棚里突然只剩下他一个人。
“确实是一小片雪,他冷得像冰,脚像海绵。立刻回家!”
他们三个人爬上通往高处走道的小径,派翠西亚的脚印像越来越厚的积雪中的马蹄印那样大。
“快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子,有白屋顶!”
“亲爱的,我们一会儿就能到那儿。”
“我宁愿待在外头,做一个像阿诺·马修斯的雪人。”
“嘘!嘘!你母亲会等你。必须回家。”
“不,母亲不会。她已经跟罗伯特先生去闹事了。闹事、喧闹、吵闹!”
“你很清楚,她是跟派崔吉夫人去买东西,你可不能扯这么坏的谎话。”
“嗯,阿诺·马修斯扯谎。他说他爱你胜过艾蒂丝,但他背着你,跟她说悄悄话。”
派翠西亚停止走动。“你不爱艾蒂丝吗?”
“不爱,我爱你,爱的是你。我完全不爱艾蒂丝,”他说,“哦,天啊,今天太糟糕了!你不相信?我爱的是你派翠西亚。艾蒂丝不算什么。我只是习惯同她见面;我经常待在公园里。”
“但你告诉她说,你爱她。”
男孩困惑地站在他们之间。派翠西亚为何那么生气,那么严肃?她脸孔泛红,眼睛闪亮,胸膛起伏。从她长袜的一个洞能看到她腿上的黑长毛。她的腿像我的腰那么粗,他想。我很冷;我想喝热茶;我的钮扣上面盖有雪。
阿诺在小径上慢慢往后退。“我必须那样告诉她,否则她不会离开。派翠西亚,我必须这样做。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恨她。我发誓。”
“砰!砰!”男孩喊道。
派翠西亚在打阿诺,拉扯他的手套,用手肘敲击他。她用拳头把他击倒在小径上,使劲叫嚷:“让你对艾蒂丝说谎!你这只猪!你这个坏蛋!让你伤她的心!”
他蹒跚撤步,遮住脸,抵挡她的拳头。“派翠西亚,派翠西亚,不要打我!有人在!”
阿诺倒下时,大雪纷飞,有两个撑伞的女人在树丛后面窥视。
派翠西亚高高在上。“你对她说谎,也对我说谎,”她说,“阿诺·马修斯,站起来!”
阿诺爬起来,戴好手套,用红色手帕擦擦眼睛,举起帽子,走向遮棚。
“至于你们,”派翠西亚说,转向窥视的妇人,“你们应该感到害臊!两个老女人在雪地里胡闹。”
两个女人躲进树丛后面。
派翠西亚和男孩手牵着手往上爬,回到高处的人行道。
“我把帽子留在雪人旁边,”男孩记起来,“是我那顶有托特汉姆徽章的帽子。”
“快跑回去,”她说,“反正你没法更湿了。”
他发现了藏在雪人下面的帽子。阿诺坐在遮棚的一个角落里,读着艾蒂丝掉落的信件,慢慢翻着潮湿的纸页。他没有看到男孩,站在一根柱子后面的男孩并没有打断他。阿诺仔细地读每一封信。
“你找帽子花了很长时间,”派翠西亚说,“你看到那个年轻人了吗?”
“没有,”他说,“他走了。”
回到家里温暖的起居室,派翠西亚又要男孩换衣服。他双手伸在火前面,不久便感觉到两手很痛。
“我的手着火了,”他告诉她,“还有我的脚趾,还有我的脸。”
她安慰了男孩一番,说:“嗯,这样好一点儿了。疼痛飞走了。你不会马上又哭爹喊娘了。”她在房间四处忙碌,“我们今天全都好好哭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