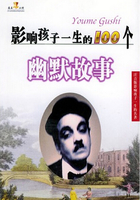我提着万分的紧张,死死的盯着对我走来的好大一群人,他们离我似乎越来越近,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都顶着一顶白帽。我不敢移动我的视线,甚至连眼都不敢眨一下。又过了大概两分钟,对着我走来的那一大群人我看的更加清楚,我依稀的能分辨出来。可就当我看清楚后差点没吓得我失声大叫出来。因为我居然看见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没有任何声响的朝着我走了过来,为首的人双手捧着个什么东西。我不敢在继续看下去,于是我想回铺子里,就在我想躲开这群朝着我走来的人时,我的腿就像在地上长了根似的动也动不了。
可那群人离我越来越来,我直接都不敢再去看,于是我想闭上眼睛,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闭上眼睛后我依然还是可以看看街道上的场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撞了邪了,反而我稍微镇定了点,我便强忍着看着那群对我走来的人,他们离我几乎只有百十来米了。这时我才真正的看清楚为首人双手捧着什么。
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张遗照,遗照放在一个盒子上面,不过距离还是有一些远我分辨不清照片上人得长相,但没过一会我便差点吓到坐在原地。大概那群奇怪的人走到离我还有五六米距离的时候,我看清了遗照上的面孔,这人居然是我爷爷!而且遗照下的那个盒子就是在火车上做梦梦见的那个从我爷坟前挖出来的那个盒子。见到这我不由的吓得失声大叫了起来,可就在我吓得叫出来以后,正要从我身前街道走过的那群披麻戴孝的人居然毫无生气的停在了原地,他们的头都缓缓的朝着我看来。见到这一幕我已经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差点没尿了出来,我看见那群人居然根本就不是什么活人,全都一脸死灰,乌黑的嘴唇。这分明就是一群死人。他们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只感觉我背后的冷汗直冒,身上的短袖早就被汗水渗透。我试着转腰扭头避开他们的眼睛,我这一扭头闭眼只感觉后背发凉,这群东西不会是靠过来了吧!
就在我被吓得即将又大叫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叫我,我非常恐惧的慢慢睁开眼,然而奇怪的是非常刺眼,我根本没在什么店门口而是躺在床上,一睁眼就被窗外射进屋的太阳晃得睁不开。我下意识才知道我居然做了个噩梦,而且居然又有那个盒子,这不由的让我感觉有些纳闷儿。
见我似乎被吓懵了,我爹就问我:“你干啥,睡觉不好好睡,一惊一乍的。”
然后他就没在理我回了自己的房间继续睡觉,我脑子有点乱就起床穿鞋准备出去洗漱,而刚把鞋穿好手机就响了,我拿起手机一看,只见是杨大蛮,他问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我就给他说没事,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回复了他的消息,我就洗漱了一番,然后走到了铺面的大门外,而这时基本街两边的门面都运作了起来,到处都是木工机器切割木头的声音。还好不想梦里那样,虽然这条街晚上挺吓人,但白天还是别有一番风景的。
胖哥和另外两伙计正在搬运木头,见我走了出来就递给我两袋包子,说给我爹也拿一袋。我一边啃着包子一边朝我老爹卧室走去,他房间挺乱的,到处都是工具机器以及很厚的灰尘,我真想不通他怎么带下去的,臭脚丫子味和浓烈的烟酒混合到一起差点没把我眼泪给我感动出来。于是我用手挡着鼻子,憋着一口气,我真怕用嘴呼吸他房间里的味道,这不就跟用嘴吃屎是一个道理。我把包子丢在他面前,然后给他说了一声就急忙跑出房间,我是真憋不住气,太熏眼了。我没理会他会不会吃,估计他昨晚又喝多了吧。
我来到门口,和胖哥几个人吹了会儿牛,之后我的朋友大蛮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反正也没啥事,去找他玩玩打发一下时间。于是我对着他家走去,他家离我家没多远,走了五六分钟就到了,他家挺热闹的,他爸一共四兄妹,哪像我家都是独苗,也不知道我父亲和我爷年轻的时候孤不孤独,反正我是感觉挺孤独的。
我来到他家门口,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精瘦精瘦的,正拿着一把扫帚扫着地,我认识他,他就是大蛮的大伯。我上前和他大伯打了个招呼:“杨大伯,扫地呢?”
他回头看着我,有些惊讶就说道:“哦,郑郝。你也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说我和大蛮一起回来的,大蛮上哪去了。他大伯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就给我说在屋里呢,让我去叫他。我给他大伯打了根烟就钻到了杨大蛮的房间里,而这狗东西还在床上四仰八叉的躺着。他见我来了,露出很傻缺的笑容,我不知道他笑什么,就问他:“笑什么啊?有啥好笑的。”
只见他摇了摇头,然后一副极度猥琐的样子,点了根烟吸了一口才缓缓说道:“呃哈哈哈,我泡到了一个妹子,就是你家旁边那技校里的学生。她还约我待会下午出去玩,你这种单身狗怎么能理解你蛮哥的心情。”
我看他一脸的骚包样,就不耐烦的干笑了一声:“呵!我估计待会人家看到了这幅尊容估计躲都躲不赢。”
不是我故意调侃他,而是他的形象实在令人不敢言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那个精神病院里没关住的杀马特。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长得要命,两手都是纹的一些流里流气的纹身,咋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听我这么一说,居然还起床去一旁衣柜的镜子旁照了起来,我以为他会发现自己挺陋,没想到他居然还自我陶醉起来,而且一边陶醉还一边自夸道:“嗯!不错!发型挺时尚,纹身挺有个性。就是我这一身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