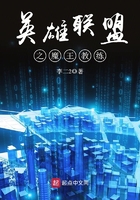施蛰存先生有首诗,谈到一段如烟往事,四十二年后两位男女主角再度相逢,虽已是头发斑白,但仍是情不能自已。诗云:
儿女赓词旧有缘,至今橐笔藉余妍。
碧城长恨蓬山隔,头白相逢亦惘然。
一九六四年间施蛰存在读了陈小翠的《翠楼吟草》后写了十首绝句,又殿以赠陈小翠的书怀二绝,这是其中的一首。话说一九六四年元月,当施蛰存从好友郑逸梅处得知了陈小翠的住址之后,即于同月二十日到陈小翠家中登门拜访,施蛰存在《闲寂日记》中写道:“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三天后的日记又云:“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寄赠陈小翠。此十二诗甚自赏,谓不让钱牧斋赠王玉映十绝句也。”可见这诗还是他的得意之作,因为它里面还蕴藏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后来施蛰存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北山谈艺录》内中有一篇《交芦归梦图记》,谈到他与陈小翠这一段“并不如烟”的往事,云:“余少时尝与吾杭诗人陈媛小翠有赓咏联吟之雅,相知而未相见也,逾四十年,岁甲辰(1964),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大雪,始得登元龙之楼,披道韫之帷,晤言一室。”这也就是他诗中所说“儿女赓词旧有缘”一事。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施蛰存就编有《翠楼诗梦录》,在集子中施蛰存述及这段往事,只可惜这集子一直未出版,故甚少人知。
施蛰存在年少时曾以“施青萍”或“青萍”的笔名,在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中发表文章,据黄转陶《卡党小传》文中说施蛰存曾译《生育女子须知》载于浙江民报《妇女周刊》中,另外还有小说《寂寞的街》刊登于《星期》杂志、小说《伯叔之间》刊登于《半月》杂志、小说《红禅记》刊登于《兰友》杂志,除此而外,他也写过不少旧诗词。他说施蛰存“撰稿好用钢笔,字迹细匀,不稍参差,墨水喜紫罗兰色。有瘦鹃风也”。
一九二一年九月,周瘦鹃在上海创办《半月》杂志(共出4卷96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曾邀请当时以月份牌美人画而名噪一时的谢之光绘制每期的封面。谢之光所绘仕女图,其画笔法采中西之长,别具一格。当年施蛰存被这些封面所吸引,于是从第一期至第十五期,逐一以词题之,十五帧封面用十五个词牌,如《一斛珠》《蝶恋花》《行香子》《醉花阴》《巫山一段云》《喝火令》《极相思》《忆萝月》《好女儿》《步蟾宫》《锦帐春》《罗敷媚》《减字木兰花》《醉太平》和《步虚调》填词而咏之。施蛰存说这十五阕词寄给周瘦鹃后,却一直杳无消息。其实周瘦鹃在收到词稿后马上找到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之女陈小翠,以《洞仙歌》《卖花声》《浣溪沙》《一搦花》《如梦令》《菩萨蛮》《鹧鸪天》等词牌和之,写了九阕词,分别配以第十六期至第二十四期之封面。这“珠联璧合”的二十四阕词,后来在一九二二年的第二卷第一号(即第二十五期)以《〈半月〉儿女词》刊出,当时施蛰存年仅十七岁,而陈小翠也近双十年华,称得上是青春“儿女词”。
施蛰存有位表叔沈晓孙当时在陈蝶仙创办的“家庭工业社”中任职,而陈小翠也在该社中兼任配料员之职。沈晓孙也读过《〈半月〉儿女词》,觉得这对小儿女颇有“文字因缘”,遂向老板陈蝶仙提亲,期望促成施、陈两人的姻缘。陈蝶仙对施蛰存的才华颇为欣赏,但女儿更是他至为钟爱的,故提出要施蛰存亲自登门拜访,或许他想要进一步再考察施蛰存的人品和学识。沈晓孙于是带上陈小翠的照片回松江见过施蛰存的父母。施父随即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施蛰存商说小翠之事。可惜施蛰存听罢此事,即以“自愧寒素,何敢仰托高门”为由,婉谢了这门婚事。原本一对“绝配”的才子、才女,就此错过了一段人世姻缘。
郑逸梅谈及小翠的婚姻时说,最初南汇顾佛影追求她,佛影诗神似渔洋,和小翠很合得来,可是佛影一介书生,门第上是有差异的,终未能成佳偶。结果由父母之命,小翠嫁给了在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的孙子汤彦耆。怎奈婚后两人意趣不相投,没多久,夫妇分食,后竟分居,但并没有离婚。后来汤彦耆于鼎革之际渡海去台,陈小翠在一九五四年写的《咏汤氏园白藤花》一律,有“东风吹冷黄縢酒,翠羽明珠漫寂寥”之句,用陆游赠其前妻唐琬《钗头凤》词中语,言破镜已难重圆;此生只有寂寥独守了。
学者刘梦芙指出,陈小翠与汤彦耆分居时,正当盛年,才情艳发,诗画兼工;处杭州、上海金粉繁华之地,乃父事业兴旺,家境殷实,按今人观念,完全可以再觅一知音伴侣。但小翠却恪守“烈女不事二夫”的古训,忠于盟约,谢绝友人的追求,独立谋生,这正是贞介人格的表现。到一九四六年秋,顾佛影返回上海,与小翠相见,重叙旧情。大概佛影流露了结为伉俪之意,但小翠却以诗明志:“梁鸿自有山中侣,珍重明珠莫再投”,她表明两人只能做好朋友,不能进一步发展关系。因此一九五五年顾佛影病重自知不起时,乃将小翠所写书、函、诗、词,亲付一炬,谓不愿小翠负此不好声名,这是对小翠的尊重和爱护。也因此在《翠楼吟草》只仅存几首她和顾氏唱和的诗词,其中有《南仙吕·寄答佛影学兄》一词,记述两人相识、相别又相逢,哀婉凄怨,令人不忍卒读。
历经四十二年,施蛰存、陈小翠两人才首次见面,当年曾是小儿女,如今都两鬓斑霜。陈小翠在后来为施蛰存写的《题画》一诗中,有句云:“少年才梦满东南,卅载沧桑驹过隙。”真是感慨万千。尤其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里,他们以诗词书画进行心灵的交流,感受到了那种人世间少有的真挚情义。只是好景不长,他们只再续了一段为时四年半左右的“文字因缘”。“文化大革命”祸起,小翠因兄陈定山在台湾、女汤翠雏在巴黎的亲属关系,饱受凌辱。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陈小翠甫及上海中国画院之门,即望见诸画师均罗列成行,为阶下囚,小翠反身逃回其寓,却被发觉,红小将追踵而来,小翠坚闭其门不纳,一时叩门如擂鼓,势将破门而入。小翠没有办法,乃引煤气自尽,终年六十七岁。
当有研究生问起陈小翠时,施蛰存爽直地说:“她是才女啊!能诗能画,才艺双全,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死得惨。”而二〇〇〇年五月,沈建中为施蛰存编《云间语小录》时,用心良苦,将陈小翠的一幅“落叶荒村急”作为封面,并故意问施老:“把您二人的名字排在一起,有何感想?”施蛰存说:“她要是还活着,不得骂死我啊!”脸上却笑成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