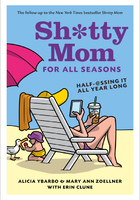孔吉眼见那人要动手,索性系好裹钱的衣衫,在腰里缠绕住,叫道:“不知者无罪,求老爷放我一次,下次改过。”那瘦子骂道:“你这小贼,追上你才求饶,我今日打死你解气。”另两个人也追上来,气喘吁吁喝道:“打死你个坏种,都和你一样,也没有王法。”那瘦子伸手就一巴掌,只要打的他脸,孔吉眼尖,后退几步,却抽个空,瘦子大怒一时便呼呼抡起拳头,他自恃手快身子轻灵。只要迅速拿住这孩子,两人斗几回合,瘦子屡击不中,这一次眼见一拳打到孩子的肩膀正沾沾自喜,却又被他伸出双手竭全力格开,那瘦子焦躁起来,却无可奈何,一时围观者也多起来,诸人皆不平,有一个认得瘦子的便叫道:“侯兄弟,快住手吧!怎么打一个小孩儿呢?”那瘦子叫山猴,听见人叫他只得罢手,脸皮涨红,却无语解释。同来的另两人忙道:“我们这是秉公办事呢!”那两人一个绰号叫“扒皮”,一个叫“扒骨”。
山猴说:“
你把钱留下,就可以走”孔吉气愤道:“哼,你只做梦呢!”那三人互相诡异的一望,心有灵犀。扒皮却柔声对孔吉说:“我们可以放过你,你自己对我们的头儿说吧”说着抬左手一指,孔吉慌忙一看,三人一拥而上,一个人抓手一个人抓肩一个人抓住他的前襟,山猴狰狞笑道:“我要一下打扁你”他们三人一齐哈哈大笑。
倏地,便有一个孩子拨开围观众人站出来骂道:“三个畜牲不如的东西。”那孩子圆脸大眼,穿一件长长的旧灰衫,鞋也破得露出脚指。扒骨先松开孔吉的手,恨不得一口吞下那孩子,人群哗的裂开一道口子,扒骨气势汹汹的走来,他本身体高大相貌丑陋,生起气来额头的青筋已暴出,像几条蚯蚓扭扭曲曲盘踞其上,十分得吓人,那孩子见他走近,朝他啐一口,稚声细气的说:“坏家伙
以为我怕你吗?”扒骨挥拳打去,他
力气颇大,一拳挥去风起,离得近的人衣衫摆拂,只急忙的后退,一面惊恐的闭上眼睛不忍直视,心里暗暗替着那孩子担忧。忽然“哎呦”痛苦的呻吟声传来,却是扒皮和山猴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痛苦的打着滚儿,孔吉兀自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他本来无心伤人,迫不得已才反击,那是两年前他见
云香练过的一套掌法,他看一遍便默默的记在心里,第一次练时便让爹狠狠揍了一顿,爹说:“谁教你的,也太阴毒啦?天下居然还有这种人呢!”爹当然知道那人是谁。孔吉
当初看着那套掌法软绵花俏很好玩儿,也就记忆深刻。不想才被山猴用铁钳似的手用力捏着他的肩胛骨时,他一下死命挣脱,也就随意使出一招,当他发现他们俯下头来,他要打着他们的眼睛时,他忙收力,但他已经打中了,那两个人一手捂眼,各一拳打来。就在扒皮打中他胸口后,他霎时间打中他们咽喉,小腹八次。两个不可一世的税差缓慢而痛苦的倒下,每一次他们总痛殴别人,他们也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怜的人,但这一次,该到他们尝食恶果了。
扒骨以为他可以一拳击飞那孩子,却发现那孩子正对他吐出舌头
,而且站在他面前毫无俱色,“小混蛋,我要打死你。”他喊道,他扑过来,一拳又未打中,他追着孩子奔跑起来,围观的人惊讶的发现他们跑一会儿歇一会儿,两个人仿佛在做游戏,那孩子行走起来足不沾地,如驾风一般。似乎还只是玩耍,孔吉也看得呆了,只见扒骨苍苍浪浪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儿,哦,他再也不想去追赶那孩子了。
人丛里一个粗壮的青年看到扒骨狼狈的坐在地上,暗暗的想:“早知道我上一次也跑掉啊!”一面为自己的想法大胆而感到得意,正摇头露出笑容,只见扒骨站起来,眼睛射出凶光斜睨着他,一时吓得魂飞魄散,再也迈不动步了。
“喂,快走啊!”孔吉一时被身旁边的人推了推,大家都正在开始离去,孔吉看到那个小男孩朝自己走了过来:“我们走吧”他说,“谢谢你啊!”孔吉说:“我们做个好朋友行吗?”“我叫阿丙,我八岁。”“我们做个真正的朋友,不,还是兄弟吧!就像三国时的张飞和关羽他们一样”
阿丙欢喜的大叫:我才来这里三天,便有了哥哥。“你知道我才来几天吗,也就五天啊!”两个孩子都很惊讶彼此怎么偶遇的呢?又恰好认识呢!阿丙说:“我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就见他们三人也从那么远的市场里将一个老头儿追到此地,那老头儿就因为早晨少一吊儿钱打算午后便还给他们,拿着钱他们还追着他打骂,在你和他们打斗的地方,他们把他按在地上打,实在叫人气愤的慌。”孔吉听了由不得咬牙切齿说:“早知道我才打得他们轻了,该打死他们。”阿丙叹了口气又说:“
也教训他们一下才好,不过我确实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只能打他们每人一拳一掌便逃,他们自是追不上我,好几次我差点让他们捉到,我挑起他们的火来,他们疯狂的追我,直绕城跑一圈儿。我走得极快,待引着他们远了,回来一看,老者还躺在地上,眼里满满凄苦之色,只是不能走,鲜红的血从额头淌下把满是灰土的脸和衣服都染红了,我勉强扶起他,把他送回家去”
这时,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走上一条狭窄
的长巷,两排矮小的房屋破旧不堪,三个两三岁穿红花衣的小孩子正在玩耍
,一只秃尾巴的褪尽白毛的老狗在
路上不停煽动鼻子嗅着,但除了垃圾,也只有石板铺的街面石头缝里顽强不息生
长出来的野草。一个满脸褶纹的老妇人坐在一张磨得光亮四条腿却微黑的板登上,在房檐下大门旁坐着,目光忧郁的望着对面的一户人家,大门虽然敞开但空无一人,
地面凹凸不平。
孔吉见所有房子门窗十分狭小,屋内又黑漆漆的,形容不出的老旧,心里只觉得沉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