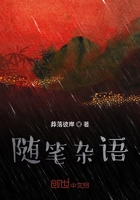下卷
我晚上到了亚摩斯,就奔到旅店。我知道,即使那位伟大的来客,那位在他面前一切有生之物都要俯首听命的来客,还没光临这一家,坡勾提家那个空屋子——我的屋子——十有八九也很快就要有人住的,因此我才在旅店落脚,在那儿吃了饭,定好了床位。
我离开旅店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许多铺子都已经关门上板了,镇上一片冷清沉寂了。我来到欧摩与周阑商店的时候,只见百叶窗已经关了,但是店门还敞着。我能看到铺子里面欧摩先生全身的轮廓,靠在起坐间的门那儿抽烟,我就进了铺子,向他问好。
“哟,哎哟哟!”欧摩先生说,“你好哇?请坐,请坐——我希望抽烟不碍的吧。”
“一点也不碍的,”我说。“我还喜欢闻烟的味儿哪——可得是在别人的烟斗里。”
“啊!在自己的烟斗里可不喜欢,对吗?”欧摩大笑了一声,答道。“那样更好,先生。年纪轻轻的就染上了抽烟的嗜好,可并不是好习惯。请坐吧。我抽烟是为了治我的哮喘。”
欧摩先生给我腾出地方来,为我安了一把椅子。他现在又落了座,喘作一团,叼着个烟斗直倒气,好像烟斗就是那种必需之物的来源地,他没有它就非一命呜呼不可。
“我听到巴奇斯先生病重的消息很难过。”我说。
欧摩先生只不动声色地瞧着我,同时直摇脑袋。
“你知道他今个晚上怎么样吗?”我问他。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话,先生,”欧摩先生回答我说。“但是因为有顾忌,所以才没问。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碍口的地方。如果有当事人病了,我们不能打听那个当事人怎么样。”
这种碍难开口的情况我原先还没想到,虽然我刚一进这个铺子的时候,我就又害起怕来,唯恐听到旧日听到的那种梆梆的声音。但是经他这样一说,我也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也就说,可也是。
“对啦,对啦,你明白啦,”欧摩先生点着头说。“我们不敢打听那个。唉!既然绝大多数的当事人都是病得不能好起来的,那我们要是说,欧摩与周阑对你问好,你今儿早晨——或者是今儿下午(这得看情况而定),觉得怎么样啊?那叫人听来,岂不要吓一跳?”
欧摩先生和我互相点了一点头。他又从他那烟斗里吸收了新的补充之气。
“就是这一点使得干我们这一行的把我们本来常常要表示的关心弄得也不能表示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认识巴奇斯先生归里包堆前后整整四十年啦,每次遇到他从我们这个铺子外面走过的时候,我都对他鞠躬,跟他打招呼。但是我可不能跑了去问‘他怎么样啦?’”
我觉得,这真有点跟欧摩先生为难,我也就这样对他说了。
“我希望,我这个人并不比别人更自私自利,”欧摩先生说。“你瞧,我这个肺管子,不定什么时候可以一口气上不来就把我断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知道,我不大会自私自利的。我说,一个人明明知道,他的肺管子说要一口气上不来,就会一口气上不来,像个吹火管拉破了那样,那他不会自私自利的;何况他又是都有了外孙女儿的人啦哪,”欧摩先生说。
我说,“决不会。”
“我对我干的这个行当并没有抱怨的意思,”欧摩先生说,“我没有那种意思。不论哪个行当,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我所希望的只是:当事人都心路更宽一些,理性更强一些才好。”
欧摩先生脸上一片怡然自足、和蔼近人之态,不声不响地又抽了几口烟。于是他接着刚才那个岔儿说:
“这样一来,我们要确实知道巴奇斯先生的病情怎么样,就没有别的法子,不得不专靠爱弥丽了。她知道我们的真意所在。她把我们看得就像一群小羊羔一样,决不会对我们疑神疑鬼,大惊小怪。敏妮和周阑刚刚往那一家去了,实在就是去问一问爱弥丽,巴奇斯先生今儿晚上怎么样(她下了班以后,就往那儿去了,去帮她姨儿点忙);要是你肯在这儿等着,等到他们回来了的时候,那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切详细情况的。你用点什么不用?喝一杯掺水的橘子汁和罗姆酒好不好?我自己抽烟就用橘子汁和罗姆酒就着。”欧摩先生把他自己那一杯拿起来说。“因为据说,这种饮料可以使呼吸通道变得滋润柔软。呼吸就是靠通道才起作用的啊。其实,哎呀呀,”欧摩先生哑着嗓子说,“我这并不是呼吸通道出了毛病啦,我跟我女儿敏妮说,把我喘的气给足了,那我自己就能把呼吸通道修好了,我的亲爱的。”
他实在没有余气可喘,而且看到他发笑,真令人大大地惊心。我等到他又好了一些了,可以跟他谈话了,我就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是对他要款待我的饮料却谢绝了,因为我刚刚吃过正餐。同时承他好心好意,把我留下,等他女儿和女婿回来。我看到这样,知道我非在他那儿等不可,我就问他小爱弥丽怎么样。
“呃,先生,”欧摩先生从嘴里把烟袋拿开,为的是他可以摸下巴,同时说,“我跟你说实在的吧,她要是结了婚,我可就太高兴了。”
“这是为什么哪?”我问。
“呃,她这阵儿有些心神不定,”欧摩先生说。“这并不是说,她没有从前好看啦,因为她比从前更好看——我对你担保,她比从前更好看。也不是因为她干起活来不如从前了,因为她干起活儿来还是跟从前一样。她从前一个人能顶六个人,她现在还是一个人能顶六个人。但是,她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无情无绪的。如果大概齐说,你明白我这句话,”欧摩先生又摸了一下下巴,抽了几口烟,说,“‘使劲拉,用力拉,伙计们,一齐拉,啊哈!’[1]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可以跟你说,她短少的就是那个劲头儿。这是大概齐说的。”
欧摩先生脸上和态度上所表现的太明显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感到亏心地直点头,算是表示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看到我这样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好像很高兴,所以又接着说:
“我说,我认为她这种无情无绪,主要地是因为她的状况还不稳定,这是你知道的。我们——她舅舅和我——她的未婚夫和我——下了班以后,都把这个问题谈了又谈;我的看法是,主要是因为她的情况现在还不稳定。你得永远记住了,爱弥丽,”欧摩先生轻轻地把脑袋摇晃着说,“是一个心肠特别慈爱的小东西儿。有一句格言说,你不能用猪耳朵做出丝钱袋来[2],呃,我可不敢那样说。我倒是认为能用猪耳朵做出丝钱袋来,不过可得你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头做起。她把那条老船做成了的那个家,连石头和大理石房子都比不上。”
“我敢保她是把那条老船做成了那样,”我说。
“看到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小东西儿,老离不开她舅舅,”欧摩先生说,“看到她每天每天紧箍着她舅舅那种样子,箍得紧而又紧,近而又近,简直是叫人开心的光景。不过,你要明白,要是情况是这样的时候,那总是心里头有斗争。这种情况,又有什么理由,应该让它不必要地拖下去哪?”
我倾耳静听这位好心眼儿的老人,全心全意地同情他所说的一切。
“因此,我就对他们说啦,”欧摩先生用一种心舒神畅、无牵无挂的语调说,“我说,你们绝不要死钉坑,认为爱弥丽非让期限订死了不可。期限可以由你们来支配。她干的活比原先想的可就值得多啦;她学习起来,比原先想的可就快得多啦。欧摩与周阑可以把没满的期限一笔勾销。你们想要不叫她受拘限,她就可以不受拘限。如果她以后愿意另作什么小小的安排,比如在家里给我们做一些零活儿,那很好;如果她不愿意,那也很好。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的。因为,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欧摩先生用烟袋碰了我一下,说,“像我这样一个喘不上气儿来的人,又是一个当外公的,还会跟一个像她那样眼睛像秋水、脸蛋像鲜花儿的小东西儿斤斤计较吗?”
“绝对不会,这是我敢保的,”我说。
“绝对不会!你说得不错!”欧摩先生说。“呃,她表哥——要跟她结婚的是她表哥,你当然知道?”
“哦,我知道,”我说,“我跟他很熟。”
“你当然跟他很熟,”欧摩先生说。“好啦,先生!他表哥好像事由儿很顺利,手头儿又宽裕,因为我这样说了,他很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对我表示了感谢(总的说来,他的行为一直都是使我敬重的),跟着就去租了一所小房儿,那所小房儿那个舒适劲儿,叫你我看了,都舍不得拿下眼来。那所小房儿这阵儿完全都陈设好了,又严密、又完备,像个玩具娃娃的起坐间一样,要不是因为巴奇斯先生的病(可怜的家伙)一天重似一天,那他们早就成了小两口了——我敢说,这阵儿,早就成了夫妻了。因为他的病越来越重,他们的婚期才往后推延了。”
“爱弥丽哪,欧摩先生,”我问,“她是不是比以前安定了一些了哪?”
“哦,那个,你要知道,”他摸着他那个双下巴回答我说,“按照自然的道理讲,是不能指望的。眼前看得见的变化和分离,我们可以说,很近又很远,两种可能同时并存。巴奇斯先生要是马上就伸腿了,那他们的婚期倒不至于再拖下去,但是他的病这样一耗时候,他们的婚期可就得拖下去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是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局面,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可以看得出来,”我说。
“这样一来,结果哪,”欧摩先生接着说,“爱弥丽可就仍旧还是有一点提不起精神来,定不下心去了。也许,总的说来,这种情况现在比从前还更厉害了。一天一天地,她疼她这个舅舅越来越厉害,她和我们这些人越来越舍不得分离。连我对她说一句好心好意的话都会叫她掉眼泪。你要是能看到她跟我女儿敏妮的小女孩在一块儿的光景,那你就要永远忘不了。哎哟哟!”欧摩先生琢磨着说,“她对那个小女孩儿那个爱法呀!”
那时候欧摩先生的女儿和女婿还没回来把我们的话打断,我想起来打听一下玛莎,我认为那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问他知道不知道玛莎的情况。
“啊!”他又摇脑袋,又很忧郁的样子回答我说,“不好呢,先生。不管你怎么看,都得说叫人不受用。我从来没认为那个女孩子会怎么坏。我在我女儿敏妮面前,老不敢提她,因为我一提她,我女儿马上就要说我——不过我从来没提过她。我们从来谁也没提过她。”
欧摩先生比我先听到了她女儿的脚步声,就用烟袋把我一捅,把一只眼睛一眨,作为警告。跟着,敏妮和她丈夫马上一齐进了屋里。
他们的消息是:巴奇斯先生“要多糟就有多糟”。他完全不省人事了;齐利浦先生刚要走以前在厨房惋叹地说:内科医学院、外科医学院和药剂师公会,如果把他们这三个机关的人员全都请到了,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对于他这个病,那两个学院早已无能为力了,而药剂师公会只能把他毒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又听说坡勾提先生也在那儿,就决定马上往那一家去走一趟。我跟欧摩先生、周阑先生、周阑太太都道过夜安,就以庄严肃穆的心情拔步朝着那一家走去,这种心情使得巴奇斯先生完全成了一位与前不同的新人物了。
我在门上轻轻一敲,坡勾提先生就应声而出。他并没像我原先想的那样,见了我觉得事出意外。坡勾提下了楼的时候,我在她身上也看到同样情况,并且从那时以后,我永远看到她这种情况。我想,在期待那种可怕的意外之时,所有一切别的改变和意外都收敛缩小,如同无物了。
我跟坡勾提先生握手,和他一块儿来到厨房,他把厨房的门轻轻地关上了。小爱弥丽正坐在炉前,用两只手捂着脸。汉站在她身旁。
我们大家都打着喳喳说话,说话中间,还时时听一下楼上有什么动静没有。我感到,厨房里会不见有巴奇斯先生,这多么奇怪!这是我上次到这儿没想到的。
“你真太好了,卫少爷,”坡勾提先生说。
“一点不错,太好了,”汉说。
“爱弥丽,我的亲爱的,”坡勾提先生说,“你瞧这儿,卫少爷上这儿来啦!唉,打起精神来吧,我的好宝宝!难道你对卫少爷连句话都没有吗?”
只见她全身都发抖,这是我连现在都能看到的。我握她的手,那只手是冰冷的,这是我现在仍旧还能觉到的。那只手唯一的活动,就是从我手里缩回。跟着她从椅子上溜开,跑到她舅舅那一面,把头低着,仍旧一声不响、全身发抖,趴在她舅舅怀里。“她的心太软了,”坡勾提先生一面用他那只大粗手摸着她那丰厚的头发,一面说,“所以经不住这样的伤心事儿。年轻的人,从来没经过这儿这样的凶事儿,都发怯害怕,跟我这个小东西儿一样——这本来是很自然的。”
她箍在他身上,箍得更紧,但是却没抬头,也没吱声儿。
“天已经晚了,我的亲爱的,”坡勾提先生说,“这儿是汉,特意上这儿来接你回家。我说,你跟着这另一个心软的人儿一块儿去吧!你说什么,爱弥丽?呃,怎么,我的宝宝?”
她说话的声音我听不见,但是他却把脑袋俯下去,好像听她说什么似的,跟着说:
“让你跟你舅舅一块待在这儿?我说,你真想要那样吗?跟你舅舅一块待在这儿,我的小乖乖?你丈夫,眼看就是你丈夫了,特为上这儿来接你回家,你可要跟着你舅舅一块儿在这儿待着。我说,你这样一个小东西儿,跟我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粗人在一块儿,没有人会有那样着想的,”坡勾提先生带出满怀得意的样子看着我们两个说。“但是海里含的咸盐也没有她心里对她这个舅舅含的疼爱多——你这个小傻子似的小爱弥丽!”
“爱弥丽要这样,是很对的,卫少爷,”汉说。“你瞧,既是爱弥丽愿意这么办,再说她又有些害怕,沉不住气,那我就让她待在那儿,待到明儿早晨好啦。我也待在这儿好啦!”
“不成,不成,”坡勾提先生说。“像你这样一个成了家的人——跟成了家一样的人——可白旷一天的工,可浪费一天的工,那可不是应当应分的。你也不能又干活,又看病人,那也不是应当应分的。那样可不成。你回家睡觉去吧。你不用怕没人好好照顾爱弥丽,这是我敢说的。”
汉没法子,只好听从了这番劝告,拿起帽子来要走。即使在他吻她的时候,——我从来没看到他在她跟前,而不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真正的上等人——她都好像箍着她舅舅箍得更紧,而且还有躲避她那未婚夫的样子。他开门走了,我跟着把门带上,免得满屋里那片寂静被搅扰;我关门回来的时候,看到坡勾提先生仍旧还在那儿跟她说什么。
“这会儿,我要到楼上去告诉你姨儿一声,说卫少爷来啦,这可以叫她多少提起点儿心气儿来,”他说。“我的亲爱的,你先在炉子旁边坐一会儿,把你那两只死凉死凉的手烤一烤。你用不着这么害怕,这么发慌。怎么?你要跟我一块上楼去?——那么好啦!那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好啦。——来吧!要是她这个舅舅,有朝一日叫人赶出家门以外,得跑到沟里去趴着,即便那样的话,卫少爷,”坡勾提先生说,说的时候那份得意,也不下于以往,“我相信,她也要跟着我去的。不过眼看就又另有一个人啦——眼看就又另有一个人啦,爱弥丽!”
后来,我上楼的时候,我从我以前住过的那个屋子前面过,那时候那个屋子黑咕隆咚的,我有一种模糊的印象,觉得好像爱弥丽正在屋子里面的地上趴着。但是,究竟真是她,还是屋子里乱糟糟的黑影,我现在不敢说。
我在厨房的炉前,有那么一刻的闲工夫,所以我就想到爱弥丽对于人要死的恐怖——再加上欧摩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我就认为,她所以跟平素判若两人,就是因为这个——在坡勾提还没下楼以前,我坐在那儿,数着那一架钟的滴答声,更深深地感到我四周那一片庄严的寂静。那时候,我还有一刻的闲工夫,对爱弥丽那种害怕死神的怯懦加以宽容。坡勾提把我抱在怀里,对我祝福又祝福,感谢又感谢,说我使她在苦难中得到那样的安慰(这就是她说的)。跟着,她请我到楼上去一趟,一面走,一面呜咽着说,巴奇斯先生一直就老喜欢我,敬爱我,在他还没沉入昏迷的状态之中以前,他还时常谈起我来。她相信,要是他从昏迷中还醒过来,那他见了我,一定会提起精神来的,如果世界上还有任何事物能让他提起精神来的话。
我看到他以后,只觉得他重新还醒过来的机会是小而又小的。他正躺在那儿,把个脑袋和两只胳膊用很不舒服的姿势伸在床外,把个身子一半趴在那个让他费了那么些心血和麻烦的箱子上。我听说,自从他无力爬出床外开箱子以后,他就让人家把那个箱子放在床旁边一把椅子上,他白天黑夜永远抱着那个箱子不放。他的胳膊现在就放在箱子上。时光和人世,正在从他身旁跑开溜走,但是箱子却仍旧还在那儿。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用解释的口气),“净是些破衣烂裳。”
“巴奇斯,亲爱的!”坡勾提几乎高兴起来的样子说,一面弯腰往他身上俯着,她哥哥和我就站在床的下手。“我那个亲爱的乖乖——那个亲爱的乖乖,卫少爷,来啦,原先就是他给咱们两个撮合的,巴奇斯!你不就是让他给我带的信儿吗?你还记得吧?你跟卫少爷说句话呀。”
他跟那个箱子一样,不言不语,无知无识,他那仅有的表现,只能从箱子那儿看了出来。
“他正跟着退潮的潮水一道去了,”坡勾提先生用手遮着嘴对我说。
我的眼睛模糊起来,坡勾提先生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但是我却打着喳喳儿重复道,“跟着潮水一道去了?”
“住在海边上的人要死的时候,”坡勾提先生说,“总是赶着潮水几乎都退枯了的时候。他们下生的时候,也总是赶着潮水差不多涨满了的时候——不到潮水涨满了,不能完全生下来。他这阵儿,正是跟着退潮的潮水一道去了。三点半钟潮水往外退,半点钟以后潮水就退枯了。要是他还能活到潮水再涨的时候,那他总得等到潮水涨满了,再跟着下一次退潮的潮水一道去。”
我们待在那儿看着他,看了好长的时候,看了好几点钟。他的知觉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在他跟前,对他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影响,我不必故弄玄虚,加以说明;但是事实却是:他最后开始微弱无力地胡思乱想起来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在那儿嘟嘟囔囔地说赶车送我上学校去的事。
“他又还醒过来了,”坡勾提说。
坡勾提先生碰了我一下,用郑重严肃、恭敬畏惧的口气说,“他跟潮水——两个一道很快地去了。”
“巴奇斯,我的亲爱的!”坡勾提说。
“克·巴奇斯,”他微弱无力地喊。“哪儿也找不出来再那么好的女人了!”
“你瞧一瞧!卫少爷来啦!”坡勾提说。因为这阵儿,巴奇斯先生睁开眼了。
我正要问他是否还认得我,但是还没等到我开口,只见他做出把胳膊一伸的样子,对我面带微笑、清清楚楚地说:
“巴奇斯愿意!”
那时潮水正落得最低,他同潮水一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