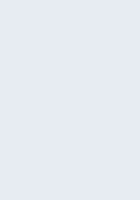戈登顶着凛冽的寒风往家里走去,风势将他的头发吹往脑后,秀出他那“好看的”额头,比任何时候都好看。路过的人看到他的姿态会以为——至少他希望如此——他是个放荡不羁之人,故意不穿上大衣。事实上,他的大衣在当铺里,当了十五先令。
西北段的柳堤路严格来说不算是贫民窟,只是很肮脏萧条,离真正的贫民窟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程。那里的出租屋家庭一张床睡五口人,要是有人死掉了,在尸首下葬之前,家里人都得与其同眠。在后巷里,女孩长到十五岁就和十六岁的男孩靠着斑斑驳驳的灰泥墙初尝禁果。不过,柳堤路本身看上去还保持着一丁点儿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体面,在其中一户房子门前甚至还挂着一位牙医的黄铜招牌。三分之二的房子都在客厅窗户的蕾丝窗帘之间,在一株叶兰的叶子上面挂着一块绿牌,上面用银色字体写着“公寓”二字。
戈登的女房东威斯比奇太太专门招徕“单身绅士”。房间是卧室兼起居室,有煤气灯,自己安装暖气,洗澡另外加钱(房子里有热水锅炉),在陵墓一般黑漆漆的饭厅里吃饭,饭桌中间密密麻麻摆着许多瓶已经凝固了的酱料。戈登中午回来吃午饭,一周付二十七先令六便士。
三十一号房门上方结了霜的气窗里透出煤油灯昏黄的光芒。戈登取出钥匙,摸索着插进钥匙孔里——这种房子的钥匙和锁头从来就没有严丝合缝过。玄关狭小漆黑——事实上,那只是一条走廊——带着洗碗水、卷心菜、破布地毡和卧室废水的味道。戈登看了玄关架子上那个涂漆托盘一眼。果不其然,没有信件。他已经告诉过自己不要指望有信件,但他还是心存侥幸。他的胸口掠过一阵不算疼痛但很不舒服的感觉。罗丝玛丽或许已经写了信了!自从她上回给他写信已经过去四天了。而且他给几份杂志投了几首诗,却还没有收到回信。能够让今晚好过一点的事情就是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有他的信件,但他的来信不多——每星期最多只有四五封。
玄关的左边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客厅,后面是楼梯,再过去是一条过道,通往厨房和威斯比奇太太自己住的不可侵犯的房间。戈登一进门,通道尽头的门打开了一英尺左右,威斯比奇太太探出头,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立刻缩了回去。晚上十一点钟之前,进出这间屋子都会被这样审视一番。不知道威斯比奇太太到底在怀疑你什么,可能是怕你偷偷带女人回来吧。她是那种经营出租屋的不好相处的体面女人,年纪约莫四十五岁,身材矮胖却很好动,脸色红扑扑的风韵犹存,而且特别会察言观色。她那头灰色的头发很漂亮,却总是愁眉苦脸。
戈登在窄窄的楼梯底下停住了脚步。上面传来了浑厚的歌喉,唱着粗俗的小曲,“谁怕大灰狼啊?”一个三十八岁的大胖子从楼梯的拐角处走了出来,跳着对于胖子来说很难想象的轻盈舞步。他穿着一套时髦的灰西装和一双黄色的鞋子,戴着一顶时髦的呢帽,外面披着一件粗俗无比的束腰蓝色风衣。这位是一楼的房客弗拉斯曼,是示巴女王卫浴精品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下楼的时候他扬了扬一只柠檬色的手套朝戈登致意。
“你好,老伙计!(弗拉斯曼管每个人都叫‘老伙计’)”他快活地打着招呼,“你还好吗?”
“糟透了。”戈登回了一句。
弗拉斯曼已经走到楼梯底下了,伸出短短胖胖的胳膊热情地搂着戈登的肩膀。
“开心点,小老头,开心点!干吗像奔丧一样。我去克莱顿酒吧,一起去喝点东西吧。”
“不去了,我得写东西。”
“哦,该死的!别那么见外嘛,好吗?在这里发呆有什么好?到克莱顿酒吧去,我们可以捏一捏那个吧女的屁股。”
戈登挣脱弗拉斯曼的胳膊。和所有个头瘦小的人一样,他讨厌人家碰他。弗拉斯曼只是咧嘴一笑,和大部分胖子一样,他很有幽默感。他真的很胖,那条长裤鼓鼓胀胀的,似乎他是被融化后再倒进裤腿里一样。不过,和其他胖子一样,他从不承认自己很胖。如果可以的话,没有胖子会说起“胖”这个字。他们用的是“肉头”这个词——“健壮”这个词更好。一个胖子说自己很“健壮”的时候最开心不过了。第一次与戈登见面时弗拉斯曼就想说自己很“健壮”,但戈登那双绿色的眼睛露出狐疑的神情,于是他转而用“肉头”形容自己。
“我得承认,伙计,”他说道,“我确实有点肉头,但并不影响健康,你知道的。”他拍了拍胸膛和腹部那条模糊的界线。“结实得很呢。站起身来可算得上身姿挺拔。不过——嗯,我想你可能觉得我很肉头。”
“像科特兹[51]。”戈登提了一句。
“科特兹?科特兹?就是经常在墨西哥山区里转悠的那个家伙?”
“就是他。他很肉头,但眼睛像雄鹰一样锐利。”
“啊?真是太有趣了,因为我太太也曾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乔治,’她说道,‘你长了一双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你的眼睛就像鹰眼一样。’她就是这么说的。那是结婚前的事情了。你懂的。”
弗拉斯曼现在与妻子分居了,不久前示巴女王卫浴精品公司给所有旅行推销员发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奖金,有三十英镑之多。弗拉斯曼和两个同事被派到巴黎向几家法国公司推销新推出的天然色泽性感唇膏。弗拉斯曼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的妻子这三十英镑的事。当然,那趟巴黎之旅是他生命中最快活的时光。直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一说起巴黎之旅他就会口水直流。他总是向戈登绘声绘色地吹嘘他的享受。揣着老婆根本不知道的三十英镑在巴黎待了十天!我的天哪!乖乖!然而,不幸的是,不知哪里走漏了风声,弗拉斯曼回到家里,发现报应正等候着他。他老婆用一樽雕花玻璃威士忌酒瓶打破了他的头,那是他们保存了十四年之久的结婚礼物。然后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自此弗拉斯曼便被流放到柳堤路。但他可不会因为这个而忧愁。事情总会过去的,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好几回了。
戈登又尝试着摆脱弗拉斯曼,登上楼梯。可怕的是,他心里其实很想和他一起去。他很想喝一杯——提到克莱顿酒吧就勾起了他的酒瘾。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钱。弗拉斯曼伸出一只胳膊跨过楼梯,拦住他的去路。他真的很喜欢戈登,觉得他是个“聪明人”——在他看来,“聪明”其实是没有恶意的精神癫狂。而且他不喜欢独自一人,就算走几步路到酒馆这么短的时间也不愿意。
“走嘛,伙计!”他催促道,“你需要喝杯吉尼斯啤酒让自己振作起来。你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还没见过雅座吧台那里他们新请来的小女孩呢。乖乖!就像水蜜桃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打扮得这么潇洒,对吧?”戈登冷冷地看着弗拉斯曼那双黄色的手套。
“被你猜对了,伙计!噢,就像水蜜桃一样!她是个金发女郎,而且懂的事情还挺多,这种骚货都是这样。昨晚上我送给了她一管我们公司的天然色泽性感唇膏。你真得看看她经过我的桌子时朝我晃着她那小巧的屁股是什么样子。她令我心悸了吗?心悸了吗?乖乖!”
弗拉斯曼猥琐地扭动着身子,舌头伸在双唇之间。然后,他假装戈登就是那个金发吧女,搂着他的腰,温柔地掐了他一把。戈登将他推开。有那么一刻,去克莱顿酒吧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几乎征服了他。噢,喝上一品脱啤酒!他几乎可以感觉得到啤酒涌入喉咙的快感。要是他有钱的话就好了!就算只有七便士买一品脱啤酒也好。但光想又有什么用呢?他口袋里只有两个半便士。你可不能指望别人会帮你付酒钱。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烦我!”他气恼地说道,挣开弗拉斯曼,登上楼梯,没有回头看一眼。
弗拉斯曼把头上的帽子摆正,有点愠恼地朝前门走去。戈登闷闷不乐地想到,如今情况总是这样,他总是冲别人友好的问候泼冷水。当然,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总是关于钱的问题。当你口袋里没钱的时候,你无法友好待人,甚至无法彬彬有礼。他顿时觉得自怜自伤。他的心向往着克莱顿酒吧的雅座吧台、啤酒美妙的味道、温暖明亮的灯光、欢声笑语、滴满啤酒的吧台上酒杯轻轻碰撞的声音。金钱!金钱!他继续顺着黑漆漆冒着一股怪味的楼梯走着。想到要在阁楼度过阴冷的漫漫长夜,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二楼住着罗伦海姆,一个又黑又瘦的家伙,长得像只蜥蜴,看不出是什么族裔或多大年纪,每周靠兜售吸尘器挣三十五先令。戈登总是匆匆忙忙地走过罗伦海姆的门口。罗伦海姆是那种世界上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很想有人能陪陪他。他如此孤独,只要你在他门外经过时走得慢了一些,他肯定会冲出来,又是拉扯,又是哄骗把你拽进他的房间里,让你听他那些冗长而疯狂的如何哄骗小女孩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戏弄雇主的恶作剧。而且他的房间比任何一家寄宿旅馆的房间都要来得更阴冷肮脏一些。到处都是咬了几口的面包和人造黄油。这里还有另一个租客,好像是个工程师,上的是夜班。戈登只见过他几面——是个块头很大、脸色阴郁苍白的家伙,屋里屋外都戴着圆礼帽。
屋里很暗,戈登熟练地摸到煤气喷嘴,点着了灯。这间房中等大小,说大呢又不足以隔成两间,但说小呢一盏不太好的油灯根本不足以供暖。里面的家具都是那些你可以想象会在顶楼出现的东西。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棕色的亚麻布地毡,摆放着水盆和水壶的洗手架。那个白色的水壶是个便宜货,你会以为那是一口夜壶。窗台上摆放着一个涂着绿漆的花盆,种着一株病恹恹的叶兰。
窗户下面摆着一张饭桌,上面铺着一张沾了墨迹的绿色桌布。那张就是戈登的写字桌,是他几经周折才从威斯比奇太太那里要来的。原来这里摆放的是一个竹制的临时茶几——是用来摆放那盆叶兰的——她觉得摆在顶楼很合适。直到现在她还总是絮絮叨叨的,因为戈登一直不肯好好收拾桌子。这张桌子上总是东西放得一团糟,几乎被一堆稿纸遮盖住了,大概得有两百多页,脏兮兮的,页角都卷了起来,上面写满了字,用笔划掉,又写上了字——就像迷宫一样,只有戈登掌握了开启迷宫的钥匙。每样东西上面都蒙着一层灰,几个小碟子上面落满了烟灰和扭曲的烟屁股。除了壁炉架上的几本书外,这张桌子和上面那堆杂乱的稿纸就是戈登的个性在这个房间里留下的印记。
屋里冷得出奇。戈登决定把油灯点着。他拿起油灯——感觉很轻,备用的灯油也快烧完了,到星期五才能去添油。他打着一根火柴,一团黯淡的黄色火苗不情愿地绕着灯芯亮了起来。运气好的话它还能燃烧上几个小时。戈登扔掉火柴,眼睛落在草绿色的花盆里那株叶兰上。这株东西还真是奇怪,只有七片叶子,似乎不会再长出新叶了。戈登心里隐隐讨厌这株叶兰。他试过很多次,想将其扼杀,但都没有成功——不给它浇水,用点着的烟屁股烫它的茎部,甚至往土里掺盐。但这该死的玩意儿似乎是不死之身。无论怎么虐待它,它总是病恹恹地继续活下来。戈登站起身,故意将沾了煤油的手指往叶片上面擦拭了一下。
这时楼下响起了威斯比奇太太泼妇骂街一般的声音。
“康——斯托克先生!”
戈登走到门口,冲着下面喊道:“怎么了?”
“你的晚饭已经做好十分钟了。你怎么还不下来吃饭呢?我还等着洗碗哪。”
戈登走到楼下。餐室在一楼弗拉斯曼先生房间的对面。房间里很冷,而且通风不畅,有一股子味道,即使是在中午也很昏暗。里面摆放着好几株叶兰,戈登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它们堆放得到处都是——餐具柜上、地板上、临时桌台上、窗台的花架上,把光线都给遮住了。在半明半暗的屋里,周围摆放了这么多株叶兰,你感觉就像置身于不见天日的水族馆里,身边尽是枯燥乏味的海底植物。戈登的晚餐已经摆好了,正等候着他,破裂的煤气灯在桌布上投下一圈白色的光,他坐了下来,背朝着壁炉(里面摆放着一株叶兰,而不是生着火),吃他那碟冷盘牛肉,就着加拿大黄油、捕鼠诱饵那般大小的奶酪和潘彦牌腌黄瓜吃了两片板硬的白面包,喝了一杯有股霉味的冷水。
回到房间时那盏油灯已经快熄灭了,不过他想还能烧一壶水。现在将进行今晚的秘密行动——偷偷泡一杯茶喝。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摸摸地泡一杯茶。威斯比奇太太不肯给房客泡茶,因为她不想另外烧水,而私自在房间里泡茶是严令禁止的。戈登厌恶地看着桌子上那堆乱糟糟的稿纸,在心里对自己说今晚他绝对不会写作。他会喝一杯茶,把剩下的烟抽掉,读一读《李尔王》或《神探福尔摩斯》。他的书就放在壁炉架上闹钟的旁边——平装本的莎士比亚作品、《神探福尔摩斯》、维庸的诗歌、《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恶之花》和一堆法文小说。但如今他已经不读这些书了,《莎士比亚》和《神探福尔摩斯》除外。现在,他要泡茶了。
戈登走到门口,半推开门,倾听着有没有威斯比奇太太的动静。你得非常小心,她能蹑手蹑脚地摸上楼,把你逮个正着。私自泡茶可是严重的罪名,仅次于带女人回家。他悄悄地闩好门,从床底下拉出他那口廉价的行李箱,打开锁头,从里面拿出价值六便士的伍尔沃斯牌烧水壶、一包立顿茶叶、一罐炼乳、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这些都用报纸包着,免得碰裂了。
他泡茶时自有一套步骤。首先他往烧水壶里装上半满的水,然后放在煤油灯上,接着跪了下来,铺开一张报纸。当然,昨天的茶渣还在茶壶里。他把茶渣摇出来,倒在报纸上,用大拇指清理干净茶壶,把那堆茶渣折成一个纸包。待会儿他就会偷偷将其带下楼。清理茶渣是最冒险的一个环节——难度不亚于毁尸灭迹。至于茶杯,他经常等到早上再拿到洗手盆里洗干净。这真是卑鄙的勾当,有时候令他觉得很恶心。真是奇怪,寄居威斯比奇太太篱下做什么事情都得偷偷摸摸的。你觉得她总是在监视着你,而事实上,她的确喜欢随时蹑着脚尖在楼上楼下转悠,希望逮到房客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房子里住,就算上厕所也不能安心,因为你总是觉得有人在偷听你如厕。
戈登又把门打开,专注地倾听着。没有动静。啊!楼下传来餐具的碰击声,威斯比奇太太正在清洗餐具,现在下去或许安全。
他踮着脚尖下楼,把那包潮湿的茶渣搂在胸前。厕所在二楼,在楼梯的拐角处他停下脚步,又倾听了一会儿,啊!下面又传来餐具的碰击声。
安全!诗人戈登·康斯托克(“前途无量的希望之星”,《时代文学增刊》曾经这么说过)匆忙溜进厕所,把茶渣扔到下水道里,拉起塞子。然后他匆忙溜回房间,重新闩好门,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音,给自己泡了一壶新茶。
现在房间里暖和多了,茶和香烟施展出了短暂的魔力。他感觉没有那么无聊烦躁了。说到底他得多多少少写点东西吧?这是当然的。每当他蹉跎了一个晚上后他总会痛恨自己。他不大情愿地把椅子拉到桌旁。甚至翻开那堆乱糟糟的稿纸也需要下一番决心。他把几张脏兮兮的稿纸拿了过来,摊开端详着上面写的字。上帝啊,多么潦草的笔迹!写了字,划掉,在上面又写了字,然后又划掉,直到最后稿纸看上去就像开了二十次刀的可怜巴巴的癌症病人。不过,没有被划掉的笔迹很清秀,有“学者派头”。戈登下过一番苦功练出这手有“学者派头”的字,跟他在学校里所学的铜版印刷体的字很不一样。
或许他能写点东西,写上一会儿也行。他在这堆稿纸里翻寻着。昨天他写的那一段诗稿哪儿去了?这首诗很长——确实很长,当这首诗完成时会是一首相当长的诗——大约两千行,以君王诗体[52]为格律,描述在伦敦的一日。这首诗起名叫《伦敦之乐》。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雄心勃勃的工程——只有那些生活优裕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刚开始写这首诗的时候戈登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两年前他开始创作时怎么就那么鲁莽冲动呢!那时候他抛弃了一切,沦落到贫困的泥沼中,而这首诗的构思也是当初他的动机的一部分。那时候他充满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写出这么一部长诗。但几乎从一开始,《伦敦之乐》就出了岔子。这首长诗对他来说太浩繁了,这就是事实。从一开始这首诗就没能有条不紊地写下去,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零星片段。苦苦写了两年,这些就是他拿出来见人的东西——都是一些没有完成的残章片断,根本凑不到一块儿。每一张稿纸上都只写了几句诗,然后在几个月间反复修改。只有不到五百行诗句你可以说确实写完了,而他再也无法续写一句,只能就着这堆诗稿修修改改,这里添加几个词,那里删掉几个词,完全乱了套。这再也不是他创作出来的诗稿,而是变成了他苦苦与之斗争的梦魇。
除此之外,两年来他就只创作了一些短诗——或许总共有十来首吧。他总是无法让心情平静下来,而对于创作诗歌,平静的心情至关重要。他“无法创作”的时间越来越频繁。在所有人里面,只有艺术家会说他“没办法”工作。但这的确就是事实。有时一个人的确写不出东西。又是钱的问题,总是钱的问题!没钱意味着过得不舒服,意味着忧心忡忡,意味着没有烟抽,意味着总是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而最重要的是,意味着孤独。当你周薪只有两英镑时,除了孤独的生活你还能怎么样?生活在孤独中可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一点他很清楚,《伦敦之乐》将不会是他心目中所想象的那首长诗——他很清楚这首诗永远都写不完。当戈登能面对真相的时候,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尽管如此,正是因为这样,他更要写下去。这是他的坚持,是他对贫困和孤独的反击。有时候创造的灵感还是会回来的,或者说,似乎回来了。今晚它就回来了,但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也就是抽两根烟的工夫。烟雾在他的肺里缭绕,他的精神摆脱了这个卑劣的现实世界,来到了孕育诗歌的深渊。煤油灯在他的脑袋上方发出令人放松的声响。词汇变成了鲜活的事物。他的眼睛带着疑惑,落到了一年前没写完的对偶句上面。他不停地对自己说这句话写得不好。一年前读上去还蛮好的,现在读起来透着一股子俗气。他在那堆稿纸中翻寻着,直到找到一张背面没有写字的空白稿纸,把那两行对偶句抄了上去,然后又写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每句话都对自己反复朗读几遍。最后,还是没有一句能让他满意。这个对偶句得去掉,太低俗了。他找到那张原稿,用粗线将那个对偶句删掉了,觉得颇有成就感,觉得光阴没有虚度,似乎将辛苦的劳动成果摧毁掉与创作出结晶是一回事。
突然楼下传来两记敲门声,整座屋子都在震动。戈登吓了一跳,精神从深渊里回来了。是邮递员!《伦敦之乐》被抛诸脑后。
他的心扑通乱跳。或许罗丝玛丽给他回信了。而且,他给几份杂志投了两首诗,事实上,其中一首诗他已经几乎放弃了希望。几个月前他把那首诗寄给了一份美国报纸《加利福尼亚文学评论》。或许他们嫌麻烦不肯退稿。但另一首诗投给了一份英国刊物《报春花季刊》。这首诗他觉得有点希望。《报春花季刊》是一份顶讨厌的文学刊物,许多时髦的娘娘腔作家和笃信罗马天主教的职业写手的作品同刊发表。它也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之一。要是能在里面发表一首诗,那你就成名了。戈登打心眼里知道《报春花季刊》并不会发表他的诗作。他的文字还够不上水准,但奇迹偶尔也会发生,如果不是奇迹,意外也行。毕竟,他们收到他的诗稿有六个星期了。如果他们不接受诗稿的话,会保留六个星期吗?他试图平息这个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最低限度,罗丝玛丽可能给他写信了。自从她上次写信已经整整四天了。要是她知道这样会令他感到多么失望,或许她就不会这么做。她的信——写得很长,单词老是拼错,总是写了很多荒唐的笑话和对他热烈的爱的宣言——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她是永远不会明白的。这些信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他,在他的诗稿被无情地退回来时安慰了他。事实上,那些刊物总是把他的诗稿退回。只有《反基督报》是例外,因为这份刊物的编辑拉沃斯顿是他的朋友。
楼下响起了脚步声,总是得等上几分钟威斯比奇太太才会把信带到楼上来。她喜欢摆弄这些信,掂一掂信有多厚,看一看邮戳,对着灯光照一照信封,猜一猜里面装了什么东西,然后才交给信件的主人。她似乎对这些信件拥有处置的权利,她觉得这些信件寄到她的家里,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就是她的。如果你走到前门自己去取信的话,她会很不高兴。另一方面,她又不喜欢拿信上楼。你会听到她慢吞吞地走上来的脚步声,如果有你的信,楼梯平台上会传来沉重而痛苦的呼吸声——这是让你知道威斯比奇太太为了你爬了这么高的楼梯,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最后,在不耐烦的嘟囔声中,她把信件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威斯比奇太太正在走上楼梯,戈登倾听着,脚步声在一楼停了下来。弗拉斯曼有一封信。脚步声上来了,在二楼又停了下来,那个工程师有一封信。戈登的心跳得有点疼。一封信,求你了,上帝,来一封信吧!又有脚步声了。是上楼呢还是下楼呢?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这必须的!啊,不,不要!脚步声减弱了。她下楼去了。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没有信件。
他又拿起笔,但这只是在装腔作势。她终究没有写信!她真是太可恶了!他没有继续工作的心情了。事实上,他真的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失望涌满了他的心,五分钟之前他的诗在他眼中似乎是鲜活的事物,但现在他清楚地知道那只是毫无价值的废话。他厌恶地把散落的稿纸收集起来胡乱码在一块,将它们堆在桌子的另一头那株叶兰底下。再让他看到这些诗稿他可受不了。
他站起身。现在睡觉还太早了,至少,他没有睡觉的心情。他渴望能有点娱乐——廉价而轻松的娱乐。去电影院、抽烟、喝啤酒。没用的!这些他都付不起钱。他决定读《李尔王》,忘记这个卑劣的世纪。但是,他从壁炉架上拿下来的是《神探福尔摩斯》。《神探福尔摩斯》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他已经烂熟于胸。灯油渐渐枯竭,屋里越来越冷。戈登从床上拽过被子,裹在腿上,然后坐下来读书,右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放在大衣下保暖,读了一遍《斑点带子案》。那盏小煤气罩灯在上面叹息着,灯芯烧得很矮,圆形的火苗看上去像两个单薄的括号,热力比一支蜡烛大不了多少。
楼下威斯比奇太太房间里的时钟敲响了十点半。晚上你总能听见它的钟声。当—当—当,宣告着末日的到来。壁炉架上,小时钟的嘀嗒声又清晰可闻了,让戈登想起了时间在狰狞地流逝。他看了看自己身边,又一个晚上荒废了。时间就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流逝。夜复一夜,恒久不变。孤单的房间、没有女人的床铺、尘土、烟灰、叶兰的叶片。他已经快三十岁了。纯粹是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拿了一叠《伦敦之乐》的稿纸,就像看着昭示着死亡的骷髅一样端详着那些文字。《伦敦之乐》作者:戈登·康斯托克,《耗子》的作者。这是他的鸿篇巨著,花费两年心血创作的成果(成果,确实如此!)——就是这么一堆乱糟糟的文字!今晚的成果就是——删掉了两行诗句,没有多写两行,而是少写了两行。
那盏灯发出一声像噎着了的轻响,然后熄灭了。戈登艰难地站起身,将被子扔回床上。或许在屋里变得更冷之前上床睡觉比较好。他朝床铺走去——等等,明天得上班,他给时钟上了发条,调好了闹钟。什么事也没做成,又是一夜的安眠。
他躺了好一会儿才有力气脱衣服。他双手放在头下,穿着全套衣服躺在床上大约得有十五分钟。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形状像是澳大利亚地图。戈登没有坐起身子,勉强将鞋子和袜子脱掉。他抬起一只脚丫看了看。他的脚小而秀气,没有力气,就和他的手一样。而且上面很脏。他已经有将近十天没洗澡了。脚上这么脏让他觉得很难为情,蜷起身子坐了起来,脱掉身上的衣服,将衣服随手扔在地板上。然后他灭掉煤油灯,钻进被窝里,打着冷战,因为他光着身子。他总是光着身子睡觉,已经有一年多没穿过睡衣了。
楼下的时钟敲响了十一点。刚钻进床单的那阵寒意渐渐退去,戈登想起了下午他写了开头的那首诗。他低声念了一遍已经写完的那一节诗文: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
落叶殆尽的白杨树弓下了腰,
烟囱飘舞着黑黢黢的缎带,
在昏沉沉的空气中摇摆而下,
撕裂开来的海报战栗颤抖着。
这些诗句念起来就像僵硬呆板的机械发条,嗒—嗒、嗒—嗒!空洞无聊的内容让他泛起了恐惧。这首诗就像一件毫无用途的小机器滴答作响。韵律遥相呼应,嗒—嗒、嗒—嗒。就像上了发条的人偶在点头。诗歌!毫无价值的文字。想到自己毫无作为,他就睡不着。三十岁了,他的生活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时钟敲响了十二点。戈登伸直双腿,床铺变得暖和舒服了。与柳堤路平行的一条街道上有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灯光射到百叶窗上,投下那株叶兰的一片叶子的剪影,形态就像阿伽门农[53]的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