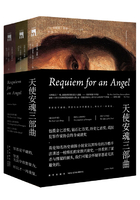徐福说:“到了。”
邵士喜就看见远处的山坡上布满了铁丝网,还有山巅上的岗楼。走近些再看,一长串墨面蓬首的人迤迤逦逦从一口山洞里扯了出来。这些人形若野鬼,散散漫漫地,无精打彩地飘游着。邵士喜看得呆如木鸡,失魂落魄。邵士喜说:“下窑的就这样?”
徐福说:“你以为是赶庙会哩。”
邵士喜说:“福子哥,真是这样,这窑我不想下了。”
徐福生气了,说:“行啊,你回,现在就走吧。还是顺着这条路,回去吧。你爹还等你镶金牙哩。”
邵士喜没有动,哭丧着脸说:“福子哥,你以为我真回喀。我不回,我爹还等着我的钱置地哩。”
徐福走出一步,又退了回来,笑着说:“这就对了,你以为我想下这煤窑,不是不下窑娶不上婆姨么。娶不上婆姨生不下孩,我娘就老也咽不了那口气么。”
他们一前一后走到井口旁的瓦房里。瓦房里坐着一个戴瓜皮帽,穿绸坎肩的胖子。胖子在喝茶,无精打采地瞟了他们一眼。徐福畏畏缩缩地走上前去说:“牛厂长,我这次回去还领来一个。”
胖子象打量牲口似的看了邵士喜一眼,说:“有点瘦,不过,看得出来还能受苦。”
徐福说:“受苦是好把式哩。”
胖子点点头,说:“去劳资股交钱领工具吧。”
徐福示意邵士喜出去,说:“厂长,不是介绍一个,给一份介绍费么。”
胖子说:“那是三天前的章程,从今日开始,不再给介绍费了。”
徐福说:“我不是白介绍了么。”
胖子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你可以让他再回去么。”
徐福就退出来了,他看见邵士喜痴眉瞪眼地望风景,就懊丧地说:“你不是想回么,你回吧,这下窑真不是人干的。”
邵士喜惊异地,说:“窑上不要我?”
徐福边走边说:“这些王八蛋,说话不作数,屙下能吃进去。我操他八辈祖宗。眼看到手的五块钱没有了。”
邵士喜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小跑着在他身后追着,喘着气说:“老虎不吃回头食,我咋好意思回去哩,你让我咋和我爹我娘说哩。”
徐福把邵士喜带到山坡下的窑洞外边,说:“你想下就下吧,将来有个三长两短可别埋怨我。记住,不是我诓你来的,是你非要来的。”
徐福又说:“愿打愿挨。我就不说什么了。你带钱了没有?”
邵士喜摇摇头,说:“我是出来挣钱,还带什么钱。”
徐福说:“这就怪我了。我先给你垫上吧。不交钱领不上油灯,领不上铁镐。没有油灯,没有镐把,你咋挣钱哩。”
邵士喜说:“我给有钱人家扛长工,也没听说自己出钱买镰刀,买锄头呀。”
徐福说:“就是么。可这矿上就这章程。二占区比日本人还杀剥。我给你先垫上,下月开资你还我。人不亲土还亲。谁让我把你领出来了呢。士喜子,你说我这人咋样?”
邵士喜忙说:“你这人真好。”
徐福嘻嘻地笑了,说:“我这人就见不得栖惶人。那天,你一说要跟我来下窑。我就咋也忘不了啦。醒着睡着都记着你的这件事。”
邵士喜说:“你心肠真好。”
徐福说:“好不好吧。人好能咋地。你等着,我给你登记,领工具去。”
不一会儿,徐福带着油灯,拿着铁镐走了出来,说:“都办妥了。他娘的,又涨价了。三块八了。要是回了咱村里,一块钱也没人要。明坑人么。”
邵士喜接过油灯,接过铁镐,左看看,右看看,说:“就这,靠这就能挣钱?”
徐福说:“可不就靠这,你以为打日本人呢,要洋枪洋炮。咱下窑的就靠这。”又说:“士喜子,饿了吧?”
邵士喜说:“不饿。”
徐福说:“你别骗我了,走吧,咱们喝酒吃饭去。今日本来应该是你请我。可你还没挣上银钱,我就先请你吧。”
邵士喜忙说:“等我日后挣下银钱,隔几天请你一次。”
徐福笑着说:“不敢,我也承受不起,你一年请我三四次就行了。我这人别的不好,就爱喝几盅酒,喝得迷迷糊糊,心里就清静了。啥也不想了。什么爹娘老子啦,娶婆姨生孩儿啦,熬日子啦,啥都忘得光光的啦。脑子就没有糟心的事啦。”
邵士喜说:“真是的?”
徐福说:“我还哄你不成。”
徐福举起碗说:“喝吧。”
邵士喜猛喝一口,顿时火辣辣得眼冒泪花,卷着舌头说:“不行,我不行。”
徐福说:“那有不行的,你再喝一口。”
邵士喜就又喝了一口,酒铺里的人便在他眼睛里颠颠覆覆的晃悠,他说:“我真不行了,我要晕过去了。”
徐福说:“你吃菜。”
邵士喜的手颤颤地去挟菜,却挟在了徐福的脸上。徐福就开心地大笑,说:“你真喝多了。没事的。来,我把盘子递到你嘴边,你只张口就行了。对,对,就这样吃。”
邵士喜像狗舔盘子似的吃了几口,便觉得舒服了些。他还想吃下去,却见盘子忽忽悠悠地飘走了。
徐福把盘搁在自己一边说:“你太能吃了。一盘子山药蛋,你吃下多半盘子。”
邵士喜羞得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支了头,傻嘿嘿地笑。
徐福浅斟慢饮着,一边说:“咋,舒服吧。还想家不想了,不想了吧。还觉得下窑苦不苦了,不想了吧。对,一喝了酒,就啥他娘的也不想了,就想睡觉,下窑的人,没有不喝酒的,为啥,喝了酒就啥也不怕了,二占区也不怕了,天下就是咱老子一个人的。”
邵士喜直盯盯地看着徐福说:“福子叔,你说得太好了。”
徐福卷着舌头说:“你咋又叫我叔了,不要叫我叔,你一叫我叔,我就老了,我还没娶婆姨呢。”
邵士喜很愧疚,拍着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一喝酒就忘了,福子哥,你不见我的怪吧。”
徐福说:“我咋能见你的怪呢。人不亲还土亲呢。我只是不想让你叫我叔,我比你才大三四岁。我咋好意思当你的叔呢。走在路上,你叫我叔,人家还以为我五六十了,我虽然显得老气,可我到底才二十六岁。”
邵士喜说:“福子哥,你一点也不显老,咱俩走在外面,怕是人家都以为你是弟,我是哥哩。”
徐福就“吃吃”地笑了,把菜盘子又推过去说:“士喜子,你真会说话。行,你行,你吃菜。”
邵士喜想吃菜,但他发现盘子里连一根土豆丝也没有了。徐福在空盘子里划拉着,还是热情地招呼着说:“士喜子,吃菜,快吃,一会儿就凉球了。”
邵士喜也在空盘子里用筷子划拉着,把筷子尖放在嘴里舔舔,说:“这菜炒得地道。比我娘炒得好吃。”徐福说:“当然好吃,你娘咋能比得了。”
这时,有一黑脸汉子进来,徐福招呼说:“白永祥,来,坐下,喝酒,吃菜。”
叫白永祥的人不屑地瞅了一眼,说:“吃啥,喝啥,你们酒也干了,菜也完了,叫我吃啥。”
徐福看着空空的盘子,说:“你真能胡说,这明明还满满的一盘子山药蛋么,你说没了。你的眼真是瞎了。士喜子,你说,这盘子里还有菜没有?”
邵士喜说:“有呀,咋能说没有了呢。”
白永祥哈哈大笑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招呼上酒上菜,又回过头来说:“你又领来一个?”
徐福点点头,说:“他非要来,我就领来了。我说,这下窑有甚好的,四块石头夹一块肉,有今日没明日的,可他还是非要来。他以为一来,就能镶上金牙呢。”
白永祥说:“你知道不知道,德元昨日死了,张八子前日也殁了。”
徐福的筷子就惊得掉在了地下,说:“我走得时候,他们还好好的么,咋就死了。”
白永祥没理他,把头伸进碗里,“咕咕”地喝着酒,喝尽后,把碗使劲朝桌上一砸,“快,再给老子上一碗,这酒兑他娘的水了。”
徐福眯缝着眼看了他一下,说:“永祥,昨日夜里你又逛窑子了吧。”
白永祥回头瞪着他,说:“你是那把壶不开提那把壶。”
徐福笑笑,又说:“你给我说,昨日夜里到底去了没有?”
白永祥把酒杯“砰”地一声砸在桌上,说:“不去白不去,说不定那天就见阎王爷了。好活一阵算一阵。”
徐福还是傻笑着,说:“你想得对,不象我,要多冤有多冤,今日死了,还不知道女人是啥滋味哩。我连女人那个东西长着啥样还不知道哩。”
白永祥瞄了一眼邵士喜说:“你看你,当着这个娃娃说这些话。”
徐福说:“他是娃娃?他说不定比我知道得还多哩。你说是不是,士喜子。”
邵士喜羞得低下了头。
徐福又说:“永祥,你也不要光图个老二舒服,攒点钱娶个婆姨,日日都是你的。”
白永祥仰头哈哈笑了两声,说:“我娶婆姨,我拿球甚娶。”
徐福走到他身边,端起他的酒碗呷了一口,压低声说:“都说你想上山去哩?”
白永祥急忙左右看了一眼,喝斥他说:“你她娘的,嘴咋这么贱,这是这里说得事么。”
徐福“嘻嘻”笑着,说:“山上能要你这爱逛窑子的人,还不把你的老二割了。”
白永祥火了,一把将徐福推倒在地,悻悻地走了。徐福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脸,对邵士喜说:“这人,吃不下窑里的苦了,想奔游击队去哩。”
邵士喜忙扶他起来,说:“福子哥,这话可不敢乱说。”
徐福晃晃地站起,说:“球,我不怕,我也想上山投八路呢。”
邵士喜觉得自己没吃饱,可还是跟着徐福下了井,徐福说:“你就跟在我后面。”
邵士喜就亦步亦趋地趟着水朝窑里走。
徐福说:“我咋走,你咋走,我咋干,你咋干。我可不想让你死,你还欠我的酒哩。对了,这工具钱我还给你垫着哩。”
邵士喜牙齿有些打颤,说:“福子哥,这些我都记得哩。现在是,爹亲娘亲不如师傅亲。”
徐福就在前面嘻嘻地笑:“士喜子,你真会说话,我以前看你呆头呆脑,昨日看了,你还真行。”
邵士喜说:“我不行,是我爹我娘教我呢。”
巷道里阴森森的,伸手不见五指,偶而看见一两盏油灯,也象妖鬼的眼睛,一只老鼠从邵士喜的脚边蹿过,把他吓得一个悸愣。
邵士喜想抓住徐福的后襟,徐福却躲着他,“福子哥,咋还不到呢?”
徐福说:“早着呢,你知道这掌子面有多远,五里路呢,从你们村到我们村,前面的煤都让日本人挖走了。”
一盏油灯由远而来,渐渐地走近了,邵士喜看见一个牲畜驮着一筐煤朝这里走过来了,忽然有人声道:“接班来啦?”邵士喜定晴一看,那四脚着地拖着筐的不是牲畜,竞是一个人,当即惊出一身冷汗。把油灯照近了看,就见是昨天在酒铺里见过的叫白永祥的人。
白永祥歇了歇又匍匐着远去了。
邵士喜说:“这下窑真不是人干的。”
徐福回过头来剜了他一眼,说:“你真球不会说话。这咋不是人干的。你不是人,我不是人?你以为你是东家,你是少爷,你是仰着身卖的窑姐。”
邵士喜没想到一直慈眉善目的徐福会发这么大火,当即呆了。忙说:“福子哥,你骂我吧,我真球不会说话。”
徐福说:“我不是骂你。我是看你不会说话。”
邵士喜说:“我真是不会说话。”
连续下了几天井,邵士喜就有些累。他见不远处的徐福和其它窑工都仰卧在煤堆上歇着,也就蹉伏在煤帮上打开了盹。迷迷糊糊中,就听见一声呼叫。他还是困得睁不开眼。突然就觉得脊背上火辣辣的痛。他一支身,头又撞在煤帮上,顿时眼冒金星。“我让你睡,我让你偷懒。”一个人在他身边吼着,一边将皮鞭打在他身上。邵士喜火了,抓起一块煤要往那人身上砸。徐福爬了过来,把他手上的煤块夺得扔了。就听徐福对那人说:“他是新来的,李监工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你就看在我面子上,饶他这次吧。”
李监工“哼”了一声,说:“我刚才看见他拿煤块了,他想砸我不是,反了他的。”
徐福挡在他的面前,赔着笑脸说:“他那里敢呢。他刚来,有眼不识泰山哩。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老忙去吧。”
李监工悻悻地走了,走远了,徐福就“啐”了李监工的背影一口,说:“这个完八蛋,不就仗他老婆让厂长日着,做个臭监工么,娘的。”
邵士喜还委屈得流泪。徐福就说:“你爹说啥了,不打勤的,也不打懒得,就打不长眼的,监工不在,你愿咋歇就咋歇,监工来了,你就得可劲地干。知道了吧。”
邵士喜点点头。摸摸脊背,还火辣辣的痛,就骂道:“我操他十八辈祖宗。”
徐福说:“你骂吧。可是你记住,监工来了,你就得装孙子哩。”
白永祥鼓动大家罢工,他说:“咱们都别去下窑了。狗日的窑主太狠心,几个月不给咱们发工资了。还让人活不活了。”
邵士喜说:“咱们胳膊能扭过大腿?”
白永祥说:“咋扭不过。人心齐,泰山移。”
邵士喜说:“福子哥,咱去还是不去?”
徐福说:“都不去,咱去干甚?睡,咱们可劲地睡,睡醒了再睡,还能省球一顿饭哩。”
邵士喜就挨着徐福躺下。跳蚤很多,咬得他翻来覆去。徐福被他翻身翻得很烦,就说:“你咋这么不经咬哩,难道你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邵士喜说:“我是饿得睡不着,肚里空空的,睡得不踏实。”
徐福说:“你还是不瞌睡,对了。你明日该请我喝酒了。一年喝你三四次,不多吧。”
邵士喜说:“不多,可是矿上老不开资,我拿啥请你喝,人家酒铺又不赊我。”
徐福笑了,说:“我不过说说而已,你到当真了。”徐福想起什么,又说:“我告你一句话,你可别对旁人说,八路军快来了。”
邵士喜说:“八路军来了,咱就不用受苦了。”
徐福想了想说:“那还是八路军来了好。”
李监工推开门进来,笑容可掬地样子说:“睡着呢,起来下窑吧,今天谁下窑,给谁发三天的工钱,在井口当场兑现。”
邵士喜说:“你们说话可是算数?”
李监工说:“当然算数,我说一句,你们可别听那些八路分子煽动。要长远些看,起来吧,下窑去吧。”
李监工走了,邵士喜说:“咱去还是不去,一天顶三天呢。”
徐福支起胳膊说:“你说去不去?”
邵士喜说:“胳膊扭不过大腿,我看还是去吧,三天的工钱呢。你给我垫得工具钱还没还你呢。”
徐福就起来穿裤子,“去就去吧,歇着也是白歇着,没人给一分钱。”
邵士喜穿了一半衣服犹豫了,说:“白永祥要说起来,咱咋说呢。我看还是等等看吧。”
徐福不屑地瞥他一眼“等甚,要去就去,现在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饿死谁苦了谁。”
邵士喜说:“这到是。”
他俩提着油灯和铁镐刚出门,就撞上了白永祥。白永祥瞪着他们说:“你俩咋这屁货,三天的工钱就让买哄了。”
徐福挡开他的手,说:“我们不能和你比,我们两天都不敢吃饱饭了。”
白永祥说:“还是的呀,我们为啥不敢吃饱,因为矿上不给咱发工资,咱们要和他们斗争。”
徐福说:“你斗吧,我俩可没力气斗哩,士喜子,咱走。”
邵士喜跟在徐福后面小跑。
白永祥点着他俩的背影,高声骂道:“你俩是屁货。”
邵士喜说:“白永祥不是八路军吧?”
徐福摆了一下头,说:“八路要他?”
李监工在井口等着人下井。
徐福走过去,向他伸过手去,“给钱?”
李监工又向山下望了望,说:“就你俩?”
邵士喜点点头。
李监工说:“就你俩,那就只能发给你们两天的工钱了。”
徐福瞪起了眼,说:“你们不能屙下再吃进去。”
李监工笑嘻嘻地坐下了,说:“你们再回去叫几个,叫一个给你们三块,咋样?”
徐福说:“你们说话和放屁一个样哩。士喜子,走,咱们回,咱不挣这三天的工钱了。”
李监工急忙起身拦住他,说:“好,好,我给你们三天的工钱,你们下井去吧。”说着掏出一把钞票塞在徐福的手里。
徐福分一半给邵士喜,说:“钱,是他妈的好东西,能哄得鬼推磨哩。”
他们正要走,李监工又对徐福招了招手,说:“你跟我到房里说句话。”
徐福便跟他进了井口那间窑洞。邵士喜站在那里数钱,他数了几次,都发现少一块钱。他不知道是李监工给少了,还是徐福点错了。他又点了一次,结果还是少一块钱,他便不点了,对着井口叹了一口气。
不一会,徐福出来了,徐福说:“下井吧,拿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受苦。”
邵士喜走在他后面,说:“福子哥,李监工给得咱是三天的工钱?”
徐福没好声地说:“不是三天,能给成你四天。”
邵士喜说:“李监工给你说啥来?”
徐福猫了腰走路,说:“也没说啥,牛厂长在里面坐着。”
邵士喜说:“我手里有钱了,今天出来我请你喝酒。”
徐福马上站住,回过身来拍了他一巴,说:“对,对,你还欠我的酒哩。”
他俩坐在酒铺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他俩在井下干了十五个小时。李监工说,你们要对得住这三天的工钱。
徐福喝酒的时候说:“咱今晚也不去下井了,这三天的工钱够咱吃几天了。”
邵士喜说:“不下就不下,刚才我看见咱一搭的人都不想和我说话哩。”
徐福把一碗酒喝下,抹抹嘴说:“对,咱不能为这几个臭钱让人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