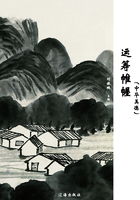这是煞月的最后一天,福恩掰着手指数着时日。事实上他每天都在默数,他很清楚今天就是了,这不会误,只是反复默数已经是他去不掉的习惯了。在黑色治所的日子,煞月二十八日面对着孤独寂寞,没有清晨鸟鸣,没有雨夜蛙声的谷口,蓝月亮格兰娜与白月亮露娜都被氤氲瘴气遮挡了光,周边也不会有别的活物,在左近的除了风声也只剩风声,若不是偶尔会从南神墙山脉透过来来几声惨淡的狼人嚎叫,他有时候还真怀疑这里是否是真实的世界。
不过这种封闭对福恩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每日例行的巡查结束之后,回到神殿的他也尚能找到些事情打发时间:通常他都会下腰靠在神祗与墙角间的空隙里,卧坐在一块不知历经多少年岁的连荒草原黄羊皮毯上,续上蜡烛,吃一点窖藏松饼和干酪,翻看业已泛黄的《识魔志》与记录《黑治闻录》,或者自己与自己来一把人魔军棋——这种游戏在大陆上流行已久,当然也是以上古时代人魔战争的故事为蓝图,而发展起来的多人回合制游戏——这种自娱自乐当然无法长期解闷,但是在守望的这一个月里也没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事情了。闲闷的时间勉强是过得下去了,只是思念在最后几天却来的越发急促。是最后一天了吧,福恩又数了一遍。可以回家了。“家”,他喃喃道,一幅宽广的草原就在眼前生长了出来,河川也奔流起来,小鸟开始鸣唱,猞猁在光洁的山岩上打着盹,接着出现的是农场与牲畜,村子里走过各色仓储房舍,然后就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阁楼,楼上烟囱在吞吐着温暖,楼前则辉映着两道温馨的影子,那是妻子艾莉与儿子埃克,他们在招手,福恩脸上也随之散开甜蜜的微笑,仿佛见到了艾莉正笑盈盈地端上热腾腾的新年烤鸡。当然还有她身后的囔囔缠着要鸡腿的小埃克。欸,埃克其实早已经是大孩子了,可不是?当年那么小的孩子不经意都16岁了。
“或许是时候了...”福恩思绪兜转,眼前的场景变换,一个英武高大的身影出现了,这是父亲的身躯,而在那伟岸身驱的阴影里,有一个懵懂少年,那是他自己,16岁的福恩。福恩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守望煞月,就算有父亲的陪伴与指引,孤独与害怕还是纷至沓来,不见日月星辰的漆黑,偶尔会有夹杂着猩红色或者姜黄尘烟的骤风突破雾气袭来,以及绵绵不绝的魔声祷叫,那暗夜中虚无影子的威慑压迫感...他清楚记得那幼小的精神真是时时刻刻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就是现在想起也仍会身上起冷汗;而且那种属于黑色治所特有的气息就是在回到居留地后好久也都一直裹挟在身上,挥之不去,那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东西,或许是感觉,无论一天洗多少次蒸汽浴都摆脱不了;父亲把它简单称为魔气,据传是太古精魔战争时代大量牺牲魔族与精灵的鲜血不断反复混合侵并挥发沉积,历数十万年,成为了黑治空气的一部分。虽然对其极为不舒服,但是也没见着任何问题,于是乎经历过数次守望反而倒也习惯了,他这会只担心埃克。
呜呜呜,风声渐起,浓郁的雾气及混杂的瘴气等在风的裹挟下开始了后退,漆黑随之也渐趋消弭,偶尔已经可以看到几丝外边的明光间断穿过。福恩知道封印阵正在恢复正常运转,只要过了这个正常运转周期间隙,四散的瘴气将被再次收容进黑治之中,大陆将重新获得生机。
这也被认作是大陆历的新年开始标志。
瘴气散得差不多了,福恩便步出古老的神殿,神殿前面是一截断崖,崖口高数千丈,而崖壁却异乎寻常的光滑,福恩记得第一次跟父亲到这里的时候,差点就没站稳滑下去,他当时越想逃离这深渊,却又不自主地走近它,仿佛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牵着自己的心神。“孩子,心志不坚定的话,深渊就会吞噬你。”福恩尚记得走在身前的父亲的话,而父亲的背影却早已经消失在遥远的时空里了。他遥遥脑袋,镇定心神,现在可还不是想过去的时候呢。
这会谷口上已经几乎一片清朗,而谷底则依然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在翻滚。黑色治所在东岸山脉的出口就在这谷口下面。福恩凝望这崖底的黑半响,深吸几口气,伸张肺腔,尝试放空对即将回家而感到兴奋不已的大脑。尽管守望过无数的煞月,可每次潜入瘴气却还是会让他感觉到强烈的窒息感。那就像是被人掐住脖子一样难以喘气,他得好好准备一下,尽管他需要的准备仅仅是精神上的放空。
良久,他深吸口气,不再做多想,平举双手,身体随重力前倾,倒向谷口,坠入黑暗,速度益趋益快,而在即将碰触谷底朽树之前,一双硕大的黑色翅膀兀地从他肩胛骨部位迅速伸展开来,强韧的双翼马上兜住了风,下降之势头瞬时立减,趁此一顿,福恩已调整好身姿,接着再奋力一挥把裹挟的空气向身后拨去,身子便借势往前而去,继而平稳展翅飞行。
“嘻嘻嘻,呼嘿嘿”,这惊悚的声音是无中生有,更层叠起伏接踵而至。“嘻嘻嘻嘻嘻”,下方混沌中阵阵戏谑声像是要愈演愈烈,却又忽远忽近地无故消散了,下一刻又从别处冒出,无所定位,无从定形。两侧干枯的死树仿佛也成了张牙舞爪的凶兽,泛着淡淡的紫芒,恶狠狠注视着穿行在它们之中的异类。“哼!”福恩不做理睬,振翅前驱。
魔声,这是父亲告诉他的。每当他巡查四方封印神殿途中,这个声音从来便不会缺席。至于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及其来源,却仍是谜团。前代守护者曾有认为魔声是来自于魔君的嘲笑,不过福恩却不认为,他不敢这么想,传说就连他的名字都会摄人心魂,让旅人发疯,动物癫狂。福恩尽力集中精神振翅飞行,却始终挥之不去那透入脊梁的嗤嗤魔笑声。亦可能是自己心底的污秽表现的放大吧,当然这是他自己给的解释,相对于那个邪恶名字的说法,福恩倒希望如此。
“呼!”翅膀挥动更频。不一会儿,福恩终于等到了远处的光点,那里是封印阵的入口节点,逾近,周遭的草木也逐渐由枯转黄,由黄转绿,甚至看起来都还有些蜉蝣在之中律动了;同时魔声也变得衰微,到最后挨近已趋于虚无。福恩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又一年成功活着回来了啊。他略苍白的面颊露出了一丝微笑,如果说世界上最美好的幸福是家庭,那么这座封印阵入口节点闪烁的些微荧光一定能排到第二,它可比太阳还能温暖他的心啊。
封印阵在一个很朴实的山洞里面,山洞入口不算大,只堪堪让福恩直身通过,洞内是一曲折斜向下的隙口,其上有前人修筑的石级和拉索,像一条大蛇一样,扭曲着身体匍匐在一众石笋钟乳之间;空间往内则是渐渐扩大,地面也趋于平缓,最后形成了一间巨大的石礼堂,封印阵就安静地的躺在礼堂中央的石头建筑群中,阵里的荧光此时正悠悠地在湿漉的洞窟里流溢着。而在洞窟更里的地方有着更明亮的光,那是来自美好的外面世界的光。
福恩站进封印阵上,四面古老石头建筑拱券与礼堂窟顶上的绿色精灵文字以及教宗国黄色的封印符号同时也辉映出亮眼的光芒,福恩那双硕大的黑翅膀此刻也自己收进了体内,身后最后的灰暗也只能被不甘心地隔绝在阵外起伏。他步入节点中央,枯叶败藓覆盖的石砖上登时亮起一道复杂的蓝色多级魔法阵,原本悠悠晃荡的绿色黄色荧光也越来越盛,流转加快,在魔法阵外像野蜂一样快速扰动。阵里魔法阵运行渐稳,而魔法之风愈大,荡涤吹开滞留的落叶尘埃,从脚端至头端,充盈着符文光芒在全身上下游弋,残留的瘴气也被悉数净化。福恩顿时一身轻松,心情也好转了些,特别在听到阵外更远处的寻春鸟令人愉悦的声音,以及看到由石头裂隙透露进来的点点翠色,刚刚神殿时候的浓郁思念又再被激发出来。“可不能辜负这新的一年”,他盯着一片被激荡起的柏树叶想道。
一会儿后,魔法阵光晕退散,四下便又恢复了宁静,荧光恢复了平静,依旧在悠悠游荡,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未发生。福恩此时也已脱下了夜巡时候的黑风衣,从壁龛里取出事先预备的呢子大衣穿上,整理好衣襟,崴崴颈脖,稍稍扭了扭腰,拉伸肢体,深吸了口气,从石礼堂走出,地上斑驳落叶草本铺成的松软长毯令他倍感舒适。“外面真好。”他感叹着。而脑子却早云游物外——他今年一定要跟艾莉跟埃克野游一番,在绿坪上野餐,在棕榈树下乘凉,再去听涧水淌淌,朝北神墙山脉呐喊,再听阵阵悠远的回声,继而卧看远处层云变幻,叆叇光景,定是美不胜收。福恩想那必定非常惬意。可惜去年因为要检查黑治东岸山脉沿线封印阵瘴气通透密度而没有去成,今年要再次失约,艾莉那埋怨的眼神,他可受不了。
福恩家在前哨村,顾名思义即是曾经作为哨所的居民地。村子离黑色治所东岸山脉封印阵很近,相对拉斯特城则还比较远。从他的祖辈的祖辈起就一直定居在这里,或许时间比那更久远也未知。凤凰王朝之时家中先祖与皇室交好,在拉斯特城也有着相当的地产,生活富裕无忧;然而随着凤凰王朝的突然覆灭,世袭的伯爵地位也被剥夺,家业也付之一炬,若不是有着守望者血脉的缘故,恐怕这个姓氏便早被贾斯蒂王朝埋葬在火鸟的灰烬里了。而煞月的守望,这个让先辈活下来的职责却也难堪幸运之名。也许是那双翅膀赋予的使命,每一代克莱曼斯都是唯一的煞月守护者,人们赞美他们的尽职却忘了他们本身也只是凡人,有血有肉的人,也想拥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生活。可守望已经融入了这个家族的血液,克莱曼斯这个姓氏的历史。福恩记得,父亲曾无数次感叹这个姓氏享有的光荣和崇高的职责,可是家族每代都仅有一个子嗣且全部都为男丁的事实在现在的福恩看来却不像是某种福祉,而更像一种胁迫,一种姓氏的苛责,甚至是诅咒。当然,年轻的福恩还没有过多时间思考这种命运的原因,就不得不独自走上了黑治的神殿,接替的正是在煞月守望里失踪的父亲。
福恩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日,拉斯特城领主格雷德侯爵骑着他高大的雷蒙青鬃马和他高贵的骑士们在这个偏僻山村突然出现,在村民敬畏的眼光下,格雷德在侍从护卫簇拥下缓步走到迷茫的自己身前,拔出鎏金宽剑正擎于胸前,目光如炬,宣读封册,任命自己为下一任煞月守望者。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听村民们说,骑士们找到的遗物只有那件黑色风衣,以及那本业已翻烂的《识魔志》。
福恩在守望之初也多次找寻过父亲下落,他不相信父亲会没有缘由地一去不归,肯定有一些事情在背后被隐瞒,他觉得父亲要活着肯定是留有一些不起眼的信息给自己的,但是从《识魔志》里的标号到书脊的压痕,乃至风衣的脱线,他都细细探查过,可都无法找到其中的关联,那个伟岸的背影仿佛就随着黑暗的瘴气淹没在恐怖的黑色治所当中了。他郁闷,他无助,在此期间,母亲也含着对丈夫的思念病逝。悲伤愤怒以及怨恨萦绕着年幼的守望者。如果不是艾莉走入了他的世界,福恩觉得自己怕是早误入歧途,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了。因此,他有时候甚至想这个世界有艾莉跟埃克就很足够了。可能就是这自私的想法让魔音愈来愈烈吧,不过他不在乎。
走出了东岸森林,眼前就是一片开阔的牧场,木栅栏里奶牛在低哞,养鸡场家禽在扑棱啼鸣。小溪潺潺滋润着大地,远方山峰上一点晕红。近处,一位早起的农夫正叉着腿斜躺在板车上,耷拉的四沿帽遮住眼睛,嘴里还衔着根藜草梗,正哼着小调晕乎,显然是还没有完全摆脱煞月的影响而在躲懒。福恩跟这里的农夫们都比较熟络,农闲时也经常聊天逗趣什么的,恰好今天心情也不赖,就想走近逗弄逗弄。
福恩靠近作势要动手挠他时,注意力却不经意落到农夫哼的调子上了,那调子音律变化短骤,转折突兀,充满了不安的感觉;福恩并不通懂音乐,可他是知道这曲子名字的——《文君归来》。曲里这个文君可不是什么五国一盟的最高统治者,这是独属于那个名字的称谓,这曲子便是古时候降服于那个名字的人类对他的敬颂。而时过境迁,六勇者时代都过去了两百多年的今天,一个普普通通本分的农民为什么要在新年第一天哼着如此避讳的曲子?福恩还在疑惑时,大地却突然一阵颤动,紧接着听到一声轰响,森林鸟群各自惊飞。那农夫一惊,哼的曲也中断了,从板车上滑落在地,四沿帽也落在一旁,伸手要取却发现了一旁面色严肃的福恩,一时惊讶而说不出话。福恩轻压手腕示意不要说话,而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不远处冒着白烟的农舍。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那里面发生了什么?换做平常他肯定是冲过去帮忙救人,但是风中一阵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却又让他僵在原地,他心脏开始加速,试图要否定自己器官的感知行为,可他做不到,这种气味他刚体验过一整个月呢。
他从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情况,很明显那间农舍里有着与黑色治所相似的味道,或者说它就是?风神保佑,别出事啊,这可是新年第一天呀!在福恩犹豫的时候,冒着白烟的屋舍再次垮塌了一半混砖土石墙,屋下朦朦胧能看到一个人影,似乎在挣扎着要逃离,可身体貌似受了伤,不听使唤地一瘸一拐往外挪动;此时房屋还在继续倾斜,显然是失去了承重而行将倒塌。“安...安娜!”那个农夫此时也回过了神,连滚带爬地试图冲过去,而失控的情绪却让他身体举步维艰,双腿发软。管不了太多,福恩甩下大衣,顾不得脱内衫就唤出了那对翅膀,双翅膀呈半握拳状态引开,包着两团空气就使劲朝身后拨去,身体接着呼啸着冲了出去。瞬时就已扑到了那人影身侧,就在福恩刚抱起昏厥在地的妇女后,身后的农舍再也绷不住,哗啦啦就倾泻了一地,阵阵浓烟夹杂着飞屑霎时扑面而来,福恩只来得及蜷曲翅膀护住自己跟怀里的妇女,就整个被包裹在烟雾里了。
烟雾里视线虽然受阻,但他的感官依然敏锐,他愈发清楚的感受到了那股气息,最让福恩惊恐的是那团气息不仅存在,而且还在慢慢移动,最后居然停留在自己背侧,这让他脊柱悚然,甚至比双羽上的塌方更有压力。那不是被瘴气侵袭而变得古怪的树等静物的味道,福恩已经闻得到那酸臭的味道。一个不详的想法虽然极力想掩饰却还是形成了——魔。接着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也酝酿成了——他要转身看清楚,是魔还是不是。
“我一定是疯了。”他想。二十多年的守望,从来都是在黑治的边缘地带活动,真正进入黑色治所腹地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那不是他的任务范围。但仅有的几次探寻到后来也都会被强大到扰乱心智的魔音逼回。而这一次,魔是否还存在的谜题他一定要揭开,这个机会现在正摆在他的眼前,他不能错过,不只是为了履行守望者的责任,也是为了那一点希望——父亲的失踪是否与之有关呢?
他小心地放下村妇,以左腿作轴,右脚踝拨动身子,双手撑地缓缓转身,他不敢肆意卸掉双羽上的木屑石块渣滓,只怕这响声会惊跑那东西。浓烟依然未褪去,而混沌中有一团黑影格外注目。福恩屏住呼吸,眯着眼,缓缓挥动翅膀鼓动着风吹散烟尘。渐渐明了,废墟的木椽,折断的木枋,遍地的石块,损毁的家具床榻渐次出现在眼前。越来越近了,不到半米,福恩心脏加速,耳鼓仿佛完全被高频抽搐的脉搏占据。就快了,那前蹄已经从烟里逐渐透露出来。黑色的,福恩心头微动,不是人的手,而是一只锋利的爪,也不是已知动物的。爪上棱突,指甲槽突,指关节脊刺的特征。福恩紧张得心跳飞快,可脑袋却条件反射一样自发高速运转起来,要去印证什么,他对这只爪子有印象,《识魔志》中的一些插画开始在大脑里播放,浏览筛选过滤。和目光中的爪子开始慢慢重叠吻合。福恩咽下一口唾沫,到这里心中已十分了然,这只是低等级的魔族或者亚成体魔,所以他继而萌发了又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能把这东西逮住。
而内心这一刻某个声音却表达出了抗拒——别,回头吧,就当一切未发生吧,回家吃新年大餐吧,跟阿莉埃克出去野游吧。这是自己的心声么?福恩踟蹰着,挥动的翅膀也缓下来。他虽大概已经明了真相,可若是没有最终看到面目,自己也是选择拒绝相信的,毕竟除了身居幽月谷精灵之森里面的那几位谁也没有见过活着的魔物。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本心从最初就十分抗拒,也可能是胆怯,传说中的万恶之源,杀人不眨眼的祸害就在眼前?他虽然巡查黑治多年,却也没真正遇到过什么邪恶的东西,最多是一些捕风捉影自己的幻想,而这个爪子可是实打实的真货。况且前代守护者也并没有捕捉之法流传下来,自己该如何应付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家传的那几招格斗技法以及剑法对付下蟊贼尚可,对付狼人都已经过载,何况魔呢?
血脉的亲情给予他的希望他无法就这么抹杀,守望者的职责也不许亵渎。而假如真相大白,贾斯蒂皇帝肯定会派人来调查,那样一来身为守望者的自己注定要为此事到处奔走,那么与艾莉、埃克的相聚时间就会变得寥寥无几,这也是他难以接受的。如何抉择?福恩这时发现自己居然那么卑微,多么弱小。
“乌鲁阿拉拉的啊,乞我卡萨嗯!!!”就在福恩恍惚的刹那,一阵莫名的摩擦声,或者说是怪叫声,毫无征兆地响起。那黑影仿佛受到惊吓,倏忽就收回了爪子窜走于烟尘之中,福恩反应过来抖擞翅膀,奋力吹尽最后余烟,烟雾散尽,满地残渣败絮,哪里还有魔的踪影。福恩瘫在原地,面朝天空,此刻天色已经大亮,汗水顺着他的脖颈向下淌,闪着剔透的光芒,福恩眼里无神,脑子空白。
“呜呜呜...”呜咽声顿起,福恩循声木然偏过头,在废墟边缘,那名叫杰克的农夫正跪倒地上,双手杵在地上盯着自己。两眼之中透出惊惧。
他在害怕。
害怕我?害怕我吗?福恩从未在这些农夫面前伸展过双翼,他们害怕也是自然。“嗨!别害怕,没事了。”福恩收起翅膀,向他挥挥手,勉强装出一副镇定的表情:“已经没事了,不用怕。”
农夫没有反应,仍然惊愕地看着他。福恩心下纳闷,回头看了看背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恐怖东西存在啊。
“伙计还记得我吧,我是福恩,福恩·克莱曼斯,我们一起玩过略特牌呢,已经没事了,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农夫不仅没有搭理他,眼里的恐慌反而在递增,膨胀,连福恩都清楚看到了他睁得滚圆的眼里升起的黑影,仿佛想撩开晶状体从眼睛里钻出来。那不是魔影。那切实是真实的影子。
他自己的影子。
“路西法尔”,农夫喃喃着伏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