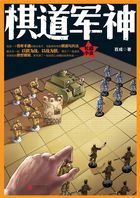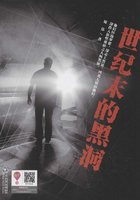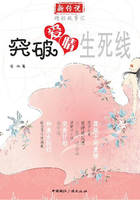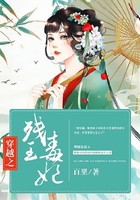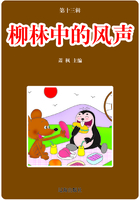《海浪》也许是弗吉尼亚·吴尔夫创作的九部小说最不容易读的一本书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遇到若干关乎可能性的问题;在阅读她此前此后的作品时,都不存在。譬如那些标明“某某说”的内容,怎么可能由人物口中道出;六个人物,又怎么可能聚在一起这样说话;此外,这些人物所“说”的部分与有关海浪的描写究竟是何关系,为什么能够相互穿插在一起,构成这么一种文本。这些问题不予解决,阅读障碍无以逾越。——正因为如此,《海浪》遭到站在小说立场的某些论家的批评,甚至斥为“失败之作”;当然同时也获得了另外一些论家的赞扬。然而即便对于后者来说,作品中前述可能性之存在,仍然有待于得到确认。
梅·弗里德曼作为不很欣赏《海浪》的一人,在《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中说:“每个人都似乎在对自己或没有听进去的旁听者讲话,而不是在交谈,……当读者随意打开书而看到‘伯纳德说’时,不免为之惊讶,因为下面紧接的话,恰恰是不想说出口的。”只消把《海浪》读上两三页,我们就会表示赞同,即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人在说话。大概正因为如此,论家称之为一种“内心独白”。可是弗里德曼对此也不认可:“独白本身过于独具一格,难以使人相信是内心独白。……思想的连接是严格符合逻辑的,措辞也符合英文的一般句法。”《海浪》不仅无法归并于一般小说,与意识流小说也有明显差异。那么作家所写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此前的《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其实已经存在,不过不大彰显罢了。我们无法相信克拉丽莎或拉姆齐夫人置身某一情景之中,真的就是那般想法;作家实际上并未直接描写人物的意识活动,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所丰富,有所升华,其间又与人物所处环境多所呼应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之为“诗化的心理分析”最为恰当。詹·哈夫雷说:“弗吉尼亚·吴尔夫需要的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必须来自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声音,但同时又能意味着把观察和叙述当作一种创造而不是当作一种传达来加以戏剧化。”(《弗吉尼亚·吴尔夫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再现“生活本身”的艺术》)正因为叙述者身兼人物内心世界的观察者和分析者,观察、分析与叙述糅杂在一起,所叙述的内容也就不妨有别于人物自己所思所感,读者不至于太不习惯。于是有如哈夫雷所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意识,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创造出秩序,从而说明了它自己,而这个叙述者的意识,似乎便是意识本身。”无论是克拉丽莎,还是拉姆齐夫人,最终都是吴尔夫自己。
到了写《海浪》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人物的内心世界仍然被观察,被分析,并被叙述出来,但是原来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也就是那个观察、分析的人消失了。上述观察、分析仍然是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方式,不过这一工作改由人物自己承担了。作品中标以“某某说”的,就是所观察、分析,并被叙述出来的内容。人物也许相对趋近于自身立场,但至少观察、分析的方式还是吴尔夫式的,亦如哈夫雷所说:“这个叙述者的声音以消融在它所创造的其他人物的声音中而著称,特别是消融在内心独白之中。”弗里德曼曾批评道:“六个人物若是离开了他们的抒情独白,就失去了生命。”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通过这种独白获得了生命。
哈夫雷说:“从外表上看来似乎有两种真实(按指‘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但最后呈现为只有一种真实,因为它们是由同一个创造者以同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即从个人的准则和需要中有选择地创造出来的——同样,我认为,在其他场合,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叙述者也都是创造者,而不是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报道者。”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人物丰富、升华了的意识活动,正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新的真实,讲得确切一点,一种新的主观真实。吴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真正贡献——尤其是区别于乔依斯、福克纳之处——即在于此。
这种创造出来的主观真实,在上述两本小说中是被置诸客观真实——对克拉丽莎来说,是她的晚会;对拉姆齐夫人来说,是她在海滨别墅的生活——之中,《海浪》却又有所不同。客观真实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一种创造出来的真实取代了它。这就是伯纳德、苏珊、罗达、奈维尔、珍尼和路易怎么会在一起“说”的原因。莫洛亚在《吴尔夫评传》中把《海浪》别致地称为“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地念出词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不过舞台并非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处,它发生于一个新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交流方式,并不等同于在现实世界中的交流方式。所以这些“某某说”,虽然偶尔能被其他人听到,甚至形成对话,更多的时候则近乎自言自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把它叫做“内心独白”。——这个“独”字至为关键,伯纳德等拥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比拟的独立性。他们所“说”的常常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事;但是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彼此距离非常遥远。
这可以被看做是超越每个人物的主观真实之上,并为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主观真实。然而它不仅仅是由六个“声音”——彼此多半听不到的声音——所构成的。娜·亚·索约洛娃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色彩趋于黯淡的世界》中说:“作者为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把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的意识进化过程显示出来。意识的每一阶段,都是与自然或宇宙的某一特定状态相应的,而从早晨到黄昏波谲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又作为每一个意识进化阶段的前导。”有关海浪的描写具有象征意义,大概无可置疑;然而就像这里所揭示的,如此“相应”,又复“前导”,似乎其间还有一种较之象征更其密切的关系。弗里德曼说:“描写部分并不为独白提供必要的外界背景。”显然并非如此;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从早晨到黄昏波谲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理解为六个“声音”发生的现实意义上的外界背景,肯定也是不对的。
小说开头,有关海浪及海滨花园的一番描写之后,六个人开始了他们的“说”;所说的都是对于客观真实的感受,——后来伯纳德回顾道:“园子那边是海。我瞧见了某种发亮的东西……”正与最初他“说”的“我看见一个圆圈,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一圈光晕,不住晃动”相对应。这提示我们,描写部分与内心独白共同起始于客观真实中某一具体时刻,具体环境——这也是除内心独白时而涉及的有关人物经历的内容外,《海浪》惟一与客观真实发生联系之处。此后上述两种成分就分别按照它们各自的时间逻辑向后延续,对于海浪来说,是从早晨到黄昏的一天;对于伯纳德等六个人物来说,是几十年,他们活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时间自身的顺序得到严格遵循,无论海浪的变化,还是人物的意识,都是朝向未来的。只是到了最后一部分,伯纳德“说”:“现在来总结一下吧。”人物改为转身面对既往的岁月。如果单看内心独白部分,我们会觉得由这些“某某说”组成的新的真实,只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空间,在时间上仍然属于现实世界。当它们与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相互穿插,形成现在这种文本之后,就完全不同了。海浪是作家所创造的新的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确为内心独白提供了“必要的外界背景”,但同样是创造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地讲,六个人物的几十年,相当于海浪的一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时间关系。人物的内心独白发生于其中,或者说,人物的命运发生于其中。这样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才是一种全新的时空关系,它打通了原来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界限,把它们一并囊括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浪》较之《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的确大大发展了一步。如果说在那两部小说中,客观真实对于作家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有可能造成一种羁绊——按照吴尔夫自己的逻辑,的确如此;虽然换种看法,也许会说它们正是相得益彰——的话,现在她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状态。回过头去看她在《本涅特先生与布朗太太》中说的:“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在《海浪》中,她已经把这一概念改造得不仅与她的前辈威尔斯、本涅特和高尔斯华绥等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且与她自己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所演绎的也相去甚远。《海浪》是吴尔夫的一部义无反顾之作,甚至对她自己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吴尔夫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任何既有的可能性的可能性。或者如吉·杜南在《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的信条》中所说:“吴尔夫的信条就是祛除不可能性。”
在上述框架之下去理解“海浪”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恐怕就不止是一种对应关系了。林·戈登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把这种描写与《到灯塔去》第二部“时过境迁”联系起来,是独具只眼的。海浪,海滨花园,以及花园中的小屋,种种景色变化,显然处于异常细微而又不动声色的观察——某些地方甚至使我们联想到后来罗伯-格里耶式的纯客观描写——之中,那么谁在观察着这一切呢。类似的眼光我们在上述“时过境迁”中见过。戈登说:“《海浪》一开始就像造物者一样,写了一个无人的宇宙,它后来就有了居住者。”“时过境迁”具有同样性质,虽然它只是人们离去——包括死亡——和剩余的人归来的一个间隙而已。《到灯塔去》中这一部与前后两部的对比,和《海浪》中有关海浪的描写与“内心独白”的对比不无类似之处。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人之存在与否的话,后者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极向——这正是吴尔夫所创造的新的真实或新的时空关系的两极。一端属于造物的,自然的;另一端则是人自己。也就是说,在对应关系之上,还有一种相互观照的关系: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映衬着伯纳德等人的存在;伯纳德等人的内心独白,则有一个天长地久、生生不息的背景。
关于《海浪》中六个人物的相互关系,论家多有论述。小说临近末尾处,伯纳德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对理解此点有所助益:
“如今我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一直在谈到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等于是他们全体合而为一么?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突出的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坐在这儿。不过如今波西弗早已死了,罗达也已死了;我们被彼此分开;我们并不聚集在这儿。可是我并没找到任何能把我们分开的障碍。我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当我这会儿在说这些话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你’。我们看得那么重的所谓彼此的区别,我们那么热心维护的所谓个人人格,如今都抛开了。”
如此说来,“彼此的区别”,“个人人格”,都曾经存在;不过“如今”在伯纳德这儿“合而为一”,而这个伯纳德并不同于与奈维尔等并列的伯纳德。这是小说最后一部分与前八个部分之间的一种发展,一种变化;当然同时还伴随着别的发展变化,即如此时汇聚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或许还应加上虽未发出“声音”,却为所有“声音”所关注的波西弗——的伯纳德所“说”:“在我身上也涌起了浪潮。它在逐渐扩大,高高耸起。”这是另外一种“合而为一”,发生于“我”与海浪之间;而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首先由六个“声音”,继而由有关海浪的描写和内心独白所组成——最终完成于此。在此之前,我们恐怕还不能不承认六个“声音”的相对独立性,有六个生命的确活在其中;虽然体现为内心独白的不同历程,而又为作者事先确定的各自的性格基调所导向而已。
这里伯纳德最终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路易以及波西弗“合而为一”,说来与《达洛维太太》中克拉丽莎最终将塞普蒂莫斯与她自己“合而为一”,以及《到灯塔去》中莉莉·布里斯科和其他活下来的人最终将拉姆齐夫人与他们“合而为一”多少相仿。都体现了吴尔夫本人对于生命的深切感悟。对于作家来说,或许正是全部寄托所在。杜南说:“也许因为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结尾,要有一个限度,所以作家给某些读者以失败的感觉。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想把对世界的体验和盘托出,并把这个任务、这种职责赋予写作;成功之处,就在于让写作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失败之处呢,就在于小说的必然性,结束的必然性,作品总得有一个结尾,因为要有一个形式,外在于书的主题的形式。”的确吴尔夫诗化的心理分析——《海浪》中的内心独白仍可归属此类——最具魅力之处,主要还在对于过程灵动而饱满的揭示,而这一过程似乎并无自行终了和归为任何结论的趋势;然而即便结尾的设置限制或简化了这种揭示,对于吴尔夫来说,仍然非这样结尾不可。
止庵
二〇〇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