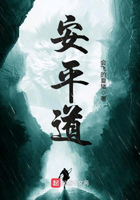落于宁河一处大弯的宁水城,可谓是陇南地头等的行商大城,虽然宁水城的大小只不过稍稍强过一些上等城池,但是宁水城的财富的流量可是陇南地首屈一指的。就好比在渔期时,条条河渠汇成大江,蹲在河渠边还是守在大江下游?那答案是肯定的,死盯着江河交汇处,那里的肥鱼肥虾可是会争着往船里蹦跶啊,而宁水城就是类似于江河交汇处的这么一个地方,河有宁河,山有凉山,整个陇南地,哪条商路通不到宁水城?
宁水罗家,整个陇南大名鼎鼎的行商大家家主罗问庭,二十年前也只不过是个顽劣青年,二十岁时在外游历了一番,回来时便在宁水城做了生意,谁能想到,这小子还真成了,原本进城时一人一马,到后来富甲宁水城,使罗家短短二十年便成为了宁水城的头三家之一,而宁水城的百姓落日闲聊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个罗家,谈起这罗家也总是唏嘘不已,较年长些的更是亲眼看着这罗家从这宁水城中掘地而起。
此时罗家府邸中,罗家家主与大小管事齐聚在前堂中,罗问庭端坐在主座中,一众管事分则坐在客席,个个面色凝重。
这位罗家家主看上去,年岁不过近半百,面相宽厚,双眼有些细小,上嘴皮外翻,但却鼻挺梁高,同样一把年纪,虽然比不得周镇那般英姿勃发,却也算是个耐看的老头子。
罗问庭端起檀木桌上的一碗酸梅汤,牛饮半碗后,砸吧砸吧嘴,从袖中摸出一条绣有小桃心的粉色手帕,拭去嘴角的水渍,做罢后,瞅了瞅座下那一张张紧锁这眉头的脸,不禁笑出了声。
“瞧瞧你们,摆着张臭了脸坐的挺端正,一个个的像是像是被捏着尾巴的猫子。”说完,罗问庭又是哈哈的笑了两声,继续说到。
“不就是商队被凉山那帮不成气候的贼娃子给抢了嘛,赶明儿早让罗立带着人去把货要回来,顺便把那一窝小贼也宰了,说说你们,做生意的时候老底都赔出去了,眉头都不皱一下,今儿遇到几个不讲理的贼匪就把你们收拾懵了?”说罢,手又缓缓伸向剩余半碗的酸梅汤,准备一饮而尽。
这时,一个身穿褐色窄袖长袍的中年男子站起了身,朝着罗问庭行了一礼,开口说道:“家主,被抢的那个商队,是从勾云城来的。”
鸦雀无声中,只瞧见那装有碎冰与酸梅汤的瓷碗摔在了地上,中年男子抬头一看,堂中哪还有罗问庭的身影。
这时,一道靓丽的人影跳进人们的视线中,娇声喝道:“都愣着干嘛?该抄家伙的抄家伙,我爹一把年纪了,还要让他一个人上凉山收拾那帮贼匪啊?”
当年,罗问庭一人一马进城时,还提了一杆铁枪。
凉山
许姓少年拎着鼓鼓囊囊的麻布袋子走到了一处偏僻的砖房前,相较于其他的屋舍,这间便显得简陋寒酸了许多,整间屋子只有一扇门上了锁的木门,还有人头差不多大小的窗子,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还不时有些虫鼠蹿过,许姓少年皱了皱眉,从腰间取下了钥匙,小心翼翼的插入锁芯,还没等扭动钥匙,沉重的铁锁便砸在了地上,带起阵阵尘土。
等蹲下吹开尘土仔细瞧了瞧,许姓少年满头黑线,这铁锁压根儿就是个坏锁,好歹也是一群占山为王的贼匪,怎么连关个人都如此粗心大意,万一这人若是跑了出去,将寨子的情况报给城府,这不就麻烦大了吗?
此时的少年想到这,有些后悔了,之前只顾着上了山能有快活日子,可这毕竟做的不是什么善事,万一哪天触碰了谁的底线,寨子被推了,那可真得把命得交出去。
毕竟还是个年轻娃娃,也就喘个气儿的功夫,就咬了咬牙,下了狠心。这山都上了,也被赐了山位,再瞻前顾后的哪还是个拿命搏快活的大丈夫,一番自勉后,许姓少年拎起麻布袋子,挺直了腰杆走进了砖房。
这人才刚踏进屋子,便慌忙从里头跳了出来,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拎这麻布袋子,脸色难看的再次打量着面前的破旧砖房,“这他娘的到底是牢房还是茅房,就算关畜生的屋子也没有这么恶心的。”从许姓少年从里头跳出来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去了,即便刀架在脖子上。
可看着手上的麻布袋子,少年又犯起了难,自己刚被赐了山位,这才是交代了第一个活儿,总不能这点事都办不成,这一来肯定进不了几位当家的眼,若自己一直是个小喽啰不能出头,张老赖和自个儿可又得像之前那般受尽欺负。可是,看了看里头一片漆黑的砖房,那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少年在门口踌躇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最后紧紧捂着鼻子,右臂大力一甩,将麻布袋扔了进去,手脚麻利儿的关上门,挂上铁索后,逃命似的飞奔离去。
除去窗口处照射进来的微弱阳光,砖房内的其余地方基本是伸手不见五指,房内一处黑暗的角落里,时不时传出细微的鼾声,若是耳力稍差些,哪里能感觉到房内的角落会有其他的活物,当房门被打开时,这细小的鼾声戛然而止,阳光从门外倾泻而入,也只不过照亮了一小半房间。
好像有人尝试着进入这间屋舍,却又被恶臭逼了出去,不一会便从门外扔进来半斤重的麻布袋子后,门便被重重的关上,屋舍内又重新归于黑暗,隐约听见门再次被挂上锁,脚步声迅速远去后,角落里松了一口气,随后一道人影从黑暗中冲了出来,趴在麻布袋子前,手脚颤抖又急不可耐的打开麻布袋,手忙脚乱中却一直打不开系的很死的绳结,这人喘着粗气,时不时发出痛苦的低吼,最后竟然用嘴去撕咬,随着麻布袋被扯开的声音,口齿满是鲜血也毫不在乎,如同在泔水槽边翻找吃食的饿狗一般疯狂。
终于,抓到了一把带着灰粉的碎草叶,小心翼翼的放在一块烂布中,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杆铜制的烟斗,轻轻的在地上磕了磕后,便将粗布中的碎草叶一点一点填进槽内,做罢这一切后,一手将槽口放在一块大黑石旁,一手拿起一块略小的石块像大黑石砸去。
随着沉闷的声响带出的火星,点燃了烟斗槽中的碎草叶后,便立马轻轻对着烟草吹着热气,不一会碎草叶便完全着了起来,发出通红的火光。
这人扯过一张草垫,躺了上去伸展开来,一手枕着头,一手拿着烟斗猛吸一口,小腹也跟着慢慢收缩,又随着烟气呼出而恢复。这一吞一吐使其不禁舒服的叫出声,整个人如同飞至云端之外,之前浑身像是万千蚁虫叮咬的痒痛之感全然消去,骨头更是酥麻轻爽,飘飘欲仙。
这座破旧的砖房所落在一处荒林中,杂草横生,树木交错,并没有什么林中仙境的美感,甚至阳光也被遮蔽了大半,只有几缕残光透过枝叶,留下了几分光亮,不大的窗洞时不时飘出淡淡的烟雾,远观望去,却是悲伤与孤独在弥漫。
秦山山崖边的一处岩突上,一个年轻男子跪向大雁飞来的地方,双目微红,嘴唇微微颤抖,太阳在天际缓缓沉下,留下的余晖烧红了浮云,红霞映照在男子的脸颊上,反射出晶莹的光芒,男子身后不远处伫立着一位貌美女子,女子身着宽袖蓝边服,鹅蛋脸上有着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琼鼻精致,樱唇微张,像是荷塘中的水仙,清雅高贵。
女子轻步走到年轻男人身后,伸出双臂轻轻抱住了浑身僵硬的男人,将下巴轻放在其肩上,而男人依旧呆滞的望着远方泪流满面。
“阿瑶,秦山刀宗没了,周家也没了,母亲不在了,父亲也不在了,叔公们也走了,我说过此次事罢要带你去见见他们,去见见我的父母亲人,我还没有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我还没有和他们聊聊这几年我的经历,我还没有和他们说你是个多好的姑娘,他们就不在了,那是我的父母亲人啊,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男人一字一句哽咽的说道,从开始眼泪默默流淌,到后来的放声哭喊,“是我害了宗门,是我害了周家,我该死啊,我就应该留在那个地方和他们一起死啊,为什么让我活着,阿瑶你告诉我为什么啊,我活了二十年,修行十五载,我却连我的家都护不住,我生来何用,生来何用...”
女子亦是满面清泪,抱着男人的双臂更紧了些,声音颤抖,“青松,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蓝光瑶自相识这个男人以来,从未见过他的泪水,即使当初两宗覆灭,这个男人也依旧将眼泪逼了回去,可这次,这个男人彻彻底底的崩溃了,当初站在这里如同猛虎出世般长啸的男人,如今,只不过是跪在这里,像是丧了家的幼犬,放声哀嚎。
太阳落了,余晖如同鲜血一般染红了天空,最终无力沉下,黑暗随之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