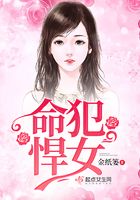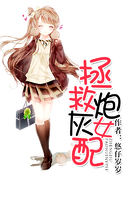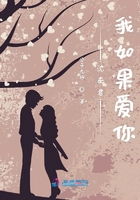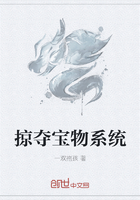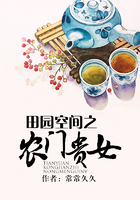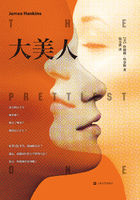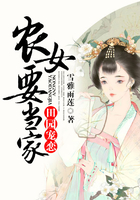再看看车窗外,注写着高甲戏班出处的幕头帘持续的被海风抚着。
她的正上方,那么远又那么近的云层里浅藏着刚露新的芽月,弯钩钩的悬吊着,即便露白的不多,但搁在“打捕村”的夜空,还是显得比较的明与柔,呼应着天底下这闹腾小戏台溢出的光亮。
照的戏台下的“老老织布”也打起哈欠泛起了困,发沉的头壳不时不定的往下、往左、往右掉,一旁的“老织布”往她在腿上披绒毯时把哈欠接了过来自己也打上了。
这高低远近的动静交融,明暗交辉,让“老织布们”都略显出了祥和。
“打捕村”闲时常有的慵懒与自在露出来了些。
“噼里啪啦...”
不过不懂阿喂他才不懂那么些个气氛。
什么时干什么事,到点了就夹起嘴里的烟头点着了条短炮,把老人吓的睁开了眼,也把车里的司机振醒了。
这第一遍短炮的意思,按着“打捕村”的老例是高甲戏文已唱过大半,车里的来人也懂,他的气质由表及里也透着股土生土长的地瓜味,自然是门清这十里八乡的规矩,他敢连闹钟都不预设一个,就知道得有这么一遍遍短炮来催他起来揽活。
也不怕白跑一趟,表哥兼师傅都传授了:
开放二胎都半年久了,今天“打捕村”这个农历酬神的日子又叠挨着新历的清明假日,对他们这些个干保媒拉纤的也算是双喜叠加的好日子,村里高高低低或穷或富,怎么都得回来,新娘轿扛到,才想要绑脚的人(方言,临时抱佛脚)肯定也会有,盯住来拜拜母堆里出公的,八九不离十准出单。
来人抻展开身体,咧嘴挤眼,点了根提神的烟,边抽边解锁手机,点听了未读的语讯:
“王士,你一定记住了,如果看到有打捕来捧贡碗的,肯定是屎到才挖坑的(方言,临时抱佛脚),最有门,咬住咯”
还是那些车轱辘话,滚来滚去的,压的来人心头上长出了些厌烦,他就想表哥怎么就对自己第一次单干那么的不放心。
啐掉歪咧嘴角上还剩的大半根烟,下了车,再用阿喂同款的旅游鞋碾灭,像是透过鞋尖往上散气,也像在为自己打气。
手机关了机,帽檐压了低,依次检查了几个口袋里的东西,尤其是怀里揣着的硬家伙,摆弄调整了下位置,似乎在他的心里,又明晃晃的反了那么好几下白光。那可是出状况时用来保命的。
一连贯熟悉的动作后,来人开始走回戏台。
此时台下的村民可渐次多了起来,并非戏好(hǎo)或好(hào)戏。戏文一近尾声,“打捕村”里轮值上贡酬神的人家掐算着时间,都纷纷拢聚到庙前台下来等着捧撤贡碗。
来人就躲在不太亮的高处搜巡着猎物,一个个,一遍遍的,精神头很足。
跟戏台子隔着几排几列高低错落的楼或厝。一个人也沿着厝墙根下朝戏台走来,柔美月光让他也不至于太摸黑。
他叫张齐斌:“打捕村”庞大曲江传人中某一支不起眼的血脉,还亮着的丁(灯),独苗,一个娴熟的打捕手,一个被茶米油盐拿住的“讨海兄”。
下有小上有老的年纪,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女儿,一个中晚年居孀的阿母,没能让父亲看到自家的香火得已延续,是张齐斌活在村里人眼里最大的不该,父亲是新逝的,所以他的愧疚感被岁月冲淡的并不多。
放在“打捕村”的标准里,他的后半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没非得要发财,但似乎一定要生个“丁”,诸如今晚“普度”之类的活动,全村的社交集中爆发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日常的围剿。
他只套了身掉了色的松垮球服就出了家门,手胳膊腿肚子都袒露在外蹭着凉,看得出是靠卖力气讨生活的人,都奔四的人了,体型还是天然的好,高大,壮硕,匀称。
配的上“打捕村”老话说的:“站起来如东西塔,躺下去如洛阳桥”,再加上海风烈日搭配着熏烤出来的麦色皮肤,连蚊虫都喜欢,也追着烦。
张齐斌的眉心天然的拧着,上扬的眉梢,搭配着一对炯炯的凤目,只要不笑正常办公,看起来就显凶。
平辈人里,谙他脾气的,敬着喊他”牛头斌“,认准的事,按部就班,推不动,拉不回;长辈人里疼着喊他“盖头斌”,只凭他从小到大,一犯起牛脾气,就拉下个脸,像对苍蝇眼被龙眼壳盖住,没头没脑的乱撞,不听劝。
当然,更多的时候,谁说话情绪都不上头了,人们只是喊他“阿斌”。
不管是阿斌、牛头斌、还是盖头斌吧,反正他就是有把倔脾气,这种天资,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得到过发挥,那时的他混(hún)过,在他们镇上的那所破中学里讲话跟校长似的。
加上后来又没怎么读书,到现在心理多少还是藏着些棱角。
晚上他手里提溜着准备装贡碗的竹篮,与自己的男人味极不般配。粗号大脚掌上挂着的人字拖“啪”“啪”一响接一响的,虽说远处有戏文锣鼓点的声响垫着底,张齐斌扎实的吨位踩碾过土路上的碎石子,还是很突出的沙沙出响。
阿斌来的算晚,完全一副“提竹篮,假烧金”的讨债模样,要不是家中阿母催逼的紧,唠叨的太过,乘上老婆的当仁不让,两个巴掌对拍响。
他打死不会真的应了差遣,来这更闹腾的戏台跟前躲清静。虽然他也希望能再生个“打捕”续下香火,可还远不至于信服阿母嘴里絮叨的老话:“有食有行气,有烧金就有保庇”,唯心的那一套。
张齐斌自打勉强履行完了义务的教育,便再没来这庙台周遭边上蹿下跳过。毕竟初中结业后,文化不长自尊心跟个头却一并见长,就没好意思再来当孩子王。
他甩摆着竹篮,硬着头皮,循着曲响的方位往戏台踱步。动静越发明显了。
临到了,经转一条幽暗村巷,再绕个角便是闹热的戏台。
阿斌快出巷时,声响动静随着光亮一起漫散过来立刻影响到了他,烦躁的心情顿时有了些许变化。
转出角,新修葺的宫庙戏台柳暗花明地摆在他眼前,搭配着灯光看,他的情绪倒也有些新鲜感。
不过这点情绪上的波动还远不足以把他带去光照太清楚的地方,他只挑了个光亮衰减厉害的阴暗偏僻处杵着:保证戏台上的热闹能看见,台下站着坐着的“织布”和“老织布”们也能多少盯防着点就好。
阿斌查了查眼前,果然传统的老俗旧礼还得是由这些妇女们来发落(方言,落实,执行),妇女婆子们依旧是撑起“打捕村”半边天的坚强娘子军,没见半个大老爷们的影。
如果实在想要从性别上找点衡权,顶多能见到三两跑窜的小崽子们是“打捕”。对了,实在还不死心,那宫庙前还能找到个不懂阿喂充数,他正踱来踱去地像在维护着什么。
所以阿斌得躲啊!
他怕,怕刚从家里躲出来的清静,一走到“织布”堆里又得被她们,没话找话地关心,盘问。
这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会有的套瓷拉近没有错,可一旦冲进“织布”堆里,顶着车轮式的关心,十嘴九**,连说话带放屁的,换了谁都得是变成闹心。
这可比干下一天的粗重活来的累,阿斌他想,光看那老的坐着的不算,年富力强的“织布”可围着二三十个呢,这他们家三千年一次海涨,如此隆重地派出个盛年男丁来,不得是丢给他们话柄啊。
阿斌心里这点逻辑提防还是有的,这些“老织布”们都活成精了,看他都来了,不得围上来嚼嚼舌根子。
不知怎么的,阿斌脑壳里又回旋起阿母刚还絮叨的话:
“你自己去庙里拜拜,有食有行气,有烧金就有保庇(方言,俗语),心要诚些!“,他不免有些头胀。
阿斌即便是躲在暗处里,可躲过了明枪,没闪过暗箭,还是成了旧小面司机的靶子。他右手的大拇哥划着手机,左手二拇哥抠挖着鼻孔,猝不及防就被暗处里冒出的来人递塞了根烟:
“大哥,点一支?”
“你谁啊?”
阿斌有点小惊,撤了撤身子,拿斜眼搭了搭比自己矮不少的来人,
“大晚上的还戴帽子?”
“大哥我秃头”
来人语气断续中带着点难为情。
阿斌听着像是真的。两人对视了一眼,看来人做势要真脱帽:
“诶!带着吧,带着吧”他心里想着,这么年轻就秃头,也不知道娶到老婆没。
“我不认识你啊?你来我们村干嘛?”阿斌继续审。
“你们村不是热闹嘛,我来做人客,喝两杯。”
边说着,烟跟火机都已架好,只等阿斌接茬,点火。
“90后吧?也爱看戏!”
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在说,他们八零后都不看了。
阿斌一丢下篮子,唇瓣刚含上烟嘴,火机口里的焰“啪”的就蹿了上来。
“大哥,钱难赚,来拜拜求个财嘛!”
说着来人就跟阿斌一并吞云吐雾了起来。
“大哥你手机能借我打个电话吗?我手机没电了”
他瞟了瞟阿斌感觉对了,再进个一步,边说边给他展示着手机证明着自己的话。
拿到手机拨出去后,放到耳边听清了是“对不起,你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就递还给了阿斌。
“关机了。”
来人露出的微笑很开。
“你是赚什么吃的?”
既然求财嘛,阿斌想着就随意的接着话头问了问。
“大哥,也不怕你笑话”
来人递给了阿斌一张名片。
他伸手去接,可来人就是不撒手。
“哧!看不起我?”
牛头斌嘴角全往一边上撇,他上了点情绪说话就容易这样,紧接着拿眼瞪这个秃头矮个。
“哥,你先别急”
来人继续笑脸相迎,让阿斌用手机的光提亮了纸片,只读出:
“未哺先知”几个字。
阿斌看着那纸片上的底案图纹,倒像是母婴用品相关的,毕竟自己也养大了个5岁多的小情人,虽说没什么文化,但这点常识还能懂。
“不就卖奶粉?还怕人知道啊?”
来人踩灭烟头,踮起脚尖,贴到阿斌的耳根旁,也不管他的闪躲,继续贴上去搭桥耳语......
戏台上,刚好锣更紧、鼓更密、曲更高,似乎在为他们的悄悄话打着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