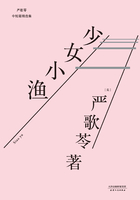她睡得不好;从一点半,杰米离开,她拖拖拉拉地上了床,到七点,最后她决定起来泡咖啡为止,她睡得断断续续,不时惊醒睁开眼睛盯着昏暗处,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再溜回兴奋又激动的梦境里。她喝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咖啡——他们本来就打算在路上吃早餐——这会儿除非她想早点梳妆打扮,其实根本无事可做。她洗了咖啡杯,铺了床,仔细挑选待会儿要穿的衣服,没来由地担心窗外是不是好天气。她坐下看书,又觉得不如给她姐姐写封信,于是她开始用那手漂亮的字体写着:“最亲爱的安妮,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听起来是不是怪可笑的?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之后,你会觉得更加的离奇……”
她坐在那里,握着笔,犹豫着下一句该怎么写,她读着写好的那几行,把信撕了。她走到窗口,外面毫无争议地是一个好天气。她忽然觉得不该穿那件蓝色丝绸洋装,太朴素了,几乎有些老气,她应该穿一些娇柔的、女性化的衣裳。她焦躁地翻着衣橱,对着去年夏天穿过的一件印花洋装犹豫了一会儿:好像稍嫌年轻了,而且还有一个皱褶式的领口,现在穿印花洋装似乎过早,可还是……
她把两件洋装并排挂在橱门上,打开小置物柜上方密闭的玻璃门,那是她的小厨房。她在咖啡壶底下点着炉火,再走到窗口,阳光普照。咖啡壶响了,她转回来把咖啡倒进一只干净的杯子里。再不赶快吃一些“实在的东西”我会头痛,她想着。又是咖啡又是香烟,根本不是正式的早餐。结婚的大日子头痛,她去浴室的镜橱里拿了一盒阿司匹林,把药盒塞进蓝色的包包里。如果要穿那件印花洋装,她应该换褐色的包包,可是她唯一的褐色包包太破旧了。她无所适从地站在那里,对着蓝色包包和印花洋装,看过来又看过去,她放下包包,端着咖啡走到窗户边坐下,一面喝咖啡,一面朝着这个只有一间房的公寓仔细地看了一圈。今天晚上他们预计要回到这里,所有的一切必须正确无误。她忽然一惊,想起忘了换上干净的床单。洗好的衣物刚送回来,她从衣橱顶的架子上取下干净的被单和枕套,她的动作很快,也不去多想为什么要换床单。床是简单的沙发床,加了罩子看起来就像一张长沙发,所以谁也看不出她换过了干净的床单。她把原来的旧床单和枕套带进浴室,塞进洗衣篮里,顺手连浴巾也一并塞进去,再把干净的浴巾挂上架子。等她忙完,咖啡冷掉了,她照喝不误。
她看钟,发现已经过了九点,她开始加快速度。洗完澡,用了一条干净的浴巾,她把这条浴巾放进洗衣篮,再换上一条干净的。她对穿着很讲究,她的内衣都很干净,而且大部分是新的。她把前一天穿过的衣物,包括睡袍在内,通通放进洗衣篮里。准备装扮的时候,她站在橱门前面犹豫了。蓝色的洋装很得体,很清新,合身又好看,只是她跟杰米在一起穿过好几次了,婚礼这天再穿它简直毫无新鲜感。印花的洋装非常漂亮,对杰米来说也很有新鲜感,只是这个季节穿它似乎太早了。最后她想,这是我结婚的日子,我高兴怎么穿就怎么穿,她从衣架取下了那件印花洋装。洋装一套上身,感觉新鲜又明亮,对着镜子,她才注意到颈圈上的皱褶把脖子包得太紧,超宽的裙摆更无疑是为小女孩而设计,专门给一个走起路来扭腰摆臀,又跳又转的女孩穿的。她照着镜子嫌恶地想,就好像我是为了他才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他会以为因为他要娶我,我才拼命地想让自己显得更年轻。她一把扯下印花洋装,扯得太急,腋下一条缝线绷了开来。穿上旧的蓝色洋装,她觉得舒服又自在,只是毫无兴奋感。这跟你穿什么没太大关系,她坚定地告诉自己。转个身她又沮丧地对着衣橱,看看是否还有别的替换。没一件适合她跟杰米结婚穿的,连稍微合适一点的都没有,一时间她真想冲到附近小店去买一件衣服。这时她发现已经接近十点,她只剩下梳头化妆的时间了。头发很简单,只要挽到后面,在脖子上打个发髻,但是化妆可是一项精致的平衡艺术,要有点假又不能太假才行。她不想掩饰自己蜡黄的皮肤,或是眼睛周围的细纹,给人感觉好像只是为了今天的婚礼,然而想到杰米带了一个憔悴苍老的人进礼堂结婚的样子又令她无法忍受。终究你已经三十四岁了,她对着浴室的镜子无情地告诉自己。三十四岁,这是身份证上说的。
十点过两分。她对自己的服装不满意,对自己的脸不满意,对自己的小公寓不满意。她把咖啡再加热,坐到窗口的椅子上。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她想,她也没有意愿在最后一分钟做任何改善。
心情慢慢地平复了,她试着想杰米的样子,她竟然看不清他的脸,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对于一个自己深爱的人,出现这种情形也是常有的事,她想着,于是她让自己的心思溜过今天和明天,溜进更远的未来,溜进他们规划了整整一个星期、有着金色乡间小屋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杰米的写作有了名气,她也不用再去上班。“我以前是个很棒的厨子,”她曾经向杰米保证过,“只要花点时间练习一下,我就会做出好吃的天使蛋糕。还有炸鸡,”她说,她知道这些话多多少少都留在了杰米的心坎里。“还有蛋黄酱。”
十点半。她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走到电话机前。她拨了号码,等待,那个刺耳的女声播报着:“……现在时间十点二十九分。”她迷迷糊糊地把时间调回一分钟,她想起昨天晚上自己说话的声音,就在门口:“那就十点。我会准备好的。这一切真的是真的吗?”
杰米的笑声一路延伸到走廊。
十一点,她把印花洋装上的裂缝缝好了,将针线盒仔细地放进橱里。穿上印花洋装,她再坐回窗口喝第二杯咖啡。我大可以从从容容地修补衣服,她想;不过现在太晚了,他随时都可能到,她不敢再做任何的修整,担心一发不可收拾。屋子里没半点吃的东西,唯一的存粮,是她为了他俩开始共同生活而精心准备着的:一包没有开封的培根、十二个盒装的鸡蛋、没开封的面包和没开封的奶油,这些都是为了明天的早餐而准备的。她想冲下楼到杂货店买些吃的,就在门上留了张字条。最后还是决定再等会儿。
十一点半,她饿到发晕,全身无力,她非下楼不可。如果杰米有电话她早就打给他了。现在,她只能拉开书桌,写了张字条:“杰米,我下楼去杂货店。五分钟回来。”钢笔墨水渗到指头上,她进浴室清洗,用了一条刚换上的新毛巾。她把字条贴在门上,再看了一遍屋子,确定一切都没问题,关上门,没上锁,怕万一他刚好进来。
进了药妆店,她发现没一样东西想吃的,除了再一杯咖啡,咖啡也只喝了一半,因为她突然觉得杰米可能已经在楼上等得不耐烦了。
楼上一切如旧,安静无声,跟她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她的字条原封不动地贴在门上,屋子里因为抽了太多烟有些霉味。她打开窗户,坐下来,后来才发觉自己睡着了,现在时间十二点四十分。
忽然,她害怕起来。毫无预警地醒来,醒在这一个随时待命的房间里,这里的每样东西从十点钟开始就一直干干净净,没人碰过,她害怕了,她觉得有一股莫名的急迫感。她离开座位几乎用冲的从房间奔进浴室,往脸上泼冷水,用干净的毛巾擦干;这次她把毛巾随便往架子上一放,不再更换,以后有的是时间。没戴帽子,身上仍旧穿着印花洋装,只在外头罩了件大衣,手里拿着那只不相称的,放了阿司匹林的蓝包包,她锁上公寓的房门,这次不留字条了,冲下楼,在街角招了辆出租车,她把杰米的住址给了司机。
其实一点也不远,如果不是全身虚脱,她走走就到了。坐上出租车,她忽然惊觉这样大剌剌坐着车去找杰米,一副登门问罪的样子实在太鲁莽。所以,她叫司机在邻近杰米家的一个转角停下来,付过车费,等到出租车开走,她才慢慢地走过去。之前她从来没到过这里;建筑老得赏心悦目,大门信箱上并没有杰米的名字,门铃上也没有。她核对住址,没错。最后她按了标着“管理员”字样的门铃。过一两分钟蜂鸣器响了,她推开门走进暗黑的前厅,正犹豫着,尽头一扇门开了,有个人说:“什么事?”
就在这同一时间她才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该问什么,她慢慢移向等在亮光里的那个身影。等到很接近的时候,“什么事?”那个身影又说了一遍,她看见那是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除此之外,他们两个谁也看不清谁。
她鼓起勇气说:“我想找这栋楼里的一位住户,大门外找不到名字。”
“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男人问,她知道她非回答不可了。
“杰姆士·哈瑞斯,”她说,“哈瑞斯。”
男人静默了一会儿,说:“哈瑞斯。”他转过身,向着里面亮着灯光的房间说:“玛琪,过来一下。”
“怎么了?”里面一个声音说,等了好长一会儿,长到即使动作再慢的人也能从安乐椅上起来了,一个女人走到了门口,跟男人站在一起,朝暗黑的前厅张望。“有位女士,”男人说,“女士要找一个姓哈瑞斯的人,住这里的。这栋楼里有这人吗?”
“没有,”女人说。她的口气带些消遣的味道,“这里没有什么姓哈瑞斯的男人。”
“对不起,”男人说。他准备关门。“你找错地方了,女士,”他说,忽然又压低声音补上一句,“不然就是找错人了。”他和女人同时哈哈大笑。
眼看着门就要关上,只剩她一个人站在黑暗的前厅,她冲着只剩下一线的门缝说:“可是他的确住在这里,我知道的。”
“听着,”女人稍微再把门缝拉开一些,“这种事常会有的。”
“请你们再想想,别弄错了,”她说,她的口气十分庄重,口气里累积了三十四年的尊严和傲气,“恐怕你们不是很了解。”
“他长什么样子?”女人不耐烦地说,那门仍旧不肯开大。
“他很高,很好看。他经常穿一套蓝西装。他是个作家。”
“没有,”女人说,停一会儿又说:“他是不是住在三楼?”
“我不太清楚。”
“三楼是有这么一个人,”女人边想边说,“他确实经常穿一套蓝西装,在三楼住过一阵子。劳埃斯特他们家北上探亲的时候把公寓租给他住过。”
“可能就是吧,虽然……”
“这个人经常穿一套蓝西装,不过我倒不记得他有多高,”女人说。“他在这里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以前是——”
“你去问劳埃斯特,”女人说,“他们今天早上刚回来,住在3B。”
门关上了,彻底地关上。厅堂非常暗,楼梯更暗。
上到二楼,从顶上的天窗透进一点微光。公寓各户的大门排成一排,这一楼共有四户,静静悄悄,无声无息。2C门口摆着一瓶牛奶。
上到三楼,她停了一会儿。3B的门里有音乐声,也听得见说话声。她鼓起勇气敲门,再敲。门开了,音乐声迎面冲上来,是下午播送交响乐的时间。“你好,”她礼貌地对站在门口的女人说。“劳埃斯特太太?”
“对。”女人穿着家居服,脸上带着隔夜的妆。
“可不可以打扰你一两分钟?”
“可以。”劳埃斯特太太纹丝不动地说。
“是关于哈瑞斯先生。”
“什么哈瑞斯先生?”劳埃斯特太太直截了当地说。
“杰姆士·哈瑞斯先生。之前向你们租房子的那位先生。”
“喔,天哪,”劳埃斯特太太说。她总算睁开了眼睛。“他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跟他联络。”
“喔,天哪,”劳埃斯特太太又重复一遍。这次她把门开大了些,说:“进来吧。”接着,“洛夫!”
屋子里,整间公寓仍旧充满了乐声,沙发上,椅子上,地板上,摊着还没整理完的手提箱。角落餐桌上散着吃剩的餐点,年轻男人坐在那里,有那么一会儿感觉上很像杰米,他站起身走过来。
“什么事?”他说。
“劳埃斯特先生,”她说。乐声太大,谈话有些困难。“楼下管理员告诉我说,杰姆士·哈瑞斯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
“没错,”他说,“如果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话。”
“你们不是把公寓租给他住吗?”她吃惊地说。
“我对他一无所知,”劳埃斯特先生说,“他是桃蒂的一个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劳埃斯特太太说,“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她走到餐桌旁,把花生酱抹在一片面包上。她咬了一大口,挥着那片抹了花生酱的面包对她先生含混地说,“不是我的朋友。”
“是你在上次那个什么聚会上把他带回来的,”劳埃斯特先生说。他把收音机旁一张椅子上的手提箱拨开,一屁股坐下来,再从地板上捡起一本杂志。“我跟他从头到尾没说过十句话。”
“是你说租给他没关系的,”劳埃斯特太太说完又咬了一大口面包,“你从头到尾也没反对过啊。”
“对你那些朋友我从来都不说什么。”劳埃斯特先生说。
“如果他真是我的朋友,那你的话可多了,绝对,”劳埃斯特太太没好气地说。她再咬一口面包,说,“相信我,他的话可多了。”
“我听够啦,”劳埃斯特先生越过那本杂志说,“够啦。”
“看到没。”劳埃斯特太太拿抹了花生酱的面包指着她丈夫,“就这副样子,一天到晚就这副样子。”
一片静默,只剩下劳埃斯特先生身旁的收音机里继续狂吼的音乐声,她开口说话了,她怀疑乐声这么大,究竟能不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他走了吗?”
“谁?”劳埃斯特太太从花生酱的罐子上抬起头来。
“杰姆士·哈瑞斯先生。”
“他?应该是今天早上走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没留下任何东西。”
“走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早告诉过你了,”她对劳埃斯特先生说,“我早告诉过你说他会把一切都照管得很好的。我就说嘛。”
“算你走运。”劳埃斯特先生说。
“每样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上,”劳埃斯特太太说。她挥着手里的花生酱和面包,“跟我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没动过。”她说。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完全不知道,”劳埃斯特太太开心地说,“不过,就像我说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她忽然发问,“你在找他?”
“非常重要的事。”
“很抱歉他不在这儿。”劳埃斯特太太说。见访客转身要走,她礼貌性地上前一步。
“说不定管理员见过他。”劳埃斯特先生对着那本杂志说。
门在她身后关上,走廊又一片黑暗,只是收音机的音量变弱了。当她快要走到最后一阶楼梯的时候,劳埃斯特太太冲着楼梯井嚷着:“我要是见到他,会跟他说你在找他。”
我该怎么办呢?她想着,现在她又回到街上。回家是不可能了,少了杰米,不知道他在哪里。她站在人行道上站得实在太久,引得对面窗口的一个女人转身叫屋里的某个人过来看看究竟。最后,凭着一股冲动,她走进公寓大楼隔壁的简餐店,店的位置跟她住的公寓位在同一边。有个矮小的男人靠着柜台,在看报。她走进店里,他抬起头,走到柜台前招呼她。
隔着放冷盘肉和起司的玻璃柜,她胆怯地说:“我想要找住在隔壁公寓里的一位先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你怎么不问那里的人呢?”男人眯着眼睛打量她。
一定是我没有买任何东西的缘故,她心里想着,嘴里说:“不好意思。我问过他们了,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说他好像今天早上离开了。”
“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他说着,稍微退回到看报的位置,“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监视隔壁那些进进出出的人。”
她立刻说:“我只是以为你或许会注意到罢了。他应该有经过这里,差不多快十点的时候。他很高,经常穿一套蓝色西装。”
“穿蓝色西装经过这里的人每天有多少,你知道吗,女士?”男人问她。“你以为我整天没事干——”
“对不起,”她说。走出店门的时候,她听见他说:“搞什么东西。”
她走到转角,心想,他一定是走这条路,去我家就得走这条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她试着想象,杰米会在哪里过马路呢?他属于哪一类人呢——他会不会直接从他的公寓前面走过去,随意从人行道穿过去,在这个转角?
转角有个书报摊,说不定他们见过他。她赶紧走上前,等一个男的买完报纸,一个女的问完路。等到书报摊的男人看向她,她才说:“不知道你在今天早上十点左右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高的、穿蓝西装的年轻人走过这里?”男人只是看着她,瞪大了眼睛微微张着嘴,她想,他八成以为这是开玩笑,要不就是在耍什么花招。她急切地说:“是很重要的事,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说,这位女士,”男人开口了,她急着说:“他是个作家。他很可能在这里买过什么杂志。”
“你找他干吗?”男人问。他看着她,含着笑,她发觉又来了一个男的等在她后面,摊商的笑脸所面对的对象也包含这个男的在内。“算了,”她说,可是摊商却说:“你听着,也许他有经过这里。”他的笑里有“我知道怎么回事”的意思,他两眼越过她的肩膀,望着她身后的那个男人。她猛然惊觉自己身着这套太过年轻的印花洋装,立刻把大衣外套拉拢起来。摊商说话了,似乎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现在我也搞不太清楚了,不过,好像吧,今天早上或许是有那么一个很像你那位朋友的先生走过。”
“十点左右?”
“十点左右,”摊商赞同。“高高的,穿蓝西装。很平常啊。”
“他往哪个方向?”她急切地问,“住宅区?”
“住宅区,”摊商点点头,“他往住宅区走。没错。你需要什么,先生?”
她退后,手拢着大衣。站在她后面的男人侧过头看她一眼,再跟那个摊商对视。她正在迟疑要不要给摊商一点小费,这时两个男人开始大笑,她头也不回地冲过了马路。
住宅区,她想,好吧,她开始往这条大路上走,边走边想:他大可不必走这条大路,往住宅区,他只要走过六个街口,转个弯就到我住的那条街了。走了大约一个街口,她经过一间花店,橱窗里摆着婚礼的花饰,她想着,今天毕竟是我结婚的大日子,或许他会买些花给我吧,于是她走了进去。店主从里面迎上来,满面笑容,不等他开口,也不给时间思考她是不是来买花,她就说:“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跟今天早上可能在这里买过花的一位先生联络,非常非常重要。”
她停下来喘气。店主说:“是的,不知道买的是些什么花?”
“我不知道,”她吃了一惊。“他从来没有——”她停住,接着说,“他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年轻人,穿蓝色西装。大约十点钟的时候。”
“我明白,”店主说,“呃,这,我恐怕……”
“这非常重要,”她说,“当时他可能很赶,”她补上一句,希望有所帮助。
“好,”店主说。他笑得很亲切,一整排的小牙齿全部展现出来。“给一位女士,”他说。他走到柜台打开一本大本子,“送去的地点是?”他问。
“啊,”她说,“我想他不会叫人送去。你知道,他是要来——反正就是,由他自己带走的。”
“这位女士,”店主说——很明显地,他被惹火了,他的笑容变得很勉强,继续说:“不瞒你说,我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才能够推测……”
“请你无论如何再回想一下,”她在恳求。“他很高,穿一套蓝西装,就在今天早上十点钟左右。”
店主闭起眼睛,一根指头按在嘴上,用心地想,然后摇摇头。“没办法,”他说。
“谢谢你。”她失望地说,开始往门口走,这时候店主忽然用尖锐兴奋的语气说:“等等!等一下,这位女士。”她转身,店主又想了一会儿,说:“是不是菊花?”他带着疑问的眼神看着她。
“喔,不是,”她说,声音有些发抖,停了半晌才继续。“不适合这样一个场合,绝对不适合。”
店主抿起嘴唇,冷冷地别开视线。“我哪会知道那是什么场合,”他说,“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你问起的那位男士今天早上来过,而且买了一打的菊花,直接取货。”
“你确定?”她问。
“很确定,”店主加强语气,“绝对就是这个人。”他笑得灿烂,她也笑了笑说:“好,非常感谢。”
他陪她走向门口。“需要漂亮的胸花吗?”他们穿过店面的时候,他说,“红玫瑰?栀子花?”
“谢谢你的帮忙。”她在门口说。
“戴上花的女士都特别的漂亮,”他低下头对她说,“要不,兰花?”
“不必了,谢谢你。”她说。“希望你找到你那位年轻的男人。”他说,同时还附带一声很下流的怪声。
她走在街上想,每个人都觉得这身打扮很怪;她下意识地把大衣外套拉得更紧,那身印花洋装露出来的只剩下裙摆磨蹭的声音。
转角有个警察,她想,怎么不去问警察呢——人失踪了就该去找警察。接着又想,我怎么那么笨啊。她脑子里立刻出现一个画面,她站在警局里,说:“是的,今天我们要结婚,可是他没来。”那些警员,大约三四个人站在那里听她说,看着她,看着她的印花洋装,看着她的大浓妆,彼此看来看去地笑着。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没办法说:“没错,看起来很蠢,对不对?我梳妆打扮,在这里找寻那个答应来娶我的年轻男人,可是你们知道什么呢?我并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副样子。我有才华,我风趣幽默,我是一位淑女,我有尊严,我有爱,我有女人味,而且我有清楚的人生观,我可以让一个男人心满意足,幸福快乐。我绝对不是,绝对不只是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这副样子。”
找警察这招显然行不通,如果杰米听到她竟然叫警察追查他的行踪,他会怎么想,那就更别提了。“不行,不行。”她大声说着加快了脚步,有个人经过,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
到下一个转角——离她住的那条街还有三个路口——是个擦鞋摊,一个老头坐在一把椅子上几乎睡着了。她停在他前面,等着,过一会儿他张开眼,笑眯眯地看着她。
“是这样的,”她想也不想地脱口而出,“很抱歉打扰到你,我在找一个年轻人,今天早上十点左右曾经走过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他?”接着她又把他的样貌形容了一遍,“很高,穿蓝色西装,带着一束花的?”
她还没说完,老头就开始点头。“我看见过他,”他说,“是你的朋友?”
“是。”她无意识地笑了笑。
老头眨眨眼说:“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你八成要去看你的妞儿啦,小伙子。他们全是一个样,都是去找妞儿的。”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顺着大路笔直走吗?”
“对,”老头说,“擦了鞋,带着花,穿得整整齐齐,一副急匆匆的样子。你准是有个妞儿啦,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谢谢你。”她一面说,一面在口袋里摸索零钱。
“他一定很想跟她见面,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老头说。
“谢谢你。”她再说一遍,那只手空空地离开了口袋。
终于,她首度可以肯定他确实在等着她,她急急忙忙往前走,印花洋装的裙摆在大衣底下晃着,走过三条街,转进她住的街口。她从街角看不见自己的窗户,看不见杰米望着窗外,等着她,接近公寓大楼的时候她几乎用跑的。开楼下大门的时候,钥匙在她手里抖个不停,她朝药妆店里瞥了一眼,想起今天早上曾经在店里慌张地喝着咖啡的样子,几乎哈哈大笑起来。一走到自己的门口,她再也忍不住,“杰米,我来了,我担心死了。”房门还没打开她就脱口而出。
她的小公寓房间等着她,沉默、荒凉,午后的阴影顺着窗子拉得好长。猛然间,她只看到那只空的咖啡杯,心想,他果然在这里等她,接着发现空杯是她自己的,是她今天早上留在那儿的。她找遍了整个房间,包括衣橱,包括浴室。
“我绝对没有看见他,”药妆店的店员说,“我知道,因为我会注意到那些花。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进来过。”
擦鞋摊的老头醒过来又看见她站在面前。“哈啰,又来啦。”他笑着说。
“你确定吗?”她问,“他是不是走这条路?”
“我看着他走过去的,”老头的语气跟着硬起来,“我心想,年轻小伙子去找小妞了,我眼看着他走进那栋屋子。”
“什么屋子?”她不置可否地说。
“就在那儿,”老头说,他倾过身体指着。“就在第二个路口。手上拿着花,脚上穿着擦亮的鞋,去看他的小妞啦。就这么走进了她的屋子。”
“哪一栋?”她说。
“就在第二条街中间一半的地方,”老头怀疑地看她一眼,说,“你究竟想要干吗?”
她几乎用跑的,连一声“谢谢”都没停下来说。她飞快地走到下一条街,从那些屋子外面一户户地看一户户地找,看杰米会不会正巧在看窗外,注意听哪间屋里会不会有他的笑声。
有个女人坐在一栋屋子前面,就着手臂的长度,一来一回地推着一辆婴儿车,很单调的动作。小车里的婴儿睡着了,身体随着婴儿车一来一回地动着。
现在,她的问话越来越顺畅了。“对不起,今天早上十点左右,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走进这里的一栋屋子?”
有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停了下来用心听着,很认真的轮流看着她们两个,偶尔瞥一眼小车里的婴儿。
“我说,”那女人厌烦地说,“这孩子十点钟洗的澡。我有没有看见什么陌生的男人走过?你说呢?”
“一大束花吗?”男孩拽了拽她的大衣问她。“很大一束花?我看见过他,太太。”
她低下头,男孩大剌剌地对她咧着嘴笑。“他走进哪栋屋子?”她疲累地说。
“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男孩盯着问。
“这样问人家很不礼貌喔。”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说。
“你听我的没错,”男孩说,“我看见他了。他走进去那里。”他指着隔壁的一栋房子。“我跟着他,”男孩说,“他给我两毛五。”男孩装出低沉的吼声:“‘小鬼,今天可是我的大日子啊。’他说。他给了我两毛五。”
她给他一张一块钱的纸钞。“在哪里?”她说。
“顶楼,”男孩说,“他给我两毛五之后我就不跟了。直上顶楼。”他拿着那一块钱钞票退回到人行道上,隔得远远的,伸手逮不到的距离。“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他再问一次。
“他拿着花吗?”
“对啊。”男孩说。他开始尖着声音喊:“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太太?你抓住他的小辫子了?”他歪着身体边跑边吼,“她抓住那家伙的小辫子了!”推婴儿车的女人哈哈大笑。
那栋公寓房子的大门没有上锁,外面的走廊没有门铃,也没有住户的姓名。楼梯很窄很脏,顶楼有两扇门。前面一扇应该就是了,门外的地板上有一张皱皱的包装花纸和一条纸彩带,就像一条线索,就像档案追踪游戏的最后一条线索。
她敲门,似乎听见里面有人声,她忽然心生恐惧,要是杰米在里面,要是他来应门,我该说什么呢?刹那间人声好像停止了。她再敲,一片静默,只有些微的笑声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很可能他在窗口就已经看见我了,她想,这是面向大街的前栋公寓,刚刚那小男孩又叫得那么大声。她等着,再敲,但是静默无声。
最后她走到同层楼的另外那扇门前,敲了一下。门顺着她的手势晃了开来,她看见空荡荡的一间阁楼,墙上钉着光秃秃的木条,地板也没有上漆。她走进去,四下看了一圈:屋子里到处都是塑料袋、旧报纸,还有一只破烂的皮箱。有个声音,她猛地发现那是老鼠的声音。忽然她就看到了它,离她非常近,靠着墙壁,邪恶的面孔上一脸的警戒,明亮的眼睛死盯着她。她慌张地逃出来,关上门印花裙摆被勾住了,扯破了。
她知道有个人就在另外那间公寓里,因为她确定她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还有时不时出现的笑声。她回来过许多次,第一个星期她每天都来。早上,在她上班的路上;晚上,在她一个人去吃饭的路上,只是无论她敲了多少次,敲得多用力,从来没有人出来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