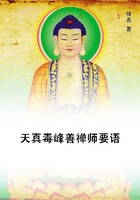我听卫玠说的不无道理,点着头说:“卫郎,不如我们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宅院吧?我有时真的不想总是与嫂嫂碰面,我也不知为何,她一见我就冷嘲热讽的。”
卫玠感同身受,点着头说:“阿玄,只是我的俸禄太少,买宅院毕竟不是小数目,可否容我再缓一缓?”
“卫郎,我明白,要不把我的嫁妆都变卖了吧?”我确实不想再跟婆婆嫂嫂一起住了。
卫玠似乎有些为难,握住我的手,柔声道:“阿玄,我知道你住在这里不惯,可是你的嫁妆都是岳丈给你的私人财产,怎能为了买宅院而随意变卖呢?”
“卫郎,对我来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若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就算散尽钱财我也甘愿。”我苦笑着说道。
因为我莫名穿越到这个时代,也许不过就是黄粱一梦,就算有再多的钱,一旦梦醒了,也许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卫玠觉得我的话有些莫名其妙,紧张地望着我问道:“阿玄,你这是何意?你说的真正的自由又指什么呢?”
“我不过是说着玩,你别当真。”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我们吃过午饭,待小月醒来后,才用极其委婉的话跟她表述了,她夫君可能已经死掉的实事。
小月先是愣了片刻,随即便泪流不止,最后嚎啕大哭起来,最后嗓子都变得有些嘶哑起来,直到傍晚,她才稍稍缓解了些,忍着疼痛,要去乱葬岗找她夫君的尸体。
我担心她的体力无法支撑,担忧地问道:“小月,要不,你身子好些了,我们再去找。”
小月却猛烈地摇了摇头说:“若是去晚了,我怕连他的尸身都找不到了。之前因王爷们争权夺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饿殍满地,城外的乱葬岗不知丢了多少人的尸体,可是野外的野兽们却把那些尸体当食物吃掉。”
我听得毛骨悚然,望了卫玠一眼,只见他眼中满是伤痛,我和他相视一看,决定带着小月去城外。
如梦和紫苏坚持要跟着,我自然拗不过她们,最后我们五人挤着一辆马车驶向城外。
待我们到了乱葬岗,只见正冒着滚滚浓烟,原本堆积成山的尸体不知早已被烧焦,这下子我们犯了难,这可如何寻找?
可是小月见状像疯子一般,疯狂地冲过去,一具一具尸体翻找着,不知为何她总是要撬开尸体的嘴巴查看。
我们四人根本没见过他夫君,也不知是何模样,也无法帮他寻找。
“小月,如今这尸体都烧得面目全非了,你又如何寻找你的夫君呢?”我尽管非常理解小月的心情,然而这么多尸体,不知要找到何时。
“就算他化成灰,我都要把他带回去,不能让他做个孤魂野鬼!”小月蓦然抬起泪眼,满脸坚毅,又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夫人,我夫君嘴里有一个特殊的印记,这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
“天哪,胎记居然长在嘴巴里?这也太神奇了吧?可是个什么印记呢?”我奇怪道。
小月摇着头说:“并不是胎记,而是生下来就烙在嘴巴里,不仅他有,而且是整个村子的男子都有。那个印记很奇怪,像是一种古老的符文,不过我读书少,从未见过。”
卫玠此时忽然有了兴趣,看了我一眼,与我一同翻找起来,尽管到处都是烧焦的味道,可是我们忍着难闻的味道不停寻找着。
如梦和紫苏也极其不情愿地加入我们,可是我们找到了黄昏,都未找到任何有印记的尸体。
此时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宵禁了,我们只得悻悻离开。
当晚我们回去之后洗了澡,东西都没吃就累得睡下了,谁知半夜却被如梦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听到她焦急地喊道:“夫人,小月不见了,而且还拿走了府里所有的金疮药。”
我本有些迷迷糊糊的,一听到如梦的话,顿时清醒了,“如梦,你说什么?小月不见了?她何时离开的?”
“夫人,我也不知道,我方才起夜,忽然看到小月的房门大开,还以为她忘记关门了,谁知我看到床上没人,以为她也去上茅房,可是我在茅房外喊她的名字,并没有回应。我进去一看果然没人,而且我发现夫人之前放药的那个房间的门居然是开着的。我吃了一惊,进去一看,珍贵的药材都还在,只是所有的外用的药都不见了。”如梦一口气说完,顿时觉得有点喘,轻轻拍了拍胸口。
卫玠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轻轻说道:“如梦,走就走吧,那些药也不值什么,就当我们送给她了。此事不要声张,若是有人问起小月,你就说小月有个亲戚把她接回去了。”
如梦尽管不懂为何公子要这样说,可她早就习惯了被命令,于是只好点点头,郁闷地回房了。
“卫郎,你可是想到了什么?”我看卫玠的凤目似乎有什么在翻涌着。
卫玠冷笑一声说:“阿玄,你我都被小月捉弄了,她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柔弱,而且我猜她已经找到了她的夫君,或者说她的夫君根本就是杜撰的。”
“卫郎,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小月的伪装,她并不是真正的农家女?可她闹这么一出又图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阿玄,你因为小月的事可是引起了东海王的不快?”卫玠幽深的黑瞳静静地望着我。
我点点头说:“不错,若不是小月的出现,我的确不大可能接触到东海王。卫郎,你的意思是说小月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与东海王结怨?可是这对她有何好处呢?”
卫玠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不自主地抚摸着下巴,他每每陷入沉思就回不由得摩挲下巴,片刻后方才说道:“也许小月的身份并不是这么简单,她只不过是受人指使罢了,那只能说明她的主人想利用你和司马越作对来获取渔翁之利。”
“可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子,而司马越却是王爷,我又能对他造成说明威胁呢?”尽管我觉得卫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还是有不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