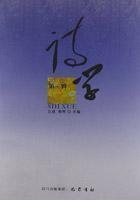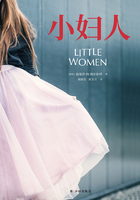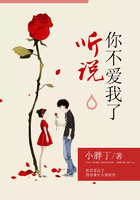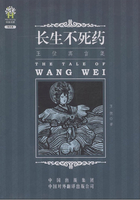杨梓
洪立于1983年在《朔方》发表诗作,写诗已三十多年,《露珠上的太阳》却是他的第一部诗集。
人生会有几个三十年?而三十年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又是何等的不易?
年初,宁夏诗歌学会经审编部推荐、会长团同意,支持洪立等八位符合条件的理事出版诗集。诗歌学会编辑部主任唐晴三番五次地催过洪立的诗稿,复印件也行,其他的都不用管了,他却不愿给学会添麻烦;我又给洪立打电话连催促带训斥,他才发来了诗集的电子版,原来是从工地请了三天假回家整理的。
我原本是直接转给印厂排版,却不由自主地打开了;原本是只想浏览一下,却一口气读完了,并略微编辑了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天空这只大茶杯里漂浮/任苦涩的眼泪落进水里/我只能安静地品尝自己”(《一个人喝茶》)。读到这样的诗,我又不禁想为洪立的诗集写点什么。
《露珠上的太阳》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质地朴拙而透出灵巧,抒情诚挚且情感浓郁,语言简明又跳脱如兔。如一道黄昏中脉脉含情的目光,在不经意之间轻轻撞击一下我的心灵。
一般来说,诗如其人,诗品即人品;个别来说,与社会伦理道德有悖之人也会写出好诗,因为真善美是人心所向。洪立显然属于前者,他不像大多数诗人有固定的薪酬,而要面对黄土,还要外出打工,但我不能称他为“农民诗人”或“打工诗人”。因为洪立的诗里并没有怎么种地、怎么打工的内容,只是他的所见所想;更因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男女、民族、城乡、身份、时代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的就是他呈现出来的诗作文本。
洪立的诗像他一样朴素,有时还显得笨拙,好像不知道怎样组织语言、怎样分行,而这又恰恰在他随意的排列中显出了灵巧、透出了诗意。如“一个人背着谷子/另一个人就摊开手掌/掂量着谷子的分量/那种弯腰的姿势/就像下垂的谷穗”(《傍晚》);再如“看一朵花开得很疼/看一片花红得发晕//花开得只剩下花了//在一朵花下/我葬下飞鸟/我想让花也开出飞来/让花也开出鸣叫”(《我多么希望花开得和天空一样》)。与其说这首诗出自一只粗手大脚的男性之手,毋宁说来自一颗细腻温婉的女性化的心灵。
西方浪漫派美学认为,“只有情感,才能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它是诗的根本条件”。透过表面上五大三粗的洪立,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洪立很敏感、很细心、很柔情,也很会抒情。
抒情是诗的气息,或一气贯通,或一唱三叹,抒情的氛围便如云雾弥漫。而气息的强弱则取决于作者内心的情感,以及对情感的适度把握——既能放开又有所节制。正如云雾,太浓则遮天盖地,太淡则一览无余。抒情是诗的本质之一,是情感的弥漫,可现代诗已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古典的情景结构变为“情事结构”。所以很多的现代诗消解了以情景为主的意象,已非抒情诗,而是以细节或情节为主的小小说化的叙事诗了。
而在《露珠上的太阳》中,大部分都是抒情诗,尤其是洪立写给父母的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同时也消解了叙述。他写父亲:“我喝醉的时候/你在后面跟着/但我不知道/你悄悄地用一尊黑影跟着……”(《喝醉的时候父亲跟着我》);“强硬的父亲/从我记事起就没这样呼喊过我/但他心里一定是这样装着/直到他的泪水偷偷从眼角流了出来……”(《父亲喊我为“孩子”了》)。他写母亲:“那是我的母亲/站在半山上/衣襟里兜着杏子/红红的闪着/微疼的光……十八年前/把自己栽到风雨里/目送我走出家园……一片杏树都已长大//我的母亲还站在半山上”(《杏树》);“站在村口张望的母亲/几次都睁开泪蒙蒙的双眼/透过泪蒙蒙的时空/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把儿女朝一块拽”(《这次》)。母亲衣襟里的杏子都长成了杏树,但母亲还站在半山上,一站就是十八年。在此,母亲就是杏树,杏树也是母亲。这里的情感已被洪立抒发到了极致。
读洪立的诗,暂且不管其诗内容与形式,仅在语言层面,常常有词语从语言中跳将出来,令人眼前一亮,让人感到惊喜。但这在诗学上还无法归于哪一种手法或技艺,倒令我突然想起一个词“跳脱”,正是“化板滞为跳脱”,亦使平面而立体。如“这里空气停留/阳光在树叶上打坐”(《正午的河边》),阳光打坐,让人联想到了佛。“黄河在一位老庄户的唢呐里/泪流满面”(《守望大河》),谁在流泪?是老庄户还是黄河?“一片落叶又一片落叶/大地布满倾听的耳朵”(《落叶》),落叶即耳朵,什么都可以倾听。“我跑到村口拐弯的地方/我发现家乡的石头活了”(《春天的象征》),春天来了,连石头都活了。“然而我认识了歌的含义/也许是内心的独白/也许是爱的积蓄/就在这个时候/她透明了”(《看望一支歌》),是诗人认识了歌,却突转到“她透明了”。
是的,在“口水诗”泛滥成灾的当前,《露珠上的太阳》无疑是一朵朵怒放的荷花。
洪立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具有语言简约、意象别致、抒情浓郁、想象奇特、节奏鲜明、勇于独创等特点,而这些恰恰是诗的审美本质。本质具有永恒的意义,关键在于诗人如何去把握;真理也具有永恒的意义,关键在于诗人如何去表现。坚持创作是诗人的安身之根,坚守纯粹是诗人的立命之本。这两点,洪立都能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十几年前,我在《朔方》编辑部,常和朋友去洪立家小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在此谢谢为我们拌苦苦菜、炒“笨蛋”、炖排骨的嫂子。我们喝大之后就拎着酒去祭黄河,与黄河干杯,还想看看醉了的黄河是什么样子——一块冰凌突然起立,又轰然倒下。是在黄河解冻的黄昏,非常壮观而又感觉恐怖。
往事如烟,生活继续。诗歌已流在我们的血液里,并成为我们继续生活的精神寄托,成为我们每天可以不写诗、但每天不能不思考的生活方式。在此,与洪立共勉。
2014年9月28日于夏都闻月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