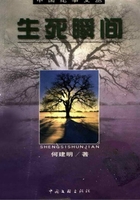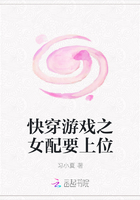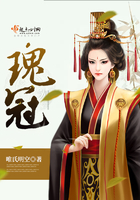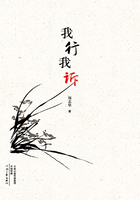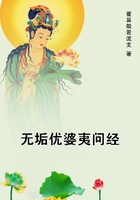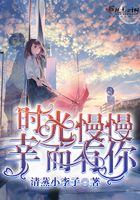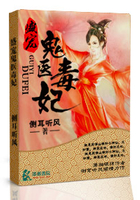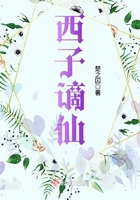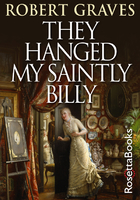记得,那是十多年前(但已被人们普遍称为“上世纪90年代”了),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了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篇还没有中译本,它们是阿尔贝·柯恩的《主的美女》、于斯曼的《逆流》、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居谢》,等等。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的期望一再呼吁,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和出版人,应该赶紧把这几篇小说译介过来。
一本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迟迟没有翻译过来,其原因大致可以猜想。是作品太难了,不太好翻译?还是作品不太不合国人的口味,或者说不太合国情?是作者“反动”、“消极”,还是反华、仇华?再不然,就是题材不合适?为色情、暴力,怕出版上通不过?
实际上,《逆流》跟反动、暴力统统不沾边,至于色情,也只局限于幽默含蓄地描绘,不属于挑逗性欲的porno。要硬说它有什么趣味上的毛病,恐怕只有一点:“颓废”。
那么,于斯曼的《逆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颓废”呢?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首先,我们恐怕得认识一下这位于斯曼。
其实,《逆流》的作者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真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参与了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活动,以一篇小说《背包在肩》而成为“梅塘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同为该集团的成员,除了左拉、于斯曼,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塞阿尔和埃尼克。而代表自然主义“宣言”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于斯曼的《背包在肩》,还有更著名的左拉的《磨坊之役》和莫泊桑的《羊脂球》。
不过,自然主义流派的好景不长。后来,于斯曼因为小说美学的趣味、诗学倾向的追求、宗教观念上的观点与左拉相抵牾,逐渐离开了自然主义流派。
于斯曼发表的小说作品,除这一部最重要也最有名的《逆流》(1884)之外,还有《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1876)、《瓦达尔姐妹》(1879)、《同居》(1881)、《顺流》(1882)、《那边》(1891)、《路上》(1895)、《大教堂》(1898)、《居士》(1903)等,被后人认为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学中某种从现实、科学的潮流走向象征、神秘倾向的代表,受到后来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推崇。他的艺术评论集有《现代艺术》(1883)、《某些画家》等,对当时还尚未成名的塞尚、德加、瑟拉等印象派画家大加赞赏。
在于斯曼的前期小说作品中,《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写实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法国合法妓院中的情景;《瓦达尔姐妹》则讲述了在巴黎一家书籍装帧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两姐妹的故事。《同居》讲述了小说家安德烈·雅扬的生活,他婚后发现妻子贝妲不贞,便离开她而前后与一个叫布兰雪的高级妓女和一个叫雅娜的女工同居。《顺流》讲述了一个受蹂躏的巴黎小书记员让·弗朗丁的故事,他始终在寻找精神的幸福和物质的舒适,却屡屡遭受挫折。以上作品,都因其高度写实的风格、直接描绘社会的主题,而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到了于斯曼的写作后期,即以《逆流》一书为标志而告别自然主义流派之后,他的主题和风格大大地改变了。《那边》讲一个平庸的巴黎作家杜塔尔对法国历史上被认定为罪人的吉尔·德·雷斯展开了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尚特露弗夫人的极度兴趣,她不久就投入了杜塔尔的怀抱,两人从此进入了撒旦的世界中。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口,宣告自然主义已走进死胡同,而只有神秘主义才有出路。在于斯曼皈依宗教期间发表的三部小说《路上》、《大教堂》、《居士》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宗教生活体验,这些作品明显影响了后来一些法国作家的宗教信仰,如布尔热、贝矶、克洛代尔甚至莫里亚克等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于斯曼在1903年担任了龚古尔文学院的第一任主席,主持评选一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
《逆流》(A rebours, 1884)是于斯曼最主要的作品,也是法国小说史上一部毋庸置疑的杰作。一方面,是于斯曼成就了《逆流》,而另一方面,更应该说,是《逆流》这部非凡的作品成就了于斯曼。
小说一开始写到,主人公贵族后代德塞森特厌倦了早年在巴黎的放荡生活,并且跟都市的资产阶级时尚文化格格不入,便幽居到离巴黎稍稍有些距离但又交通便利的郊区乡下,在丰特奈玫瑰镇买下一所宅子,去那里过着一种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认为是“颓废主义”的生活。
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塞森特在乡下隐居期间的日常生活,它从头到尾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只是杂乱地、随心所欲地、充满细节真实地描写家里家外的各种事物,以及主人公看到这些事物时心中的种种联想。而这些联想,分别涉及到自然现象、社会生活、艺术现象、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了作者对当时的时尚文化、传统的文明、各种艺术的发展情况、各种风俗习惯的演进所做的个性化的价值评判,颇有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小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百科全书来阅读。
《逆流》全书一共十六章。每一章各涉及一个话题。
作为楔子的“说明”一章,追述了德塞森特的祖上家谱,以及他幽居之前形骸放浪的往昔生活,说明主人公德塞森特的没落贵族血统,从这一点描写中,依稀还能看出左拉倡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些微影响。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写德塞森特乡间新居房屋的布局构造、家中的家具摆设、书房的藏书分类,其中关于颓废文学藏书的那一章即第三章,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列举了有关的作家和作品名称,显然有些掉书袋的意味。
第四章详细描绘了一只作为装饰品、浑身缀满了珠宝的乌龟的命运,德塞森特如何把它买下,又如何请人为它的甲壳点缀珠宝,镀上一层金,最后,它又是如何默默地死于珠光宝气之中。其间,还穿插对各种各样的利口酒的音乐调性作了极富想象力的比较。
第五章中,作者用文字描绘了德塞森特家中收藏的莫罗、吕肯、伯莱斯丁、勒东、泰奥科普利等几位画家的绘画作品,以及与一种隐士生活相适应的房间布置和家具配备。
第六章,分别涉及德塞森特对两位朋友的回忆,一个是婚后陷入到夫妻共同生活之不幸中的戴古朗德;一个是在他的教唆下开始学会嫖娼酗酒的十六岁顽童奥古斯特。
第九章,是德塞森特对自己恋爱经历(一个身材健美的杂技女演员尤拉妮娅小姐、一个会腹语术的女子,以及一段同性恋)的回顾和思考。
第七、第八、第十章,分别涉及到宗教信仰与渎圣、花卉与噩梦、香水与气味,从中可见作者在这些方面的丰厚学识和怪异趣味。
而第十一章,则描述了一次本来计划得很确切周密,但到最后却不了了之的伦敦之旅,同时穿插着漫谈了英国的小说和绘画。一开始德塞森特突发奇想,要去伦敦,便立即命令仆人整理行装,冒着大雨,坐火车从丰特奈玫瑰镇赶往巴黎,在巴黎坐了马车,吃了饭,喝了酒,就在火车站门口准备登上前往伦敦的列车之前,他断然决定放弃此行。这次未遂的英伦之行,颇有些中国古代文人故事中“王徽之雪后月夜赴剡溪访戴逵”的味道。
从第十二到第十五章,分别以非宗教类藏书、病痛不适与卖淫业、当代文学、音乐等为主题。其中的第十四章,专门论及法国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后来被认为是“颓废派”的那些诗人,表达了作者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小说第三章“古罗马颓废文学”的一个简明的补充说明。
最终,第十六章,德塞森特在丰特奈玫瑰镇的隐居生活以失败告终,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摆脱这隐修士一般的孤独生活,重返金钱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回到世俗的公共生活中去。
十六个章节,对应十六个以上的话题,于斯曼就这样借德塞森特之口,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描述隐居生活中的种种感官享受,种种奇异趣味;另外还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将自己不俗的见解一吐为快。
这样的写法,以精致、细腻为特点,以感官的愉悦为目的,在以往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故意为之的仿佛就只有于斯曼一个人。可以说,于斯曼是用十六章的离题话,描写了一个隐居的文人德塞森特所经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遐想。用作者自己后来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的“每个章节都变成了一种特殊风味的酱汁,一种不同艺术的升华;它浓缩成宝石、香精、花卉、宗教与世俗文学、非宗教音乐和素歌的一种‘精华’”[1]。
说是“精华”也好,或者“百科全书”也好,都是一个意思。《逆流》以其特殊的笔触关注到了人物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方面,让“颓废”存在于生活诸方面。
小说第五章中关于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那幅《莎乐美在希律面前跳舞》的描写,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主人公所追求的颓废生活的审美趣味。小说花费了大量笔墨,仔细描绘了这幅画的画面,以及绘画本身带给人们的感官享受。在此,我们仅只引用其中关于莎乐美形象的那几段:
在熏香的邪恶气味中,在这一教堂的热烈氛围中,莎乐美伸展左臂,做出一个下命令的姿势,右臂则弯曲,举着一朵大莲花,举到脸孔的高度,还踮起脚尖,按照一个蹲在侧旁的女子拨弦弹琴的节拍,徐徐前行。
她表情安详,肃穆,几乎可称为崇高,开始跳起应能唤醒老希律王昏钝感觉的淫荡之舞来;她的胸脯波动起伏,随着旋转不止的项链的摩擦,乳尖很快尖尖地挺立;一颗颗钻石紧贴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亮;她的手镯,她的腰带,她的戒指,喷发出点点星火;她鲜艳的衣裙上镶有珍珠,嵌有银片,缀有黄金,披金挂银的护胸甲上,每一个小网眼上都是一粒宝石,它们如火燃烧,蛇形的火焰彼此交错,在暗色的肌肤上,在玫瑰茶色的皮肤上躜动,宛如一些灿烂辉煌的昆虫,带了耀眼夺目的鞘翅,胭脂红的纹路,霞光黄的斑点,钢蓝的杂色,孔雀绿的条脉。
可与之媲美的还有作者对莫罗另一幅叫《显灵》的水彩画的描述,于斯曼借德塞森特的眼睛,看到那个舞女的妖艳和热辣:
她几乎全身赤裸;舞到炙热时,裙纱已全乱,锦缎早坠地;她身上只剩金银和珠宝饰物;一段护带紧紧围在脖子上,像是一根腰带围在腰上;而一颗精致的宝珠就像一个美妙的搭扣,投射出一道道闪光,照在两个乳房间的乳沟上;更低处,胯上系有一条带子,遮住了大腿的上部,那里垂晃着一个硕大的水晶坠子,从中流泻出一条红宝石和祖母绿的小河;最后,赤裸的身体上,护颈带和腰带之间,是鼓鼓的肚子,肚脐凹进一个洞,很像一枚缟玛瑙雕成的印戳,乳白的,带有指甲盖的玫瑰色。
就在从施洗者脑袋中散发出的热腾腾的光线底下,珍珠宝贝的所有小小表面都在燃烧;宝石有了活力,用闪亮的光线描绘出女人的肉体;一点一点的热火,刺在她的脖子上、小腿上、胳膊上,鲜红如煤火的烈焰,亮紫如煤气的火花,艳蓝如酒精的火苗,洁白如星辰的火光。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感觉如在享用一道视觉的盛宴,甚至可说是色情形象的盛宴。而整篇小说中,类似风格的描写段落还有很多,充分体现出于斯曼对“颓废”这一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其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揣摩。
再比如,单单是黑与白,主人公德塞森特也能看出其中的幻觉般的妙处来。如第四章中这样一段“夜里窗前观雪”的描写:
下雪了。灯光下,冰之草正在蓝盈盈的窗玻璃后面生长,而霜之花就像溶化的白糖,在带有小小金色斑点的瓶底状窗玻璃中闪光。
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了沉湎于黑暗中的小房子。
德塞森特想入非非;燃烧的柴火散发出热腾腾的气息,灌满了房子;他把窗户开了一半。
天空像一道高高的黑底银斑纹的帷幔,在他面前升起,黑黑的,夹着几点白斑。
一阵寒风刮过,加剧了漫天雪花的飞舞,一时间里颠倒了颜色的秩序。
天空的纹章帷幔翻转过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白鼬皮,银的底纹,白白的,夹着几点黑斑,那是夜的斑点散布在雪花之间。
如此精致的描写,恐怕只有于斯曼能捕捉其中的细腻感受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颓废”了。
“颓废”一词,在法语中为“décadence”,本来指古罗马文学中继黄金时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以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之后的一个“衰微”阶段的文学,即公元1世纪之后的罗马社会。故而“décadence”也可翻译为“衰微”,或为“衰颓”。那个时期的一些罗马作家,如《萨蒂里孔》的作者佩特罗尼乌斯,所写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复杂情节和错综的情感纠结,只是用精致华美的语言,尽量细致而客观地描写当时走向没落的罗马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颓废风俗和享乐生活。
于斯曼正是在古罗马颓废时期的这一类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即以各种各样的文字手段,来穷尽自然、生活、艺术、人为模仿所能给人带来的一切享受。
现在,“颓废”一词,在文学史上,倒反是特指19世纪末期的那些法国诗人,尤其是那些象征派诗人,例如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兰、兰波、科尔比埃、泰拉德、雅里、拉福格等人,当然,还包括同时代英国的晚期唯美派诗人,如王尔德、西蒙斯等。1886年到1889年,法国诗人阿纳托尔·巴茹(Anatole Baju)创办了叫《颓废》的杂志(Le Décadent),更是标志着颓废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当然,于斯曼的这部《逆流》,一直被文学史家们看作是颓废主义的圣经。
当然,于斯曼在这种颓废的情调、颓废的生活、颓废的趣味之上,加入了他的现代享乐主义,他的神秘主义,他的象征手法,他的宗教情怀……
就这样,以于斯曼等人为代表的颓废派作家,在19世纪末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逆流”。
于斯曼及其同道喜爱人工仿造更甚于现实,喜爱字词更甚于思想。这是他写作的一大特色,也是颓废派的一大特色。
在《逆流》中,作者借德塞森特之口说,“人为的仿造是人类才华的独特标志”。他甚至声称:“大自然的著名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会是那么微妙,或那么崇高,以至于人类才华无法创造;没有任何一座枫丹白露森林,没有任何一道月光清辉,不能用充满电灯光的布景来制造;没有任何一道飞流瀑布,不能由水利设施来模仿得惟妙惟肖;没有任何一片怪石巉岩,不能用硬纸板来逼真地拼凑;没有任何一朵鲜花,不能由特殊的绸缎和奇妙的彩色纸来与之媲美!”
于斯曼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甚至拿“北方铁路线上采用的那两种火车头模式或类型”来比喻不同种类女人的形象,“好好辨别一下自然作品中被认为最精美的那种,其创造物中被公认为具有最独特和最完美的美的那种:女人;难道人类不是仅仅靠着自己,就制造出了完全抵得上女人的一种活生生的和人造生命,至少在造型美上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那两段中,作者沉醉于对两种火车头所作的女性人物的精细描绘中:
其一,克兰普统,一个令人赞叹的金发女郎,尖利的嗓音,苗条高挑的身材,束缚在闪闪发亮的黄铜胸衣中,恰如母猫柔软而又神经质的舒展身躯,一种娇艳和鲜亮的金发女郎,其异常的优雅令人敬畏,当她绷紧了钢铁的肌肉,挥发出温暖腰身上的汗水,她便启动巨大的玫瑰花窗般的精美轮子,生气勃勃地向前冲锋,位于激流和浪潮之首!
另一个,恩格尔特,一个肤色发暗的巨大的褐发女郎,喊声低沉而沙哑,腰肢短粗,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件生铁盔甲中,一个魔鬼般的野兽,冒着披头散发似的黑烟,有六对低矮的轮子;当她稳稳当当、慢慢悠悠地牵动笨重的货物车厢长尾,让大地颤抖不已时,她显现出了何等压倒性的强力啊!
在婀娜多姿的金发美女和丰满壮硕的褐发美女中,肯定再也没有同一类型的纤细苗条和骇人力量;我们可以确定无误地说:人类能够在其自身属性规定的范围内,做得跟他们所相信的上帝一样好。
小说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对塞纳河上一条驳船上的维捷浴场的描绘,说明了人们是如何“伪造”出了一种海水浴的美好感觉。而在第十章中,则通过香水的制造来说明仿造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作者对人造的生活氛围的刻意追求,那便是居所中色彩带给居住者的视觉感受。为了让住宅中墙壁、地板、家具的颜色符合一个夜猫子在烛光下的视觉愉悦,主人公德塞森特对色彩的种种变化的可能性做足了研究:
在烛光中,蓝色转向了一种假绿色;假如是深色系的蓝,如钴蓝和靛蓝,那么它就变成黑色;假如它很浅,它会变灰;假如它色泽本真,温和,泛着青绿,它便发暗,发冷。[……]
而铁灰色,依然皱眉沉脸,并显得笨重;珠灰色则丢失了其清亮,变形成一种脏白色;褐色沉沉入睡,渐渐冷却;至于深绿色,还有皇室绿和香桃木绿,它们的情况跟海蓝色一样,会融合在黑色之中;剩下就是更浅的绿色了,例如孔雀绿,以及辰砂色和生漆色,但是,那时候灯光会流放它们的蓝色素,而只监禁它们的黄色素,而这黄色素只保留下一种虚假的色调,一种混浊的味道。
由于种种原因,主人公最终选定的主色调是橙色。
很显然,这一切“人工仿造”的享受给人带来的快感毕竟是有限的,但于斯曼就是要用“字词”使这一有限的享受达到其顶峰。除了色彩方面的视觉享乐,小说中还有多处描写了味觉、触觉、听觉、嗅觉等的感官享乐,其中第四章中对被称作“对嘴管风琴”的利口酒的桶库的描写,则同时体现出听觉上天籁之音和味觉上琼浆玉液的结合。
关于小说《逆流》的重要性,法国书评专家们编著的《理想藏书》是这样评价的:“世纪末纨绔子弟德塞森特的品行与遭际。感觉世界的一次博学的、程序化的探索。小说词汇如香水一般精致细腻。”[2]《理想藏书》竭力推荐《逆流》,把它选为最佳二十五本“法国小说”之一。
作者于斯曼自己二十年后总结本书时说:“《逆流》之后我所写的所有小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萌芽。确实,它的那些章节只是后来各部作品的端倪。”[3]
《逆流》出版后,立即获得了不少作家的赞誉,这从我们收集在本译本后面的“《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可见一斑。例如,保尔·瓦雷里这样说:“于斯曼是当今天下人里头跟我的心最合拍的人。我一直在重读《逆流》;这是我的圣经,我的床头书。最近二十年来,再没有比它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创造了一种文风、一种典型,还几乎创造了一种新艺术的罕见杰作之一。德塞森特在自身趣味上是相当的堕落,行为又是相当的神秘,足以诱惑我,我不断地嫉妒他那在精细的孤独中和在精神的魔力中的长久憩息。”[4]而马拉美,他甚至就把《逆流》称为他自己所期盼的“唯一的书”[5]。
最令后世的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的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在其名著《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让主人公道林·格雷成了《逆流》的忠实读者,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段王尔德借道林·格雷之口对《逆流》的看法:
这是一本没有情节的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一切归结于对一个年轻巴黎人的心理学研究,此人,在十九世纪中叶,把他生命中的精力全都贡献给了对以往时代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思想方式的沉思,他寻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自己心中,总结人类精神所曾经历过的各种形态;他喜爱那些被愚人们叫做美德的放弃,只因为它们的人为痕迹本身,同样也喜爱那些仍然被智者叫做罪孽的本能反抗。作品以一种精细雕琢的奇特风格写成,既闪闪发亮,又隐晦曲折,充满了俚语、老派说法、技术名词,以及博学的长篇大论,它们正是法国象征主义者中某些最完美的艺术家的作品的特点。人们从中能找到其奇异怪诞堪比一些兰花的暗喻,还有同样微妙的一套色彩。感官的生命在这里以神秘主义哲学的术语得到了描绘。有时,人们不再知道,他们读到的到底是一个中世纪圣人的精神自述,还是一个现代罪人的死气沉沉的忏悔告白。这是一本毒液四溢的书。在书页周围,飘荡着一股沉重的熏香,熏得人脑袋生疼。句子的韵律本身,从音乐性上来说充满了节奏和微妙的单调,随着章节的展开,在一个年轻人的精神中,决定了某一种麻木迟钝,一种病态的梦幻,它会剥夺他整个关于太阳下山和阴影匆匆滑过的意识。[6]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逆流》很不以为然,例如左拉,他在致作者的信中就说,他已经“闻到愚昧无知的气味了”[7]。
于斯曼心里很清楚,左拉一定会指责这本书偏离了自然主义道路:“他说我给自然主义带来了可怕的一击,我让流派误入了歧途,我用这样一本小说给自己破釜沉舟地自断了后路,因为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文学类别来界定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中一鼓而穷尽的这一文类”,而且,左拉会督促他“把自己束缚在一种风俗研究中”[8]。
对于自己与左拉之间的美学思想分歧,于斯曼毫不含糊地认定自己的理由:“首先,是我体验到的那种迫切需要,要打开窗户,逃离一个令我窒息的环境;其次,是强烈的欲望,要打破偏见,打破小说的界限,让艺术、科学、历史进入小说,总之,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来作一个框框,让更严肃的内容进入其中。”[9]他对自然主义非常失望:“这一流派,本应对把真实人物定位于确切的环境中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却落得一个反复唠叨、原地踏步的下场。”他认为,自然主义的追随者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撞在一堵死墙上”[10]。
左拉作为自然主义的旗手,当然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念,但早已另辟蹊径的于斯曼怎么可能再回头来尝试他认为庸俗不堪的老手法呢?
诚如本序言一开始便指出的那样,因为翻译困难的原因,国内多年来一直没有比较像样的《逆流》译本出版,直到201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才在国内首次推出了中译本,题目译为《逆天》,尹伟和戴巧翻译。
也正是在那一年,本人对《逆流》的翻译刚刚完成了初稿,为了在修改之前好好地冷静一下,我把译本初稿打印出来,搁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在当年秋带去法国作第一次修改。在法国,我开始在图书馆里修改译本,对照了至少三个版本的资料,还在书店里买了现有的两个版本,以方便回国后继续对照作第二遍修改。
在法国期间,我还仔细阅读了尹伟和戴巧的译本,从中获益颇多。同时,我也发现,这个译本中存在不少问题,包括疏漏和差错。尤其是对书名翻译成《逆天》,我颇有些纳闷。我想,译者这样译,大概想强调这部作品的“逆反”程度吧!
不过,思来想去,我还是坚持把书名翻译为《逆流》。其理由有四:一是法语原名为“à rebours”,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反方向地”、“逆向”,汉语中“逆流”已经有此意思了;二是,于斯曼另有作品《顺流》(à vau-l'eau),à vau-l'eau说的是“顺着水流的流向而走”,与《逆流》恰成对照,恰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逆流》为“《顺流》的一种对应物”,只是“被搬移到另一个世界中”而已[11];三是,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后来有言评价什么是《逆流》的“逆流”:“逆常识之流,逆道德感之流,逆理性之流,逆自然之流,这本书就是如此,像一把刮胡刀——但那是一把浸了毒液的刮胡刀——对准当代文学荒谬不堪与大逆不道的平淡无奇割下来”[12]。其四,主人公在丰特奈玫瑰镇隐居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而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这种较劲,准备“闭上眼睛,任凭自己被这股水流卷走”。他的行为属于“逆行”、“逆向”、“逆流”之类,恐怕还不至于到“大逆不道的”“逆天”。
记得,那是2010年秋天,为了更好地了解《逆流》的作者于斯曼,我趁访问法国的机会,在巴黎和郊区,游历了跟于斯曼有关的几处景点。
于斯曼出生在巴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那天我去见P.O.L.出版社的老板Paul Otchakovsky-Laurens(P.O.L.恰恰是他姓名的首写字母)。他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的,就是当年于斯曼出生的那栋房子:那是Suger街的9号。Paul Otchakovsky-Laurens先生热心地领我出后门,来到那9号的门前照相留念,并预祝我翻译《逆流》顺利。
又一日,我从Saint Placide地铁站出来办事时,专门绕道到Saint Placide街31号,那是于斯曼的故居。1907年5月12日,于斯曼就死在这栋楼里,享年不满一花甲。
另外,我还特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小镇丰特奈玫瑰。因为这是于斯曼写不朽小说《逆流》时,想象主人公所居住的地方。一经过丰特奈玫瑰镇的小树林,《逆流》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离巴黎那么近,却那么安静,这应该就是于斯曼的选择。告别巴黎,告别科学,告别自然主义流派,告别左拉;走向寂寞,走向孤独,走向神秘,走向象征森林。
最后,我还去了他的坟墓,那是在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墓地,第二墓区中,墓碑石上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形状的凸雕。
他的坟墓附近,就有不少法国作家长眠的安息处,如莫泊桑,如波德莱尔,前者曾是“梅塘集团”中于斯曼的同党,人们一说到于斯曼的《背包在肩》,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莫泊桑同样在梅塘小镇左拉的家中讲述的《羊脂球》;而波德莱尔则可被看作是于斯曼的精神导师,一本《恶之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逆流》。一百多年来,于斯曼始终与莫泊桑、波德莱尔为邻,而他的《逆流》,则在读者的心中,跟《羊脂球》和《恶之花》一样,标志着19世纪法国文学史的那一段: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现实走向神秘……
余中先
2011年圣诞节写于
北京蒲黄榆寓中
改定于2011年最后一天
注释:
[1]见作者序言(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
[2]见《理想藏书》(新版,余中先、余宁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3]见“作者序言”。
[4]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5]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6]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7]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8]见“作者序言”。
[9]见“作者序言”。
[10]见“作者序言”。
[11]见“作者序言”。
[12]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