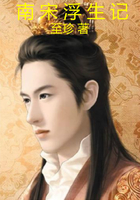树机能此时正率领步骑三万,猛攻位于山上的晋军。
十天前的武威一役,由于羌人倒戈,晋军被前后夹击,最终败退大青山。途中,牵弘被一支利箭射穿胸膛,登时气绝;苏愉虽力战突围,但苦于无法入城,只身逃亡东南方,沿途收拢残兵败将,意图在金城固守待援。但他没想到,氐、羌、鲜卑、匈奴等部见官军兵败,纷纷起兵响应,整个凉州烽烟四起。苏愉且战且退,在武威以北的金山被胡人团团围住。
两千晋军,这是凉州最后的兵力了,苏愉知道,已退无可退。
他命士兵砍伐三抱之树,以藤作结,在险要处构筑堡垒;砍下的树枝削尖,置于隐蔽坑中,形成数道防线;同时组织敢死之士,趁夜向山下发起突袭,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圈,敌军太多了。
鲜卑人发起一波又一波冲锋,先是擅长骑术的匈奴兵,后是民风彪悍的氐人,最后是鲜卑兵。山高林密,骑兵往往被藤葛绊住,躲在壕堑后面的晋军趁机放箭,射死不少匈奴人。匈奴人退却后,氐人手持短刀,举着大圆盾牌,以扇形阵势前进,沿途破坏晋军的防御工事,将晋军压迫在山顶周围极为狭小的区域。
苏愉见状,组织五百死士,以迅雷之势猛冲,氐人抵挡不住,四散奔逃。树机能见状,立即在山下建造拒马桩,并拉出丈余弩床,对准倾泻而下的晋军骑兵,刹那间,哭喊声,嘶鸣声响彻山谷。
双方激战数日,鲜卑人折了近万人,还是没能攻下山头,树机能望着山间犬牙交错的堡垒,很伤脑筋。在他看来,晋军好比肥羊,开始味道鲜美,越往后,骨头越难啃——汉人都一个德性。但不管多难啃,树机能都要磨碎它,他们是草原上的群狼。
这天傍晚时分,山脚燃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刹那间浓烟滚滚。
五十里外的司马攸看到了这把火,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把火在烧。司马攸狂吼着,命令晋军不顾一切急行军。
当晋军到达山脚时,浓烟已经铺天盖地,山,人,河流,一切都隐没在浓烟中,山间静悄悄的,只听见树木着火时的噼啪声,空气中弥漫着焦臭、血腥的味道。司马攸抵近观察,发现一面正在燃烧的信帜,他依稀辨认出,上面写着“苏”字。
坏了,是苏愉!司马攸猛然醒悟过来,狠抽自己一巴掌,苏愉苦苦等待的援军,正是他们啊!
正当司马攸痛心疾首时,斥候疾驰来报,山脚南面二十里处,发现鲜卑人踪迹。
于是,晋军变成了一支离弦之箭,张轨率领一千骑兵身先士卒,不过一炷香工夫便冲破敌军防线。大胜之后,鲜卑人正洋洋得意,或整理盔甲,或聚成一圈手舞足蹈,对晋军的到来竟毫无防范。树机能听得帐外杀声四起,急惶惶披甲出帐,只见一名须发皆白的老将军手执长枪身先士卒,先后横扫数名鲜卑兵,正向中军帐杀来。
树机能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手忙脚乱地骑上一匹马,向西奔逃。众人见主帅逃跑,军心大乱,两万多人如潮水般溃退,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直到东天泛白,杀喊声才渐渐止歇。
战后清点战果,是役,共斩获头颅一万,而晋军损失三百人。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大胜仗。兵士们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小土包,上面立着一块树皮“墓碑”,潦草的汉文写着,晋将苏愉之墓。看来鲜卑人崇尚勇士,没有难为这位敌将的尸体。
司马攸命人将坟茔陪土,重新刻了碑,并亲笔手书:凉州刺史苏愉之墓,晋太康二年九月,甲戌,晋大将军、齐王司马攸立。
晋军众将士,在墓碑前长揖不起。
虽然打了胜仗,司马攸却高兴不起来。不是有五万精锐吗,不是有身经百战的牵弘吗,不是有武威,张掖,酒泉好几座坚城吗,秃发氏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吗,凉州战事怎么发展到如此地步?司马攸连连发问,既问长眠地下的牵弘、苏愉,也是问他自己。
来不及寻找答案,他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武威周边城防,相机收回张掖城。然后想法设法寻找援军抑或盟友,否则以这丁点人,别说廓清凉州,就连武威都守不住。鲜卑人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
清理完战场,司马攸率军入了城。
武威也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大战,瓮城城楼和正面城墙已然倒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主城墙上的垛口、箭楼毁得七七八八;地面上随处可见凝固的赭红色的血斑;两扇铁桦木城门裂成四半,上面却极其平整,并无刀斧痕迹。
战场被收拾过,但极为匆忙,角落里还能看到未及掩埋的尸体,正散发着浓郁的恶臭。从相貌装束上看,有汉军,有鲜卑人,也有羌人和其他不辨种族的人。
昔日里熙熙攘攘的武威城,已成一座死城。
有件事令司马攸心生疑窦,胡人最不善攻城,但从战场来看,战事主要发生在城内,城门应该是须臾间被突破的,晋军人数不少,不致败得如此迅速。
文鸯看出了司马攸的心思,道,“这不是胡人攻城,而是我们。”他指着墙角两具扭曲在一起的尸体,继续说下去:
“这两具尸体,一个羌人,一个汉人,两人铠甲兵器都一样,说明这个羌人不是秃发部属,而是为我军效力的羌人。”
“难道是羌人反叛?”
“没错,我猜应该是城中主将领兵出战,但不久后城内羌人便发动叛乱,并紧闭城门。将士们不得已掉头进攻叛军,你看那具尸体。”顺着文鸯手指的方向,司马攸看到一个羌人,脑门中箭,匐在垛口。
“正当我军清理门户时,一支鲜卑大军刚好赶到,我军虽经力战,但还是无法抵挡兵势浩大的鲜卑人,最后只得败退。”文鸯带司马攸登上城墙,望向城外,那里是一片杂草地,其间有凌乱践踏的痕迹,还有一些长戟、铠甲,延伸百十余丈后上了大路,再也不知去向。
司马攸沉默良久,说,“传令下去,将我军阵亡士兵好生掩埋,立碑四时拜祭,其他人一把火全烧了。”
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司马攸站在城头上,再一次扪心自问。他出发前就听卫瓘说过凉州局势恶化,对此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他万万没想到,武威居然都差点丢了。数月前,凉州还有五万晋军,可目前就三千人不到。
从武威往西,依次是是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四郡共同控制着河西走廊。而武威则处于雍凉相接的咽喉地带,一旦武威失守,就会切断整个凉州和雍州的联系,晋帝国就再也无法经略西域,等于壮士失去一条手臂。
司马攸悲不自胜,身边的张轨、李良等人也心境不佳,众将都笼罩在一片失败,彷徨的悲观情绪中。大家默默地看着士兵们搬运尸体,收集武器,都不言语。
文老将军倒是看得开,云淡风轻地说:“行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凉州烽烟四起,以后还会死比这多得多的人,当务之急,是巩固武威城防,以防随时都会卷土重来的鲜卑人。”
紧接着,文鸯集合士兵,下令,“即刻修缮城墙,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