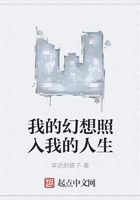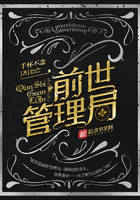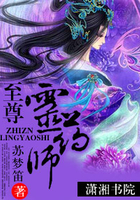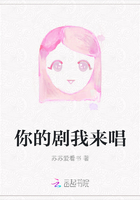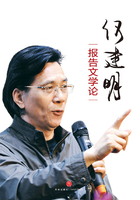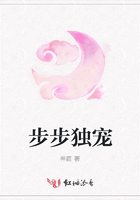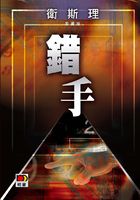卜德星家里没人——铁将军把门。
岳树仁心里凉了半截,莫非卜计划家真的出事了?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呢?
岳树仁加快脚步,心急火燎地向村南头拖拉机厂跑去。
厂子同样是大门紧闭。
岳树仁进不去,只好透过铁栏杆大门向厂子里探头探脑地张望。
往日机器轰鸣、车水马龙的局面无影无踪,除了几只鸽子在水泥地上悠闲地踱步外,最忙的就是一群又一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吵翻了天:在厂房顶上、在车间门前、在高入云天的水杉树冠里、在的灌木丛中。
岳树仁正在大门外伤感惆怅,这时传达室的门开了,走出了看门护院的老金,50多岁,岳树仁认识,一个村子的。
岳树仁赶紧走过去搭讪。
但人家一问三不知。
再问也没用,他什么也不会透漏,一脸糊涂的人往往心里都明镜似的,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岳树仁没有再为难老金,并且打心眼里欣赏他,看门的就要这样的,该看的一个地方也不会落下,这叫眼里不揉沙子。
不能说的一个字都不露,打死也不说,这叫忠诚。
一无所获的岳树仁离开振华拖拉机厂,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琅村是琅镇的驻地村,有两横两纵四条主街,井字型分布。
紧锁的厂门和卜家的房门影响了岳树仁的心情,昨晚上又和田蜜蜜聊得不愉快,他百无聊赖,不知如何是好。
无处可去的时候,家就是归处。
岳树仁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家门,只有母亲在家,父亲下地了,兄弟们不知上哪淘气去了。
见树仁进门,也不问候自己,高胜男脸上顿感不悦,略带责备的口气说道:“这一大早晨的去哪了?走的时候像个哑巴,也不说一声。”
“我去找战友卜德星,人没在家,家里还锁着门。妈,有饭没有?我饿了。”
岳树仁没注意母亲表情的变化,他在这些细枝末节的事上心粗,头不抬眼不睁地往屋里走,边走边回答着。
“饿了才想起叫妈,我还以为你妈死了呢!在锅里给你留着呢。”母亲没好气地说。
母亲一直想不通一件事,就是岳树仁小的时候,在兄弟姊妹中小嘴最甜,不管再苦再累,回家听到老大带着弟弟妹妹响亮地叫一声“妈——”什么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可不知何时起,她隐约想着是他当兵回来之后,几乎听不到见面的那声“妈——”
天下做母亲的,总是最喜欢自己孩子小的时候,要是孩子长不大就好了。
天下做儿女的,只要母亲健在,真的永远也长不大,一百岁了也想要个娘呢!
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岳树仁前脚刚进了屋,洗完手坐下,母亲后脚紧跟着端着木制饭盘子进来,上面摆着他最爱吃的大米饭、炒豆角和炒茄子。
虽然琅琊以面食为主,但是岳树仁从小养成了吃大米的生活习惯。主要原因是岳忠儒在1960年人饿的时候,闯东北去了,孩子们都是东北生人。
回琅琊的时候,老大已经十七八岁,口味是出窑的砖——定型了。
看着老大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大米饭,坐在对面的母亲嗔怪道:“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就着茄子和豆角,全吃完了,到中午就酸了。”
眼见老大还是一个劲地扒饭,母亲从饭桌上端起茄子来,一古脑儿地倒进他的饭碗里,嘴里还不饶人:
“跟你说话就当是耳旁风,剩下给谁吃啊。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可别光想着战友啊,抽空去你舅家串串门。”
岳树仁:“知道了。妈,你听说咱们村的拖拉机厂关门的事吗?倒底是怎么回事?”
母亲摇了摇头,说道:“我不太清楚,大家都传瞎话,谁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对了,你舅和厂长卜计划好的像一个人似的,两个人一直走得挺近的,去你舅家的时候,顺便打听一下呗。”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岳树仁,他如获至宝,放下碗筷就要走,但被母亲强行拦下,直到把两盘子菜吃了个底朝天,这才放行。
岳树仁的舅舅家在营里村,与琅村相邻,都归琅镇管辖。
岳树仁骑着自行车走到了半路上才想起来,舅舅是在外面卖炒货,不知道回家了没有。
转念又一想,反正也走了一半路了,舅舅没在家就看望一下舅母。
说句良心话,自己的工作一忙开,整天价昏天黑地的,除了逢年过节,亲戚之间走动得越来越少了。
不光是岳树仁是个大忙人,他舅舅高希利更是个扒家虎,不但睁着眼忙,就连睡觉做梦都要往家里划拉东西。
说起高希利,就得从根上刨一刨他那贫瘠的家史:他家不是坐地户,是他奶奶带着三个男孩子改嫁来到营里村,这个后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人,也没有硬逼着三个孩子随他姓,仍旧姓高。
不是后爷爷心狠,实在是家中太穷,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三个张口兽把后爷爷啃成了皮包骨头。万般无奈,孩子只要长得有了牵牛的力气,不管他是七岁还是九岁,就送到本村地主卜守田家里去当长工。
就这样,毫无悬念,哥仨陆续成了给营里村地主扛长活的三个长工。三个长工三杆枪,三个光棍一样长。当最小的光棍也过了四十的时候,生存已经不是危机,灭种才是真正的灾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继续这么光下去,这一支人家可就断子绝孙,房倒屋塌了。三个光棍没了指望,开始消极怠工。地主老财一下子慌了神,他的神仙日子靠这三个光棍撑门面。说心里话,给三个骡子也不换。
地主老财号准了光棍的脉,心里有了底,托媒婆给最小的老光棍买回一个黄花大闺女做老婆,价钱是大洋一百块。
这么些年下来,三个光棍嘴里不吃、腚里不拉,总共才攒了七十二块大洋,买人家闺女又不能赊账,这可愁坏了老哥仨。好人做到底,卜守田咬咬牙,借给了光棍三十个大洋,当然要从工钱里扣的,总算凑够了一百块。
旧社会也是人间,谁家卖闺女?除了吃不上饭的,就是不正干的。这个闺女姓苏,她爹是个远近闻名的赌徒,从来没赢回儿,大闺女已经卖了还了赌债。卖了大闺女,也就不差二闺女,早晚是人家的人。
这一百块钱可是个高价,门当户对的小户人家娶个媳妇也用不了五十个大洋的聘礼。
老苏明知老光棍比自己年龄都大,好白菜也舍不得让猪拱了,但赌债堆得比自己的个子还高,不要个高价也还不上啊?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白花花的现大洋的面子上,就把这娇嫩嫩的花骨朵插到那堆老牛粪上吧。
苏家二闺女如何情愿,怎能不投井上吊,寻死觅活?
人不该死,阎王不收。苏二闺女把自己折磨得心灰意冷,死不如生后,再懒着与命运作无谓的挣扎。认命了,自己不就是一块地嘛,长工愿意种地他就种吧,反正有的是种子,种瓜给他长瓜,种豆给他长豆。
老天有时喜欢捉弄人,你让他往东他偏向西,你让他打狗他却去打鸡。三个光棍花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又透支了下半辈子的收入,巴望着买回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想到,接连生下了三个闺女。
地没事,牛却累得趴窝了,没有犁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足足歇了六年,地里才长出个带把的,他就是高希利。
这孩子生日好,端午节那一天,全国人民给他过生日,他还不知足,从娘胎里出来就嚎哭不止,声震寰宇,哭得老蒋心烦意乱,无心恋战,最后跑到台湾躲起来。
老哥仨守着这么一个独苗苗,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真不知怎么对他好才是好,只要他高兴,叫他爷爷都成。
倒也是,要是论年龄,老哥仨都能当他爷爷。不是还有三个闺女吗?
哎!谁想要她们了,只是不好掐死。活着就得穿花衣,吃白饭,长大就是泼出去的水。
为了给高希利提供更好的生活,哥仨不顾高苏氏的反对,强行将第三个闺女送给一个远房亲戚。
也许是高希利命硬,也许是时乖命蹇,也许是个人的寿命由天,高希利步履蹒跚地生长,老哥仨一个个东倒西歪,陆续撒手人寰。紧跟着高苏氏也恋恋不舍地命赴黄泉。转眼的工夫,高希利成了一名孤儿,这一年,他八岁。
大姐嫁人了,自顾不暇,想管也管不了多少,二姐高胜男也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高希利从众星捧月的宠儿,到无父无母的孤儿,再到走街串巷的乞儿,人生命运的反转有时真像魔法一般,说变就变,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
高希利到底经历了多少苦难,有些事人看到了,有些事,他不说,永远没人知道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埋藏了无数的秘密,不会对任何人说的秘密。
高希利从大年初一开始饿肚子,数着太阳过日子,到了年三十也没吃过顿饱饭。对饥饿的恐惧深入骨髓,只要是看到可以吃的东西,他的眼睛就会像狼发现猎物一样,放射出绿光,那是一种无所顾及的占有欲望、没有是非的本能贪婪。
当然,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环境和时机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温度,再恶毒的种子也不会生根发芽。
高希利靠着吃百家饭长大,娶了满意的媳妇,生命力非常旺盛,要不是计划生育抓得紧,二胎应该会打酱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