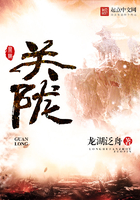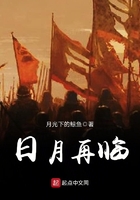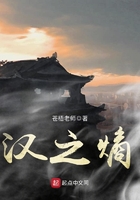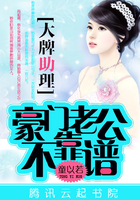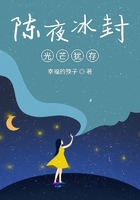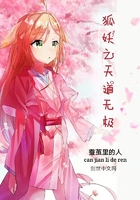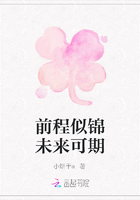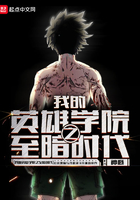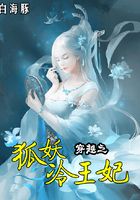《雪景寒林图》的真伪
北宋前期画家范宽的名作《雪景寒林图》再现,令人兴奋。不过画上有“臣范宽制”四字的题款,又令人迷惑,甚至有学者怀疑此画是否为范宽的真迹。引起书画鉴赏家们的一些争论,其中疑难处在哪里?为何令人费解呢?
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这件古代绘画珍品原系民间私人收藏,“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抄家物资转入博物馆。“文革”结束,北京举行“各省市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此画最引人瞩目。因为范宽传世之作有《溪山行旅图》《秋山萧寺图》和《雪山楼观图》等,此画却久已湮没,突然面世,令人惊异,这画是真迹吗?
雪景寒林图范宽生于五代末,耀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有关画史类书籍所记,其仪状峭古,举止疏野,嗜酒好道。至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犹在,一生失意潦倒而不得志,“落魄不拘世故”,常来往于汴京与雍洛之间。工山水画,曾师从荆浩、李成,后悟“师人不如师物,师物不如师心”。卜居终南山、太华山,终日危坐,纵目四顾,饱览岩壑云烟,随后雄健落笔,独辟蹊径地塑造着峰峦浑厚、气势雄伟的关陕山川形象,最终自成一家。北宋前期,与李成、关仝为北方三大山水画派的代表,后人评其“得山之骨”,尤长雪山之景,使人见之凛凛,只感寒气逼人。米芾《画史》评之为“本朝自无人出其右”。
《雪景寒林图》是绢本水墨山水大立轴,长一百九十五厘米,宽一百六十厘米。以老辣沉稳的笔墨表现了大雪覆盖下的北方山水奇观:主峰高耸,群峰屏立,山势嵯峨,岩壑幽深,有河朔气象。山头遍作寒柯,通幅一无杂树。山腰萧寺,危径长桥,皆得自然。瑞雪满坡,寒林孤秀,物态冰凝,俨然三冬在目。山下岩体棱角分明,岸边有大树数重,后有村居,一人张门而望。空间虚实相应,笔法苍润雄伟,加上其淡墨烘染出的阴霾气候,都显示出作者确为写生妙手,体现出高深的艺术造诣。
从《雪景寒林图》的近景看,树干上隐约有“臣范宽制”四字。按上述范宽生平和脾性,也未闻其曾被召入宫廷,那为什么称“臣”呢?同时,范宽是否名“宽”也存在疑问。据《圣朝名画评》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华原人,性温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图画见闻志》“范宽”条有注:“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宣和画谱》也说:“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蔡卞尝题其画云,关中人谓性缓为宽,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语行,故世传范宽山水。”似乎都表明这“宽”不是他的本名,是时人以他的脾性而称他为“宽”,因而使他的真名反而被淹没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也载:范宽“原名中正,字仲立(一作中立)。性豁达大度,人呼之为范宽,本名反不显。”
由是,著名书画鉴赏家启功先生写了《鉴定书画二三例》一文,认为《雪景寒林图》确是范宽的画法,三拼绢幅也是宋画的特点。但从此画的题款来看,此图应是宋代范派的作品,而不是范宽的真迹。宋画多半无款,这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此画中的一株大树干上却有“臣范宽制”四字,纯属画蛇添足。同时,范宽只是时人称他的一个诨号,他会将诨号题为画款吗?就如包拯会自称“包黑”这个诨号吗?此外,这个“臣”字也大有疑问,以范宽生平和举止而言,他就是题画款,也不会称“臣”。
陈传席《〈雪景寒林图〉应是范宽作品》一文提出商榷,认为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范宽条是写:“范宽,字中立,华原人,工画山水。”“宽”为其名,“中立”其字。记载并不含糊。而且古人的名和字是相配的,名“宽”配字“中立”也颇相合,倒是所谓“名中正,字中立”有点不配。而“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只是其条后的一个小注。其不作正文,表明只是出于传说。而后人不辨真伪,以此传说为真,有关记载大抵皆根据《图画见闻志》那一条小注的传闻,这种说法应属误传。如米芾是北宋人,不可能不知道范宽的名字,然而他的《画史》所记,皆用“范宽”,显然并不以此为诨号。
其实,范宽在自己画上题款并非只此一件。如米芾曾在丹徒(今江苏镇江)僧房里见到一幅如荆浩风格的山水画,“于瀑水边题‘华原范宽’,乃少年时所作。”米芾是当时的书画大鉴赏家,他岂有搞错之理,可见范宽少年作画就已有题款的习惯,且自题“范宽”,“宽”必是其名,而非诨号。最有力的证明是,台湾学者也在肯定是范宽真迹的《溪山行旅图》上发现了“范宽”的款字,该画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艺苑掇英》第十五辑有文载,其图右下树阴处有“范宽”二字。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范宽性宽厚,只能说是人如其名,而并非因性格而得名。一些专家从作品的用笔风格上也认定,《雪景寒林图》和诸画史记载的范宽作品风格尚没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应看作是范宽真迹。
唯独这“臣”字还是令人费解,这是其他画上所没有的,从逻辑上分析,范宽不应以“臣”自称,此画也非献给皇帝之作品,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会由后人添加的呢?另外,范宽的名字问题,上面的解释也并不是已毫无疑问。毕竟《图画见闻志》没有明确“宽”就为其名,后注只是传说,其他诸书也未必尽抄《图画见闻志》。当然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仅凭这些怀疑是不能轻易否定此画的作者是范宽的,只是此题款确实存在一定的疑问。目前书画界有持肯定论者,也有不置可否者。
柳永人品与作品
柳永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词作家,是第一个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的专业词人,其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词的创作。他的词吸收了许多民间俚言口语,通俗易懂,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风气。且精通音律,善于铺叙,曲尽委婉,对宋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流传至今的《乐章集》,保存有近二百首词作,是一位有着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家。然而人们对其作品和人品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甚至差之千里,也可谓一历史之谜。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其生年不详,或说雍熙四年(987),或说景德元年(1004),莫判孰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七,世人或称柳七。出身于一个重儒世宦家庭,少年生活在京都开封。时代和环境给他安排的出路,无非只是熟读圣贤书,然后于科场追逐名利。但是,柳永有“善为歌辞”的天才,于是他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社会,融入民间,成为乐工的朋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柳永为此结识了许多青楼歌妓,为她们填词作曲,尽心尽才,有求必应。其词作在内容上颇有特色,艺术上的造诣更是不俗,传播很广,有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时蜚声朝野。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柳永又不得不走科举应试之路,但此路走得十分辛苦和坎坷。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载:“(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撰《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写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坊。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确很有个性。怀才不遇,科场失意使他激愤填膺,转而对功名富贵采取冷淡和狂傲的态度,常常以“自衣卿相”自居,把功名官位看成“浮名”,还不如“浅斟低唱”、“偎红倚翠”畅快。怪不得宋仁宗看了非常反感,特意排斥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薄子纵游娼诸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由于最高当局的不满与打压,柳永屡试不第,流浪于开封、苏州、杭州等大都市,在秦楼楚馆中讨生活,依然以填词作曲为娱,与歌妓们流连忘返,使柳永有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从而替她们唱出对所受凌辱和践踏的控诉,同时寻求生活的安慰。其中,乐工借柳永传其新制乐曲,妓者藉柳永增其缠头声价,柳永也凭她们远扬才名,可谓相得益彰,风流倜傥。
据说,直到景祐元年(1034),柳永方才及第,遂改名永,字耆卿。以后,只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昌国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和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故亦柳屯田。然而其仕途仍很渺茫,游宦生活飘泊不定,充满辛酸。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皇祐年间,柳永已近人生晚年,天上出现老人星,时以为是“祥瑞”。一位姓史的宦官,爱惜柳永之才而怜其潦倒,再次向仁宗推荐,拿着柳永甚为得意之作《醉蓬莱》词给仁宗看,以期获取欢心,以助其仕途升迁。哪料词中有“此际宸游,风辇何处”一句,刚巧同仁宗悼念其父真宗的挽词相合;又有“太液波翻”一语,仁宗过于敏感,以为“翻”字不祥,看后竟气愤地将词稿扔在了地上。
有学者认为,上述事件应发生在柳永“久困选调”的庆历三年(1043)。张舜民《画墁录》说:“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由是其仕途不顺,一再受到阻碍,长期沉沦下僚。柳永大约病死于皇祐五至六年(1053或者1054),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从北宋开始,人们对其词作就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载,当时对柳词评价相当高的文人,有“《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说法;对柳词诟骂最甚的宋代文人,则有“遭柳永野狐涎之毒”的说法。那么,其词作本身是否存在如此的复杂性呢?
当时的上层社会,包括仁宗皇帝、宰臣晏殊在内,众口执词,大都攻击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封建正统派的理学家们都指责他在科场失意后,便沉沦于都市繁华的诱惑中,只追求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创作一些淫歌艳曲。此后,一些自命高雅的文人,也往往贬斥“柳耆卿曲俗”。总之,历来自命高雅的士人们对于柳词“颇以俗为病”,对其内容和格调大多持否定态度。最多说柳词在艺术上有所独创,促进了慢词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此而已。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云:“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
近现代以来,许多人仍认为,柳永是一个没落士大夫阶级的浪子,其主要精力都耗费在“偎红倚翠”放荡不羁的生活中,同时创作了大量的“猥词”,思想颓废,趣味低级。他也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以玩弄的态度对待妓女,描写中充满了色情的东西。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如此指责柳永,说他“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他们唱为喜乐”,“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说是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他的词大都在‘浅斟低唱’之时写成的,他的灵魂大都发之于‘倚红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题材大都是恋情别绪,他的词作大都是对妓女少妇而发的,或代少妇妓女而写的。”
然而,也有学者对柳永的作品与人品,持相当肯定的正面评价。指出封建社会根本不把妓女当人看待,宋代更是妓馆林立,士大夫狎妓成风,只把妓女当作玩物、货品,任意买卖、转赠乃至处罚。就像苏东坡这样温文尔雅的官员加文豪,也没有什么例外。而柳永的词却不鄙视她们,写出对她们的同情,给她们以人的应有地位。他置身于妓女、乐工间,同她(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她们作歌,付出辛勤劳动,实际上成为她们谋取生活的得力助手,这与一般纨绔子弟青楼买笑、寻欢作乐完全不同。
柳永叙写妓女的理想与要求,表达她们的苦闷心情,其中对妓女的苦难遭遇深表同情,如《燕归来》词中描写被侮辱的妓女的处境时,“肠成结,泪盈襟”。在描写妓女的技艺时,也是采用欣赏与歌颂的笔法,如在《木兰花》中对其歌舞技艺的赞美。在谈到自己与妓女的关系时,大都感情真挚,没有虚饰的玩弄态度,如《雨霖铃》中“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大量的怀妓作品中,同样表现出把妓女当作知己的心情,如《洞仙歌》中“共有海约山盟”;《十二时·秋夜》中“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视妓女为知己,因而也受到她们的爱戴。相传柳永“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每寿日上冢,谓之吊柳七”。(《方舆胜览》卷十一)
柳永以妓女为题材的词作中,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风流韵事的描写,甚至有些语句写得近乎色情。但是,一则这类作品在柳词中所占比重不大;二则其描写时仍将妓女置于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与其他士大夫玩弄妓女的态度相异。所以,他的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尤其在下层民众间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在士大夫中,也有人相当赏识柳永,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载,苏东坡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将柳永与秦少游等同看待。前面提到时人还有把柳词比作“离骚”,也有人把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他的《鬻海歌》,柳永作为晓峰盐场的监官,却能够站在制盐民户的立场上,描写其艰苦的劳作和穷困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抨击官府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大声疾呼:“鬻海之民何苦辛!”要求改变有关的榷盐制度,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地方官吏对民瘼的深切关注和真挚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是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一般以为,柳永由于怀才不遇,科场失意,转而对追求功名富贵不以为然地进行嘲弄。他的词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非议,吐出“图利禄,殆非长策”诸语,以为“才子词人,真是白衣卿相”,从而对“蝇头利禄、蜗角功名”颇为冷漠鄙夷,逐渐看破红尘,绝意仕进,专以填词作曲为业。如他在《西江月》中依然如此自嘲:
腹内胎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片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上述自嘲只是其仕途失意时的几句牢骚,谈不上是对科举功名的一种反抗。前引《鹤冲天》一词,也同样表现了落第后自嘲自解的一种心情,在故作旷达的背后,不难看出其深深的遗憾和日后为榜上“龙头”的潜在企望。柳永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清高超脱,相反常常为谋个一官半职,会费尽心机地拉关系、走后门,甚至求助于和他结交的那些歌妓。《青泥莲花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早年和柳永有过交往的孙何,官任杭州太守,柳永很想求见,以图推荐,但官府“门禁甚严”,一直无缘求见。于是作《望海潮》一词,盛赞杭州的繁华与美景,其中隐约透露出当地官员的儒雅风度和前程无限。写好后,就拿着去见名妓楚楚,恳求道:“想见孙太守,恨无门路,愿借朱唇歌于孙前,若问谁作此词,但说柳永。”果然,孙太守听了楚楚的歌,非常高兴,终于接见了柳永。此后,柳永的放荡生活开始收敛,狂胆怪情也逐步消减,经过认真准备和故友帮助,考取进士,在浙江诸地做了几任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