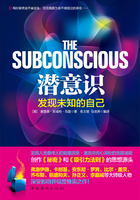张蓉萱1966年,出生在东北的新城市,那是一座以煤炭等重工业为主的四线城市。当年,因富饶的煤炭资源,曾吸引了无数闯关东的人们驻足此地,并在此安家立业。
蓉萱的父亲张柏祥,就是1952年,从内蒙的老家,穿坏了堂姐给他做的两双布鞋,最后赤着脚,走到新城市的。
那年,他32岁,父亲哥三个,他的两个哥哥,二十多岁就患上了疾病,只有大哥,留下了一个儿子之后,哥俩相继去世,蓉萱的爷爷,也是早年就去世了,只剩下她的父亲和奶奶。
父亲到新城,是投奔他的堂兄张柏顺。张柏顺在矿务局局库工作,他的二弟张柏林,也跟他一起到的新城,他们两家住在前后院,张柏林比张柏祥小几岁。经堂兄介绍,父亲进南岭煤矿当了一名矿工,离堂兄家三十多里地,住在了矿里的宿舍。
父亲从小就给地主扛活,家里很穷,三十多岁了,也没能娶上媳妇。工作两年后,矿里给了他一间平方,之后,又经堂兄介绍,认识了蓉萱的母亲江慧兰。
母亲也是内蒙人,比父亲小两岁,她温和、贤良,裹着小脚,从不多言多语,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儿,就是蓉萱的大姐蓉芳。蓉芳比蓉萱大十八岁,她憨厚、诚实、心眼直,跟母亲的性格相似,父亲对她是视如己出。母亲没有工作,一直在家做家务。
1957年,母亲又生下了蓉茵,蓉茵从小就活泼好动、聪明伶俐,很是招人喜欢,长大后,是同龄姐妹中的核心人物,经常领着一群伙伴,在房山头唱歌跳舞。
1963年,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惜的是,只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之后,就生了蓉萱,蓉萱的性格,介于两个姐姐之间,偏静一些,不喜欢张扬,张柏祥就这么三个女儿。
蓉茵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跟一个邻居吵架,那个人骂父亲是老绝户,从那时起,蓉茵就下决心,一定要比男人都强势,绝不让人欺负。
父亲体弱多病,二十多岁就得了肺气肿、气管炎,还有十二指肠溃疡。他四十六岁才有的蓉萱,那时候,他就风趣的说:“我把这个老丫头,拉扯到能领着她妈妈拿着棍子打狗要饭的时候,我就死也知足了。”
蓉萱两岁多的时候,起了麻疹,大姐和父母,抱着她去矿里的职工医院,几经周折之后,才转往传染病院,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救护车开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母亲还把手放在她的鼻孔处,试试还有没有气儿。
还好,到了医院,经过抢救,她终于转危为安,接着,又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痊愈回家,一家人皆大欢喜。
蓉萱四岁那年,大姐就从下乡的地方出嫁了,是爸爸的一个表侄儿钟向臣做的媒,大姐夫马庆恩的家,在临省的柳河市,是一个县级市,两年以后,大姐随着回城的姐夫去了柳河,姐夫也当了煤矿工人。
大姐跟妈妈一样,就上了几个月的班,然后做家务,她每隔个半年左右,回娘家一次,可能是妈妈的翻版,蓉芳同样也是生了三个女儿。
1974年,蓉萱上学了,那时候,小学的一、二年级在抗大,她梳着两条小辫子,文静、腼腆、沉默寡言,只知道学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晚上临放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检查作业,之后,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张蓉萱,你可以放学走了,其他同学全部留下。”
蓉萱蹑手蹑脚的,背着小黄书包走出了教室。回到家里,她跟爸妈学了这件事,他们都很高兴,高兴的是,家里要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了。
蓉萱的父母都没念过书,母亲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父亲却能看大书,尤其爱看《水浒传》,甚至连里面的繁体字,也认识个十之七八,他说是工作后,只上了两个月的夜校学的。
他们当然希望女儿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蓉萱凭着学习成绩,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父母都为之骄傲。
三年级的时候,她们才进了真正的小学校门,她依然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就在这一年,蓉茵中学毕业下乡了,她在青年点也是很泼辣,有一次跟一个男同学打架,竟然用大棒子伦人家,弄得没人敢惹她。
蓉茵下乡也就半年多,父亲因身体不好,办了病退,让她回城接班。蓉茵上班后,被分配到矿职工食堂,一年多以后,被调到了行管科做出纳。
蓉萱也长大了不少,辫子也留到了齐腰长,依然是少言寡语,但是,她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父母从不操心她的学习,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也都夸她是个好孩子。
1979年秋天,蓉茵最好的同学李蓉慧,给蓉茵介绍了个对象,是她哥哥的同学,叫吴忠义,就住在蓉茵家附近,他母亲去世了,父亲带着他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在矿里的工资科工作,比蓉茵大两岁,细高的身材,白白净净的,比蓉茵高二十公分。
蓉茵是姐妹三个中唯一长的黑的,一米五五的个子,还稍微有点O形腿,但是她长了一双欧式眼,模样比蓉芳和蓉萱好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点,第二年冬天,登记结婚。
她们没有举行婚礼,去北京旅行结的婚。一周后回来,父亲宴请了几桌亲戚、朋友。蓉萱看到二姐的眼眶是青着的,但是谁问,她也不说怎么回事。
她们结婚不到一年,因为煤矿多年的开采,出现煤炭贫瘠,所以,百分之七十的职工,被集体迁移到了离新城一百多公里的广原市的煤矿,蓉茵两口子也在其中。
说是城市,其实那里就是一个小城镇,蓉茵她们所在的煤矿,周边都是农村,到那后,她们都得住集体宿舍,蓉茵她们走的那天,蓉萱拉着二姐,哭的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