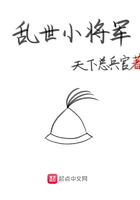屋顶的积雪没有消,天色却逐渐暖和起来,日头发着新光,枝叶上残留的那些雪逐渐融化了滴落在路上,若不是日头底下还吹着寒风,这泥泞的路,也结不出细细碎碎的冰凌来吧?
护送怀吉归来的马车远远地就发出“嘚嘚”的小步子奔跑的声音,是安坐在马车里头,从早上等到下午。
李乙已经派了人上去问话。
“怎么到的这么晚?”
“过了两座山,路泥着,怕马滑了,惊着中贵人。”来人带着浓厚的西京口音。
是安掀开车帘子,怀吉已从那青布车上下来,朝她走过来。
衣裳像是新浆的,头上的软脚幞头边也见用兔毛围了,他就近了,又躬起身子来,“公子。”
是他的声音,他却没抬起头。
“怀吉哥哥?”
他这时才微微抬了头,便是这一二年间,额上便有这样深的皱纹吗?没有旧日白些,也没有旧日那么瘦弱了,不知是穿的厚,还是真壮些了,眉梢的韵气还在,周身却散着又叫人熟悉又叫人不熟悉的气息。
李乙扶了他到马车上坐下,他倒是依言上来了,坐的这样近,两个人又这样远。
“哥哥,一路还好吧?”
他带着笑,低着头,是当年小内监的神色,“都好,都好。”
是安递了自己手炉递给他,“不大热了,哥哥将就些。”
他矮着身子接过去,终于抬起头,好好地笑一下,“公子,壮些了”。
是安不由也跟着一笑,“是了,有些黑,有些糙呢!”
怀吉的眼睛放在她腿上那一双手上,虎口处隐隐见着茧子,他的眼神一时又不自在起来,“直接进宫吗?”
是安将自己身上盖得毯子往他那里拉些,又费力将脚边的暖炉也朝他那边移了移,“先去我园子里,不急,先去我园子里歇歇。”她想叫他见见钟巘,也见见她旧日说过的梦溪后头的亭子和小楼。
怀吉的手握着只有微微一点的温的手炉,脚边上的暖炉贴着他的小腿,起先也没什么直觉,慢慢地才温热起来。
“还是直接进宫吧。”
公主还在宫里等着他呢!
洛阳不远,东京的事,总有人来回通传,内监婢女们看他的神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有程侯一封一封的书信和物件不停地从东京往来飞,便也没什么人为难他,只是大家也不大理他。
他负责清扫离宫一段不算长的甬路,时时想起他同程侯幼年的日子,他拘谨着,程侯也拘谨着。
也总做梦,梦到他牵着程侯的手从甬道里走,走去各宫娘娘们的居所,走到福宁殿去,走到崇文馆里。程侯的小手软乎乎地,夏日里总浸着汗,他蹲下身子,从怀里抽出一方丝巾来,替她一点一点细细地擦干净。
手里的帕子是嬷嬷亲手缝的,柔柔软软,那帕子后来不知怎么就变作了上好丝罗的那一方,隐隐透出一个“吉”字,是那年公主绣给程侯时,也特意绣给他的。
程侯出宫去后,将他托付给公主,她那时已经袅袅婷婷的很有贵人的样子,只是还是一阵风似得。
赤着脚、散着头发就往御花园里去了,有的时候不知从哪踩着一脚泥,有的时候又被花园里的树勾了裙子,她也不恼,笑哈哈地擎着一朵花来,“你看你看,怀吉哥哥,我说它今日要开的。”
他心疼那朵花才开就被她折了去,面上也只能躬着身子应是。
婢女打了水给她擦脚,她便将那花随意一扔道,“你为何不说我?倘使安儿折了,你也不说她吗?”
他心里只默默地想:公子若见着一花开,便是很喜欢,也要三而再地思虑半晌,终究也不忍心折了去。
她不见他的回答,也不管婢女才为她洗干净一双脚,又踩到地上三两步朝他走过来,神色带些得意,“安儿叫我发了誓好好待你呢,没叫你发个誓也好好待我吗?”
他只好连忙跪下叩首:“小的会好好侍奉公主。”
公主也蹲下来,侧着头来打量他,“侍奉?我不用你侍奉,安儿倒叫我照顾你呢!我见着你喜欢那个花儿才摘的,你不喜欢吗?”
怀吉的头低的更下去,一直贴到地上,“公主摘得,怀吉都喜欢。”
她忽然站起身去,重新叫婢女帮她洗脚,“你明明不喜欢,那下次我不摘便是了,安儿在时,我倒不见你总这么跪她。”
......
她若是对一个人好,便是真的好。
就算凶凶的,也总是为了那个人好的。
她带着他偷偷跑到垂拱殿去看驸马同人说话,驸马是很早之前就定好的,章懿太后的次侄,官家的表弟,论理,她要叫一声表叔的,也只比她大五岁,如今定了尚主,全因着官家对章懿太后的愧疚之情。
驸马长得过于敦厚些,说话也敦厚些。
公主踩着他的背朝殿里看,一会儿跺一下脚,一会儿又跺一下脚。
回去的路上,就皱着眉头。
“你说驸马长得丑吗?”
“怀吉不知道。”
“反正不如你和安儿,连爹爹宫里的都班知都不如。”她有些丧气。
“怀吉听说,驸马素有才名。”
“什么呀?我方才听了,半天没说出一句叫人合心的话来,看着也不聪明、也不伶俐、木头似的一个人。”公主又跺了脚,连脸色也悲戚起来。
“哥哥,你说我爹爹就没旁的赏赐了吗?给他们家高高的官职,给上好些金银财宝,不好吗?一定......”她歪着头拂过柳树垂下的枝丫,站在湖边上,就着夕阳和晚风,一脸少见的落寞,“何必一定要将我赏了去呢?”
怀吉远远地躬着身子,这话,端的是小侯爷问过的,“怀吉哥哥,你说我母亲他们就没别的法子表忠心了吗?何必非得将我独个儿留在这儿呢?他们对我都是极好的,可是,我不喜欢这里......”
他们一同站在朱红色的围墙下,抬起头,也只有四四方方这一片小小的天,那个时候,他很想同她说一句,“怀吉也不喜欢啊”,可是这话,他如何敢说出来。
“等公子长大了,自有旁的可尽忠的法子,便不必日日拘在这里了。”
“嗯嗯,便等我长大些,等我长大了,有了尽忠的法子,我便出去了,我也带着哥哥出去,不叫哥哥也给人拘在这里。”
他眼睛里噙着泪,自他少时走进这厚重的宫门里来,再没料想过有朝一日还能出的去呢?是出不去了的了!他自己也努力地断了这念想,可这儿有个小小的人,她握着拳头,扑闪着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一副好大的决心,她就这么直晃晃地,没有一丝遮掩地说,“我也带着哥哥出去,不叫哥哥给人也给人拘在这里”......
她是独个儿进来的,要出去,也必是独个儿出去呀!
怀吉笑着,应了好大的一声“唉”!
我的公子,你能出的去便好了,你若出去了,好好在外头待着,别再给人弄进来了才是要紧啊。
原来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苦楚。
官家最为尊贵的大公主娘娘,阖宫里都掂量着磕不得碰不得的这样一个神仙贵人,怀吉却记着她那日站在御湖边上,拂着柳的落寞。她望着远一些宫墙角上坐着的赤金兽说,“你听到他们的议论了吗?我成了我爹爹赏给人的个物件了......”
怀吉低着头,是安便瞧见他鬓角里生出好些个白发,她不由伸手要上去捋,眼睛里好一片惜怜。
怀吉默默侧了身子躲开去,“我如今这么回来......可以吗?”
是安的手给搁在半空里,她哂笑着,又拿下去,“哥哥先去我的园子里,待得我明日当班,一同进去,旁的人不会知道的。”
是偷偷的将他接了来的,官家的身子也不好,到底是心疼女儿,经不住她时时喊叫着求见,跪在膝下求啊!
怀吉两只手牢牢握住已经没了热气儿的手炉,指关节也泛了白。
好好的泡过一个热水澡,又换了是安精心备了的暖和干净的衣裳,已入了夜。
天上疏疏散散又瓢些雪。
接他的檐子路过一径盛放的梅园,往这宅子的深处去。
檐子抬得稳,是轿夫的脚力好。
雪花落在他们黔色的衣裳上,肩头慢慢便白了,一抖一动间,又有些微的白色颗粒顺着滑下去。怀吉的两只手窝在袖子里,连两只脚都蜷缩在袍子下头,他想坐的端正些,可怎么也挺不起腰来。
二十年的奴婢,不止身子是奴婢了,是连心也卑贱起来了。
这宅子的深处果真有一处小楼,外头就看着精致,小楼前头是个亭子,亭子的台阶一直铺到冰里头,便是那汪很好的水了吧!
是很雅致的。
水的一侧,通着一条小径,小径是在一片竹林里。径上积了薄薄的雪,竹竿隐在月色里,看不太真切,隐隐绰绰的。
亭子里摆着一张圆桌,是安着件厚毛大氅,绛色的狐头领子,白色的袍身夹杂着一道又一道泼墨似的绛缕,昏黄的灯下,那白色隐出了橘色,怀吉倒看不清那绛色是染得,还是织就的,她髻上还簪着一枝斜梅,是绿萼梅了。
亭子四角搁着炭盆,又摆着高几,高几上的青瓷瓶子里插着一簇一簇盛放的梅花。
梅花的香气散发出来,还隐隐有些“滋滋”声,他从檐子上下来,是安笑着,站起身来迎他。
“去同公子说,客人来了。”她转过身朝身边一个妆饰不同的女子吩咐,那女子便笑着先同他行过一个礼,退出去唤人。
公子?还有哪一位公子?
是安捉了他的小臂,一路将他牵引到亭子里头坐下,“哥哥觉得凉吗?”还未等他开口,是安又转头朝冰面指了指,“今日忽然下了雪,我想着,有月色和雪色,还有哥哥方才路过的,‘小园’里的梅花香,这地方后头有楼呢,倒挡着风,咱们在这儿吃吃饭,喝喝酒,多有风味!”
怀吉顺着她的手望出去,果然月色和雪色之下,这白堂堂的湖面,煞是叫人觉得敞亮呢!
有下人抬了三面屏风来,将来风的方向堵了个严严实实,怀吉转头,小楼隐在屏风后头,只看到门开了,然后又给人关上了。
那不同妆饰的女子已经从屏风后头转过来,手上还端着坛红瓷的酒。
怀吉脸上带着微微的笑,那屏风后头还有个修长的身影跟过来,他先矮了头,发上是乌木簪子,手上是一支白玉朱穗的笛子。
青色的外袍里头是浅灰色的棉袍子,同怀吉身上穿的正相近。
他一进来,两只眼睛先看向怀吉,唇角淡淡地勾出一抹笑,而后又朝是安一拱手,是安也站起身来,对怀吉道:“这是钟巘。”
怀吉赶紧躬了身子,那钟巘也朝他拱拱手,“在下钟巘,字重山。”
怀吉也赶紧,“我是梁怀吉。”
外头有铃铛声响起来,精巧的婢女们依次传菜过来。
是安转头对那不同妆饰的女子道:“都下去吧,我们自在说会儿话,不要叫人来打扰。”
那女子便颔首朝他们分别施一礼,带着人都退下去,立在远一些的地方等着。
是安亲自执了壶倾酒,对怀吉一一介绍道:“这道牛肉、这个蹄髈,还有鱼羹都是特地请樊楼的厨子来做的,这个梅糕是甜酸口的,特请的是悦香楼的人来做的,还有啊,哥哥快尝尝这个炙羊肉,还有这个羊肉扁食,可是京兆府的手艺。”
她也为钟巘倾满一杯酒,道:“我哥哥恐怕受不了这个烈酒,暂开开胃,咱们还是换回樊楼的酒吧。”
钟巘也不说话,微微点了头,将那杯中酒一饮而尽。
是安已经夹了炙羊肉放到怀吉碗里,怀吉偏过头看她一脸期待的样子,笑了笑将那羊肉放到口里细细品尝,果然鲜美有味。
是安看他吃的高兴,连忙又多夹了一筷子过来,“哥哥吃的高兴就多吃些。”
外头的雪簌簌地下的大起来,屏风里头也飘进来些,好在没有什么风。偶尔有婢女过来添些炭火,银炭正旺的时候,她从怀里搂出一捧梅花来,猛猛顷了,不多时便有“滋滋”地声音发出来,梅香同碳灰香夹杂起来,有才暖过胃的西风烈酒,又有杯中赤黄的甜酒,怀吉拿起杯中酒,有些摇晃的站起身来,对钟巘道:“重山公子。”
钟巘见他朝自己敬酒,也站起身来,身形巍峨,面容又似玉山,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青袍的带子吹起来,从他颜间过,他擎着酒杯,微低了头,等着怀吉开口。
怀吉忽然想起公主来,倘若不是那个木头一样的李公炤,而是面前这个孤松一样的钟重山该多好啊!
慰藉在她身旁,谈诗论画也罢、蹴鞠跑马也罢,偶一醉酒,玉山倾在眼前,便是不说话,公主心里也不会更觉得落寞吧!
是安也站起身来,怀吉低着头,眼泪滑进酒杯里,他一仰脖子,杯中酒便尽了。
有隐隐地琵琶声不知从哪儿传来,是安到他身边扶住他,“怀吉哥哥?”
她语带哽咽,怀吉的眼眶便更红些,他自己斟上酒,重又对上钟巘清冷的眸子,“拜托了!”
拜托了,拜托什么?他说不出,想拜托看顾好她?想拜托别弃了她?想拜托别为难她?还是想拜托别叫她受委屈?他张了张口,自己也说不分明。
钟巘接言道:“好。”
怀吉听他应的这样干脆爽利,可面上却波澜不惊地,仿佛在说起一件再平常不过,理所当然的事情。
怀吉又转过头来看是安,“若公主活不成了,我怕也活不成了,公子你呀......”他将自己的手放在是安的肩上,很想去摸摸她的头顶,可是不成啊,俩个人之间隔着厚厚的屏障,这屏障天生而来的,他不配、也不敢。
是安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她紧紧握住怀吉的手臂,“不会的,不会的,公主姐姐见了你,就会好起来的,哥哥快别瞎说。”
“公子你呀......”他不由想起以前春天的时候,他扎了纸鸢,同她在御花园放,纸鸢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忽然断了线,她跑着去追纸鸢,磕倒在地上,被他背着沿着宫墙跑,“哥哥,我们追不上了......”她伏在他的背上,叫着“蝴蝶、蝴蝶......别自己飞呀。”
后来,公主赤着脚也在御花园里跑,后头有嬷嬷和婢女跟着喊,“公主娘娘小心脚”,她权当没听见,拽着风筝的线,从御花园里跑到宫墙的甬道上去,沿着宫墙跑,大笑着叫他的名字,“怀吉,怀吉哥哥,你快来呀,风筝要飞了......”
圣人娘娘的凤驾正从福宁殿出来,风筝还在天上飞,她却忽然停住脚,两只脚交缠在一起,拼命地往裙下藏。
“倘若我们能像风筝一样飞出去就好了......”她后来说。
“公子你呀,可以像风筝一样自在地飞了。”
可以像风筝一样自在地飞了吗?
是安的马车从西华门进去,一直停在公主殿阁的门口,怀吉穿上那平常普通、深绿色的衣裳躬着身子立在是安后头。
一身银甲的程是安带着他,里头的婢女打开门,迎着是安走进去。
那些弯腰或者跪着的人,他们的目光从是安身上转移到怀吉身上,好奇心要戳破天去,便就是这个瘦弱矮小的人吗?看着不像是传说中那样书生一样的人啊?
公主散着头发,手背上包了帕子,帕子上浸着洗不干净的血,是怀吉熟识的样子,是安已经上前去跪下身子同公主问安,“姐姐今日还好吗?”
公主正坐在榻上,赤着脚折一只红色的飞鹤。
她见是安来了,立刻笑道:“你来了,快看,姐姐正折到你呢......”她面前放着一个小篓子,里头大大小小是各色的飞鹤,被她串着,每三个串成一条,串好了就挂起来,下头坠一个铃铛,挂到书案外边的屋檐上,铃铛一响,叮铃铃地,她就去看她的飞鹤飞起来。
是安将头盔摘下来,放到案上,又从怀里抽出一块帕子,将公主的脚包起来,用两只手捂着,“姐姐不是同我说好了,咱们冬日里要穿上鞋的,等天暖了,再赤脚的吗?”
公主见她帮自己暖着脚,便笑道:“你冷吗?我昨夜也没听到外头吹着风,今儿早起一看,竟积了那么厚的雪,你冷不冷?到姐姐这里坐,这里暖和!”她又往塌子里头移了移,拍着自己才坐过的地方,对是安道。
是安拍了拍自己的铠甲,“我才来,还未去应卯呢!姐姐不看看,我带了谁来吗?”
公主顺着她的手看过去,那躬着身子的瘦弱身影不是怀吉是谁?
她一时竟没认出来,左看看右看看,再看看是安,忽然红了眼圈道,“你不哄我?”
是安摇了摇头,笑道:“我何时哄过你?”
她便缓缓地从榻上下来,眼睛直盯住怀吉,手里的飞鹤也掉在榻上。是安的帕子还缠着她的一只脚,她下榻后趔趄着差点摔倒,还没等是安来扶她,她自己已经站好了,快步移到怀吉边上。
是安等着她放声大哭的,可她竟没有。
她看着他的侧脸,又看到他鬓间的白发,眼泪这才涌上来,可是她噙着它,不叫落下来。
是安走过去,听到她忽然开口问,“哥哥还活着?”
怀吉便跪下磕头,是安赶紧扶他起身。
她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下来,“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哥哥怎么老成这样?“
怀吉便抬起头来,也流着眼泪,“因为担忧娘娘在宫中的日子。”
她便笑了,笑的极为难看,瘦削的脸上,两个颧骨挂着,苍白的唇色也被牙齿咬出了一条痕,她忽然一把搂过怀吉,又一把将是安也揽在怀里,大笑着也大哭着。
这还是三个人第一次哭成一团吧。
是安抬了抬手,也将公主和怀吉揽住。
“哥哥、姐姐,同我”,我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