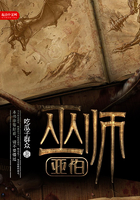郜芝兰道:“三公子,你与铁舟素来要好,如今他死了,剩下我们母女,又惹了天大的麻烦,我想,这天下间,也只有“九凤楼”的总楼才能护得我女儿的周全。”
凤天允忙道:“嫂夫人放心,我们这便启程,以后,你和畔儿便在总楼落脚,那里以后便是你们的家。”
郜芝兰突然跪在凤天允面前,说道:“那我就谢谢三公子了。”
凤天允一看,急忙也跪下,去扶郜芝兰,道:“嫂夫人可折杀我了,万万使不得!”
郜芝兰被他扶起,看了看外面的女儿,又坐到江铁舟身旁,突然吟道:“便把那离别,当成酒。喝得一分暖肠胃,又喝一分暖心头。再喝一分,已添了两行泪。余下七分,尽是哀愁!”说完,她突然一指外面,说道:“三公子,你看,月亮尽了!”
凤天允随着她的手指,看向外边,突然心底一震,感觉不对,猛然回头,却见郜芝兰的心口处正插着那把“泥剑”,已斜倚在江铁舟身边,眼神涣散。
凤天允急向外边的奶妈喊道:“快把畔儿抱进来!”
奶妈已痛哭失声,几步就冲了进来。随后众人也都跟了进来。奶妈把畔儿放到夫妻二人跟前,哽咽道:“畔儿,快看看你的爹娘,叫一声吧!”却见畔儿用手推推江铁舟,又推推郜芝兰,口中有些含糊不清的叫着:“爹!娘!”郜芝兰已然气绝身亡。
在场众人无不泪目!
此时,天已亮了。众人一起把江铁舟、郜芝兰夫妻二人葬在小屋后面不远处。凤天允削木成碑,上刻“江铁舟,郜芝兰之墓”,下款刻的是“女,江畔立。”
待所有事已完成,贺铁岚对着凤天允一施礼,说道:“此番承蒙搭救,贺铁岚、穆铁箫感激不尽。”
穆铁箫也一施礼道:“江湖路远,天涯无尽。此一别,多多珍重。他日若得相聚,当邀月同醉,与君不眠!”
凤天允回礼道:“既是江铁舟的兄弟,便也是我凤天允的兄弟,无需客套。还请两位放心,畔儿我会带回总楼,这也是嫂夫人的临终嘱托。以后,“九凤楼”便是畔儿的家。”
他之所以会强调带畔儿回总楼,又说是郜芝兰的临终托孤,是因为贺穆二人一直坚持要把畔儿带走,凤天允再三解释说是郜芝兰的临终授命,才让贺穆二人释怀。
二人离去后,凤天允对福伯、奶妈和陆蛮儿道:“今日“离楼”和“江府”恐都有变,你们不如暂且留在这里,我下山去打探一下消息,再做定夺。倘若明日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回来,陆蛮儿,你记得去总楼的路,到时带他们同去总楼。把畔儿送去。送到之后,你们可自行选择留下与否。”说完,身形一晃,向山下掠去。
此时,江州府衙大堂之上。冯贵守战战兢兢的跪在下面,靳文忠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来,说道:“你与那江铁舟夫妇平日可有联系?”
冯贵守猛一抬头,道:“没有!大人,冤枉啊!”
靳文忠眯着眼睛,问道:“那前日为何你会放行那些前来拜祭之人?如没有交往,又怎会给了江铁舟的面子。说说看,本府断不会冤枉了你。”
冯贵守额头汗珠已冒了出来,猛磕头道:“大人明察,前日……前日那些前来祭拜之人是在张贴告示之前就已来了,等贴了告示,他们就都准备走了,他们可以作证!”说着一指当时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
靳文忠看了一眼那几个人,问道:“是这样么?”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道:“禀大人,是这样,只是……”
靳文忠微笑道:“只是什么,实话实说,没关系的,只要不违法规,本府自当公事公办。”
那人道:“我们似乎看见那江铁舟往冯贵守的手里塞了东西,却不知是什么?”
冯贵守磕头如捣蒜,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小人一时迷了心窍,那江铁舟确然塞了一锭银子给小人,但小人之前真的不认识江铁舟。还请大人恕罪。”
靳文忠温柔的道:“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收受贿赂,你胆子可不小啊!我看那江铁舟跟你很是有默契啊!”
冯贵守一脸惊恐,突然道:“大人,莫不如让小人带些人,去抄了江府,也好将功折罪。”
靳文忠把头都快要贴在冯贵守的脸上,温柔的问道:“你教教我,给他安个什么罪名?说说看?”
冯贵守低下头来,想了想,却不知如何作答。靳文忠死死的盯着他看,说道:“怎么?没有罪名是么?”
冯贵守喘着粗气,额头上汗水直流。靳文忠道:“你知不知道这伏铁川的罪名是怎样来的?你知不知道江铁舟身属“离楼”?你知不知道这“离楼”又身属“九凤楼”?你又知不知道“九凤楼”总楼主凤云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一个小小的知府又怎得罪得起。倘若我们不能当场抓住他们的把柄,事后又怎敢动他们一动。你呀!还是见识太少,不过,你公然收受贿赂,却是难免惩戒了。”说完,扬声道:“冯贵守擅自收受他人贿赂,杖责三十。”
即刻有负责行刑的两人走上前来,把冯贵守按在地上,褪去裤子,随着冯贵守的一声惨叫,旁边的人在数着:“一,二,三,四……”当数到四的时候,冯贵守早已皮开肉绽,惨叫如杀猪。当数到十的时候,冯贵守早已无力喊叫。靳文忠摇了摇头,道:“哎呀!你们也算同僚,怎的单打屁股,这可不把人打废了。剩下二十杖,我来打。”说着,他一摆手,在一人手中接过庭杖,然后,一杖抡圆了“呼”的一声,打在冯贵守的后背,再一杖打在左肩,又一杖打在右肩。这二十杖打下来,没有一个同点。瞬间,只见冯贵守满身各处都被血水渗透,俨然已成了一个血人。二十杖打完,靳文忠将庭杖交给别人,喘着粗气,自怀里取出手帕,轻轻的擦着手,道:“抬下去,好好养伤。”说完,靳文忠缓缓抬头,看向外面。眼睛里露出猛兽一般的光芒,渐渐的眯成了一条线。